
进入新时代以来,戏剧工作者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戏剧作品[1],由艺术高原向艺术高峰不断抵进。在历史剧创作中,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历史文献,出现了一批以古代历史和文人贤士为素材的戏剧,以此赓续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知古鉴今,推陈出新。在红色历史、革命题材戏剧创作中,表现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卓绝历程,塑造人民英雄。在现实题材戏剧创作中,以一大批主题性艺术作品书写当代传奇,追求现实诗意。在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中,有效实现了从文学到戏剧的转型,取得了良好的剧场效益。此外,“新空间”“云演艺”,科技赋能戏剧,在剧场艺术的呈现与传播途径的延展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新时代十年美术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潮美术,与世纪之交的艺术全球化思潮,都发生了根本性改观。宏大叙事再度成为中国美术的当代性课题,架上艺术持续平衡发展显现出西方艺术世界所未有的另一种当代艺术景观,新艺科建设、美术馆发展、新型展览机制与科技艺术探索共同形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的新业态。显然,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变化不再以西方所定义的“当代艺术”为唯一路标,对艺术“当代性”的解读与实践,更着眼于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体现中国优秀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着眼于对人民这个中国现代社会的主体的精神塑造。本文试图从新时代十年美术的发展中,以理论话语勾勒出中国美术探索自主发展的新路。

新时代以来,在“两个结合”和“两创”方针指导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新作中呈现的人民性更加深邃,人民的风姿仪态更加自信,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舞台意境更加高妙和神奇;中国古典舞创作者更加深入探究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舞蹈文化元素,从历史文物和艺术遗产中提取舞蹈元素,再加以时代审美观照下的动态演绎,成为中国古典舞创作的一股强劲潮流;舞剧更是进入井喷式发展的马力全开时期,近200部舞剧不仅在现实题材方面勇猛推进,题材和舞台呈现样式也多姿多彩,与民同情,与时共进。中国舞蹈驶入全面推进、迅猛成长的快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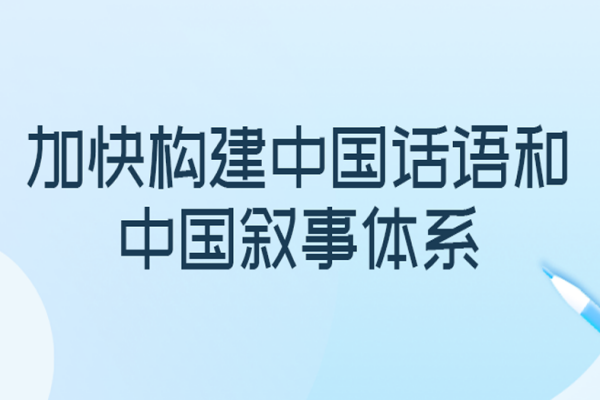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中国实践出发,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包含的价值观、文明观显现为一种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观,承载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新时代的中国文艺,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站稳中华文化立场,牢牢掌握中华文明的审美权,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创作出更多增强中国人民精神力量、增强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优秀作品,以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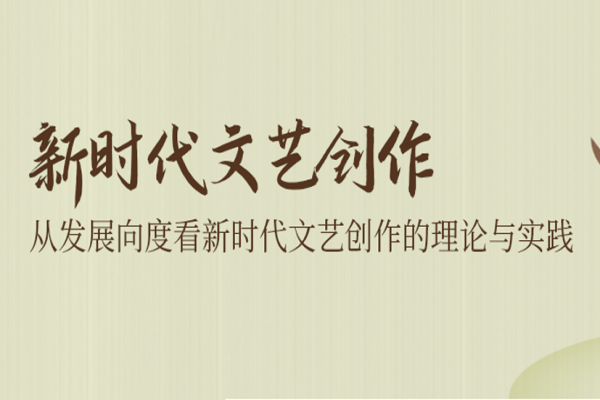
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反思中国文化,必须更加重视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内质和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其中蕴含着的生命性、血脉性、基因性、恒久性、文明性、人类性、世界性、现代性。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间的重要属性:文化与文化的类型差异和异同问题,即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及其相异相同的贯穿性问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今天,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骨气、志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是我们解答这个时代命题的科学方法论。由于文艺的形象性、可视性、独创性、审美性,整个中国的形象正在伟大的文明重塑和再现之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学风范。

流溯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正生长着的一种新美质。中国艺术美质经历了从古典感兴到现代流兴和典型、流型以及流溯的转变历程。流溯是一种在向前流动中同时溯洄过去的新旧糅合的美质,主要着眼于在当下境遇中激活古老文明精华而又同时让其融入面向未来的创新过程中,成为既流向未来而又同时溯洄传统的当代生活流中化生的创造性美质,包括溯源出新、溯洄本真、今昔漩洑、慕古启今、古雅流俗、心结开释等具体呈现。流溯的结果在于溯源创生,即在流向未来过程中同时返身溯洄往昔而转化成的新艺术美质。

人民文艺是新时代的文艺,它不同于民间文艺、消费文艺和群众文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才会出现真正的人民文艺。人民文艺将精英文艺、民间文艺、消费文艺、群众文艺整合起来,以建设性介入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突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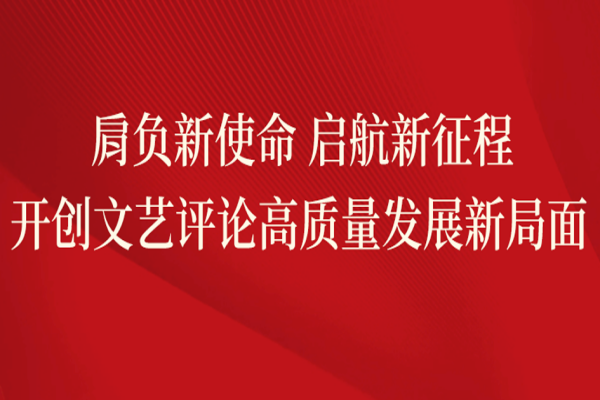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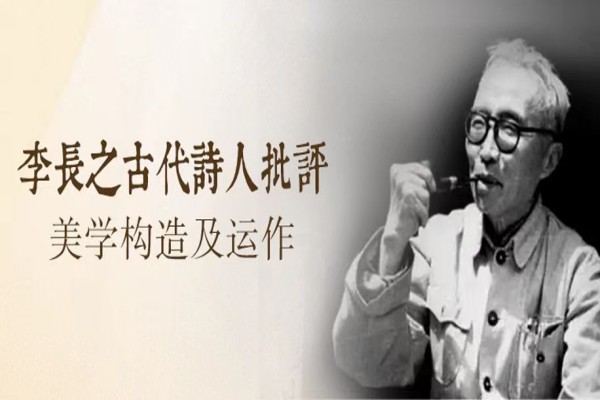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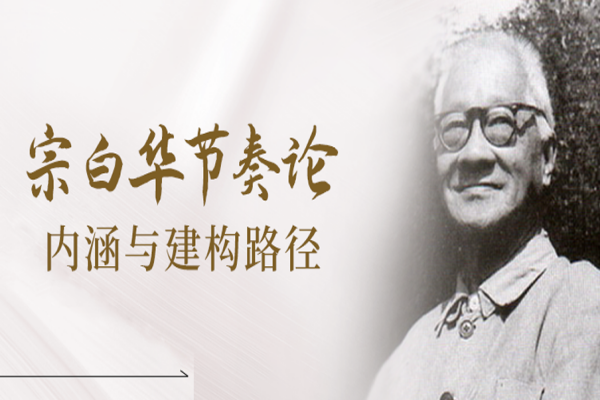
在宗白华的节奏论中,“节奏”的内涵有一个由形式层面的“一致”向生命、哲学层面的“条理”的转变过程,前者作为一种“数理的节奏”指形式上的和谐一致,产生于某一形式要素的周期性重复;后者作为“生命的节奏”指宇宙自然的规律和条理,则产生于事物正反两种特性的交替呈现。艺术形式—艺术生命—哲学—文化精神,是宗白华节奏论的建构路径。节奏论作为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具有鲜明的“及物性”特征和人生艺术化的现实指向,并非完全指向形上学境界。宗白华在节奏论建构中体现的中西互鉴、新旧融合、媒介互参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审美性阐发,使节奏论成为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对于建构中国现代美学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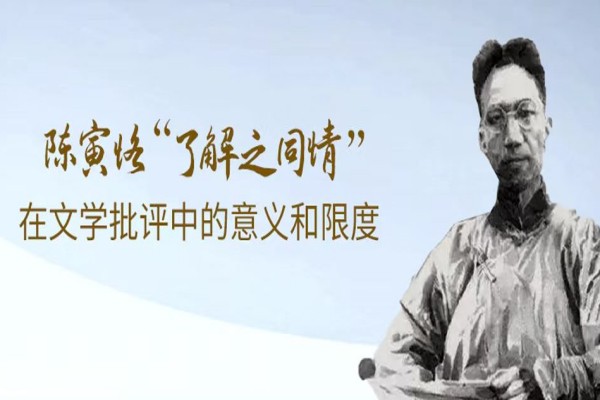
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合理应用于文学批评,有益于以“考据”与“移情”兼重的姿态,正视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品格、开显文学批评应有之“作者”视角,为思考“文本含义”的特征、思考文学评价的多元可能提供有益启示。该说在文学批评中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泥于历史主义思维模式,窄化有关创作真相的诠释空间;执着于还原创作真相,对文学现象其他要素关注不够;在衡量文学批评的水准时,时常体现出“作者中心主义”立场,部分结论有独断之嫌。进入文学批评的“了解之同情”,应保持对文学现象“审美性”的合理理解,在关注作者问题的同时,形成对单一批评视角的超越。

本文撷取2023年度具有典型性的事件、作品和现象,从舞蹈创作者的生存样态、舞蹈创作中的经典转化和舞蹈评论的时代挑战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笔者认为,舞蹈创作者所面临的新挑战是从过去在艺术创作和市场消费之间寻找平衡,转向寻找二者与网络评论之间的三点平衡;在经典的当代转化中,中国舞蹈编导作出了自己的审美尝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提高的空间;中国舞蹈评论需要审视自身的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加以对待,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作为科技创新的年度热词,也引发了美术界有关创作智能化话题的讨论。2023年度举办的若干个大型双年展以及其他艺术与科技展,都体现了AI图像挑战对艺术态势的新发。与此相反,包括AIGC图像生成在内的科技视觉强化也在不断损耗着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另一种对艺术本体的认知,2023年度美术的相关创作与展览均在这一学术氛围中展开。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则为全国美术馆的综合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各种规模化的中外藏品展形成了艺术史叙事的社会审美教育景观。

2023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六大方面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指引下,艺术学理论自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西方现代化既有路径,以“三大体系”建设引领中国人文研究新形态;在艺术学学科方面,新学科目录调整推动新时代艺术学研究及教育格局的不断完善;在艺术学理论基础理论及评论方面,强调“史、论、评”结合,且艺术评论得到重视和充分讨论;在美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与艺术学理论的交融方面,对中西古典美学概念进行溯源和重构,并对本土概念进行创造性阐释和价值肯认,促进各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在媒介研究方面,对媒介本体的思考、跨媒介艺术理论及相应的批评标准与时俱进,并在艺术管理、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展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人工智能与艺术跨界融合方面,从艺术实践到理论生产、研究范式以及人才培养得到切实推进。

2023年的国产电影创作在众多挑战与期待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头部影片在春节档、暑期档等核心档期引领观影市场,现实主义成为影视从业者的自觉意识,类型片和艺术片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内容多样性,以当代视听艺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新的标志性成果。2023年度电影创作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温暖现实与悬疑叙事的交响,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都力图呈现出与当代观众之间的情感贴近性。青年观影群体对于电影的艺术性和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也随着行业的发展而水涨船高。只有在故事强度、视听强度和情感强度三个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国产电影才能够在网络视听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持续地吸引观众,为整个社会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供给。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带领下,2023年的中国书法创作、研究和组织传播等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思想和观念的引领,特别是评论与创作的互动,以及在创作导向上的承续出新,使书法艺术既体现出了经典的传承,又呼应了新时代所提出的期待和要求。本文将从书法展赛与创作、书法教育与研究、书法管理与传播三个角度对2023年度书坛重大事件展开观察与评论,旨在为当代书法史写作积累史料,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有待突破的空间。

2023年度曲艺艺术的发展与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演活动频繁,许多新创节目反映了曲艺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探索中亦有深入的思考;二是青年曲艺人才的集中亮相,积极发挥其在业界的引领作用,亦凸显出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三是曲艺理论评论与创作、演出的有机融合,对于曲艺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曲艺事业的整体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相间的表达方式,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曲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优势,更是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

2023年,中国美学在守正与创新中奋力书写崭新篇章。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中国美学界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美学的历史脉络,推动美学的话语更新,以美学的价值引导功能,铸就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互动共生。与此同时,学界聚焦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美学流派等方面,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系统整合勾勒中国美学的整体图景。中西美学的交流互鉴,推动了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打破了西方美学研究范式的主导地位,彰显出中国美学的世界意义。在学科交叉与视域融合中,当代美学从理论对话、实践指向与现实旨归三重维度呈现出发展新趋势。

2023年民间文学在承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其表现出研究话题更为集中,特别是对民间文学口头性、集体性、人民性及体裁、语境的讨论,彰显出民间文学领域进行理论建设的自觉与学术愿景;而在对学科史、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研究者立足当下面临问题时的思考及结合时代语境对过去学人研究的重新阐释。在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研究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注重结合时代命题,多维度、立体化地进行理论拓展。当然,无论在哪个论域,我们都能看到2023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有待提升之处及未来的新趋向。

2023年是中国网络文艺聚力奋发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放异彩,奇点将至,未来已来,网络文艺跃入智能传播时代(智媒时代),网络科幻进入主赛道,“国潮热”涌动,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微短剧积微成著,展现出磅礴的想象力。网络文艺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在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用优质内容化解网生代的数字化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