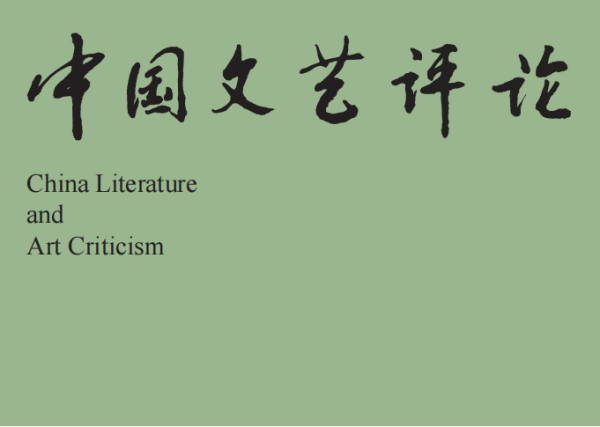

【编者按】 关于“人物性格二重性”这一文艺创作论题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强调摒弃传统的人物塑造典型化,在人物塑造上挖掘其“多重性格”,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活、立体。在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不断深化的当下,这一论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近年来,《人民的名义》 《狂飙》等电视剧中极具立体感、生活化、复杂性的人物形象,引发人们的热议。本期特邀专家学者聚焦这一热点现象,撰写理论评论文章,共同探讨文艺创作中关于人物塑造的核心问题。
——论当前国产影视剧创作的一种趋势
【内容摘要】 近年来,塑造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剧式反面人物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一种潮流。这种悲剧化书写,主要是通过展现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与展现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两种方式实现的。这一潮流的出现与我国影视剧创作类型意识的强化与现实主义的深化有关,也与当下网络时代/妥协社会受众的审美趣味与集体心理有关。恶的悲剧化潜藏着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因此创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反面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次要性格、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关系,把握好描画恶的尺度。
【关 键 词】 反面人物 悲剧化 国产影视 人物性格
近年来,人物性格刻画的复杂化、含混化成为国产影视剧的明显趋向。在此背景下,国产影视剧中涌现出高启强(《狂飙》)、叶文洁(《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秘的角落》)、辛小丰(《烈日灼心》)、王兴德夫妇(《开端》)、李承天(《回来的女儿》)、曹建军(《警察荣誉》)、沈墨(《漫长的季节》)等一大批性格复杂、善恶兼有的反面人物。这些人物命运的共通之处在于有着或多或少的悲剧性色彩,并由此屡屡引发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其中像高启强、张东升等人物甚至在网络空间中被肆意地戏仿、玩梗,成为全民热议的艺术形象。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深思:塑造令人共情的悲剧式反面人物,为何正成为一种潮流?本文尝试总结当前国产影视剧中恶的悲剧化书写的不同路径,从社会文化与艺术观念的角度剖解这一创作潮流的深层成因,并进一步探讨其中亟待正视与纠偏的问题。
一、化恶为悲的两种路径
现实生活中的恶令人深恶痛绝,但文艺作品中的恶却能引发复杂的审美体验。作为文艺作品中恶的集中体现,反面人物相对正面人物常常有更为开阔的塑造空间。正面人物如果无法引人共情,可能就很难具备充分的艺术感染力。但对于反面人物而言,令人感到恐惧和厌恶是一种胜利,令人感到同情与怜悯又是另一种成功。
我国影视剧对于反面人物的塑造,常常有定型化、喜剧化等方式。前者是以恶写恶,从政治或伦理批判的角度将反面人物塑造为与正面人物相对立的功能性配角,南霸天(《红色娘子军》)、胡汉三(《闪闪的红星》)、安嘉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李丰田(《无证之罪》)等都属此类;后者则是化恶为喜,将反面人物塑造为可供俯视与调侃的讽刺型人物,例如中村下等兵(《举起手来》)、高博(《人再囧途之泰囧》)、胡广生(《无名之辈》)等。
当下国产影视剧创作则越来越善于化恶为悲,书写反面人物有价值的事物及其毁灭的过程,以此呈现某种特殊的悲剧感。在具体的悲剧化书写中,大致又体现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展现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反面人物如果有纯善的一面,这种特质又走向沦丧或毁灭,便常常会引发观众的怜悯之情。电视剧《狂飙》中,高启强原本是安分守己、懦弱纯良的底层鱼贩。由于遭受恶势力的威胁而陷入绝境,他内心黑暗幽深的欲望才被点燃,不断滑向犯罪的深渊。网剧《漫长的季节》中,由于父母双亡,女主角沈墨自小被有着恋童癖与控制欲的大伯领养,在精神与身体上常年遭受后者的侵犯,大学时代勤工俭学期间又不幸受到不良商人的凌辱,最终阴暗人格被激发,走上手刃仇人的犯罪道路。
与《狂飙》《漫长的季节》不同,电影《烈日灼心》采取了另一条相反的路径:先讲述辛小丰、杨自道等几位逃犯在隐姓埋名、亡命天涯的生活中所流露出的善良特质,以及他们混杂着忏悔、侥幸、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心理状态与生存困境,再展现他们最终伏法的结局。这部影片有意逃离传统警匪片“二元对立” “非黑即白”的叙事惯例,而是立足于道德的灰色地带,将善与恶、罪与罚的游移混杂作为叙事的重点。通过先抑后扬的方式,影片中几位反面人物长期流露出的忏悔心理以及抚养养女的善举,也能够有效地激发观众的同情之心。
另一条化恶为悲的路径,是展现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一些对于反面人物来说异常重要的美好事物的被摧毁,同样可以营造人物的悲剧性。例如,在网剧《开端》中,公交车司机王兴德及其妻子陶映红之所以长期谋划公交车爆炸案,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女儿意外因车祸而亡、且在去世后遭受网络暴力的事实。对于王兴德夫妇而言,女儿的生命与名誉无疑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事物,却均被无法抵抗的外部力量所粉碎,令观众很难不对其遭遇心生怜悯。
需要看到的是,仅仅展现出了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或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还不足以使反面人物具有更为充分的悲剧性。悲剧性的产生,在于悲剧人物所遭遇的困厄,更在于悲剧人物深陷困厄时所体现出的抗争精神。正如朱光潜所说,“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对于悲剧人物来说,无论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其反抗都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勇于面对命运、打破现实束缚的冲动,常常能够体现出富有感染力的主体精神与生命价值。高启强、沈墨、王兴德、陶映红等人物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抗争僭越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体现出的是一种畸形的、非正义的崇高。
此外,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许多作品常常将反面人物的上述两种价值的毁灭归咎于家庭环境、社会体制、历史创伤等外部原因,归咎于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从而凸显其命运的悲怆与无奈。电视剧《警察荣誉》中,警察曹建军在岳父母长期的嫌贫爱富和冷嘲热讽下养成自卑又自大的性格,由此才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从警界英雄到锒铛入狱的囚犯,再到最后自我救赎式的牺牲。电视剧《三体》中,作为地球三体组织的统帅,叶文洁之所以背叛人类,在于她在特殊年代里遭遇和承受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创伤。父亲的死亡、家庭的崩塌、个人的磨难以及整个社会忏悔意识的匮乏,让她切实感受到人性之恶,进而产生精神危机,只能将救赎与改造人类的目光投向浩瀚宇宙。可见,国产影视剧正是通过描写反面人物的痛苦时刻,刻画他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进而让反面人物由善入恶的人物弧光更加引人共鸣。
二、进化的观念与逾越的想象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反面人物的悲剧化塑造,为何在当前的国产影视剧里成为一种潮流或趋势?考察这一问题,既要考虑国产影视剧艺术创作自身的演进,也要兼顾社会语境的迁移和受众趣味的变化。
以往国产影视剧的反面人物塑造,常常流于概念化、平面化,或沦为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化身,或缺乏较为丰满立体的性格。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工业化程度不断深入、流媒体产业崛起,以及好莱坞、韩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创作经验的不断渗透,中国内地影视剧的创作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迭代,突出地表现为类型创新意识的强化与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一方面,类型创新意识的强化尤其体现在悬疑影视剧等类型的兴盛上。在当前小屏观剧的流媒体时代,为迎合注意力分散时代观众的趣味,同时规避小屏幕在呈现场面奇观上的劣势,创作者们越来越偏爱营造紧凑刺激的故事奇观,由此导致悬疑等类型的流行。随着《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优质作品引发强烈的市场反响,各大流媒体平台与影视制作公司纷纷介入悬疑影视剧的生产中,尤以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品牌为代表。由于可将悬疑元素与犯罪、推理、动作、科幻等各种类型进行自由嫁接,悬疑影视剧体现出十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一类型天然地善于呈现人性的隐秘幽微,也就为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和反面人物的悲剧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产影视剧也在持续探索现实主义书写的可能。这首先体现在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从现实的逻辑出发去塑造人物,呼应现实生活本身的无边与流动。现实中的人性原本就是含混幽微的,充满了模糊地带。正如高尔基所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与此同时,创作者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反面人物进行典型化处理,通过人物去映射或揭示社会现实的某些本质特征。例如电视剧《狂飙》中,如果说正面人物安欣是现代法理社会的代表,那么高启强可谓传统人情社会的代表。后者发迹的旧厂街这一熟人社会,又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运作机制隐秘勾连。因此,剧中安欣与高启强的博弈与其说是简单的警匪对决,不如说是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法理精神与人情传统的冲突。理解了这一层,才能体会到“高启强”这一悲剧式反面人物的典型意义。
其次,反面人物的悲剧化潮流之所以出现,也与当前受众群体对此类形象的喜好与认同息息相关。纵观中西艺术史,文艺作品总是善于通过对恶的描画,来呈现一种逾越的美学兴致。如同德国学者阿尔特在《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恶总是作为扰乱的角色出现,在这种扰乱中一种混乱不堪的结构得到了反映”。就影视艺术来说,不乏有黑帮片等样式着力于塑造各式各样的“反英雄”(anti-hero)或“恶棍主人公”(villain protagonist),以此为观众内心深层的越轨心理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满足。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受众群体身处网络社会/妥协社会的独特语境中。一方面,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是解构化、分众化、狂欢化的时代,网络时代的受众擅长以游戏的精神消解崇高、解构权威。“雪姨”“容嬷嬷”等一些荧幕反派角色近年来屡屡遭遇恶搞与调侃便是例证。这些反派人物在“鬼畜”视频、表情包等各种“网络迷因”(internet meme)中大肆流转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反面人物原本所携带的叙事内容与符号意义被消解,观众先前对于这类人物的憎恶之情也随之淡化,甚至在传播过程中开始与人物产生共情。这种文化土壤,使得互联网时代的受众对反面人物似乎持有更多的宽容与理解。今日受众对完美的英雄与单薄的反派正日益产生审美厌倦,他们更期望看到现实的人性与人性的现实。
另一重不可忽略的语境在于,当下社会正日益走向“躺平”与“内卷”作为一体两面、充满了集体倦怠感的功绩社会与妥协社会。韩炳哲认为,这种社会发展状态的一大特点在于患有痛苦恐惧症。如他所言,在妥协社会中,“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对于妥协社会中的人们而言,悲剧化的反面人物恰恰能够提供一种痛苦的快感与逾越的想象,以供他们纾解现实生活中的忧郁和苦闷。
在这方面,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反面人物祁同伟的接受状况就颇具代表性。剧中,出身寒门的祁同伟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不断僭越法律边界,最终走上了饮弹自尽的悲怆结局。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凝结了攀附权贵的扭曲心灵和贫苦出身的小农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于连式的人物。因此,与剧中的其他反面人物相比,祁同伟的命运尤其引发了许多观众的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观众从这一寒门子弟身上看到了一个底层人物试图加入权力游戏、打破阶层壁垒的野心,也看到了穷尽所有也无法更改的痛苦宿命。
三、如何把握恶的尺度?
然而问题在于,恶的悲剧化也潜藏着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反面人物的悲剧命运使人同情、怜悯和惋惜,进而会令观众对其行为与理念产生认同感。如果对恶的尺度把握不好,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的边界也就变得含混不清。因此,有论者认为恶的悲剧化书写是一种“大胆突进”的行为,“不但尽力于邪恶中去发掘反面人物‘否定的美质’及其自我毁灭,而且还因缺乏必要的道德限制往往导致认同紊乱”。人性原本复杂,但恰恰由于现实的含混,使得文艺作品在书写复杂性的同时更应该划出一条善与恶的大致界限,并进一步抑恶扬善。
那么在悲剧式反面人物的塑造中,该如何把握恶的尺度呢?在本文看来,在描写人物复杂性、展现悲剧性命运的同时,创作者首先应当处理好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次要性格之间的关系,以恶的主导性格来统领善的次要性格。从整体上来看,反面人物应当以邪恶、反动、暴戾、破坏等负面价值因素为主导,尤其是性格发展的后期,更应该凸显其恶的主导性格。如果善恶的比重处理失当,就有可能导致反面人物的正面价值过于凸显。
以电视剧《狂飙》为例,创作者虽然用了大量笔墨展现高启强心狠手辣、胸有城府、唯利是图的一面,但同时又用了过多的篇幅来描画他重情重义的一面,导致后一种性格似乎更占据主导性。该剧一方面极力描画他与老默、龙哥等人的江湖道义,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他与高启盛、高启兰的兄妹情谊,这就让高启强俨然成为一种朴素真诚的传统伦理观的化身。例如,该剧不厌其烦地反复展现高启强吃猪脚面的场面,这并非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实际上,正是通过反复对“猪脚面”这一饮食符号背后所负载的高家情感故事的追忆,高启强这一不忘本、重家庭、有担当的兄长形象也不断地得以稳固。反观安欣,由于创作者对他的家庭环境和情感关系的着墨太少,同时将人物塑造得有些执拗、理性甚至不近人情,以至于该人物的共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高启强所压制。
其次,在展现反面人物悲剧性命运时,创作者还应该处理好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间的关系,避免将悲剧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外部因素。家庭氛围、社会环境等固然是个体命运的催化剂,但个人的性格与选择同样也是重要推手。将反面人物全然塑造为某种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那既是一种忽略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的取巧的现实主义,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豁免了反面人物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导致一种伦理的错位与价值的误导。
与此同时,在塑造反面人物时,创造者要意识到反面人物常常是作为正面人物的镜像存在的,二者往往处在辩证互动的紧密关系中。因此,能否塑造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正面人物,以此制衡反面人物的共情力量,同样显得十分重要。当前许多国产影视剧恰恰在主要正面人物的塑造方面还有待提升。例如网剧《回来的女儿》中,女主角陈佑希作为正面人物就没有展现出太多令人共情的特质。作为一位身世不详、敢于挑战秩序与常俗的孤儿,她一开始只身逃离福利院、千方百计寻找密友的行为展现出有情有义的性格。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一人物的矛盾之处开始逐渐显露,不仅时常在冲动与冷静之间、睿智与失智之间反复摇摆,人物行为还常常前后不一,很难让观众产生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反倒是剧中的反面人物李承天所流露出的因爱生恨的真实性格,更能引发观众的怜悯与同情。
当然,对于观众来说,同样也需要提升对悲剧式反面人物的理解。文艺作品中恶的书写,说到底所要激发的应当是人们内心的幽暗意识。在“幽暗意识”概念的提出者张灏看来,幽暗意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幽暗意识指代的是我们需要正视与警觉人世间的种种阴暗面,广义的幽暗意识则是指根据这种正视与警觉去认识与反思人性在知识与道德上的限制。就此而言,幽暗意识并不代表着对阴暗面的价值认可,其目的反而是以恶的剖解来反思善的可能,“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带着这样的幽暗意识去看待当前国产影视剧中的悲剧式反面人物时,我们所惋惜的就不再是其恶的被惩罚,而是其善的被毁灭。
作者:李宁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5期(总第92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