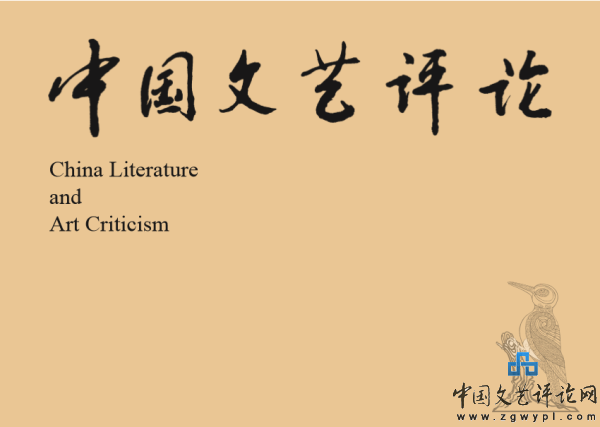
内容摘要:沈从文在短篇小说《知识》中讲述了一个有关生死的奇特故事。作者通过对佛经母本的刻意改写,有意拉开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传达出对知识的独特见解。知识、智慧和生命构成了沈从文检视知识有效性的三个维度,对于知识的过度推崇,对于生命力量的有意忽视,会消解智慧,使知识变成无用的欲望载体。沈从文的知识观与文学观互为映照,他对于作者重要性的强调,对于知识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对于创作与生命问题的考察,对于人民的热爱与尊重,为当代作家知识观与文学观的树立提供了借鉴。
关 键 词:沈从文 小说 《知识》 知识观 文学观

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重要推动力,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似乎就对服务于思想启蒙的知识抱有极大的热情。“乡下人”沈从文也关注知识,他直接以“知识”为题创作小说,表达自己对于知识的独特思考。
在沈从文的文字世界中,短篇小说《知识》毫不起眼。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知识》的文献资料较为有限,其中金介普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有一段不足200字的短评可以代表学界对于该文主题的一种思考:《知识》是沈从文泛神论思想的一种反映。笔者认为,以神学之光点亮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实是加深了“沈从文的寂寞”。言有尽而意无穷,沈从文借《知识》表达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文字背后,他对于知识、智慧、生命、文学等问题的思考,也许能成为破解当代文坛浮躁困境的锦囊。
一、“否定”知识的《知识》:沈从文的文本圈套
阅读《知识》对于读者而言,是一次挑战。摆在读者面前的通常是一连串问题:《知识》究竟在说什么,《知识》和“知识”是什么关系,沈从文为什么否定知识,又为什么创作《知识》?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进行文本细读。
沈从文钟情文学创作,著作等身,其中既有家喻户晓、广受赞誉的名篇,如《边城》《萧萧》,也有知晓面较窄、晦涩难懂的文章,如《腐烂》《生》,更不乏对于奇异湘西世界的书写,如《柏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展现与汉地相异的湘西经验世界为主的,有“民俗‘展览’之嫌”[1]。沈从文心恋湘西,却身在都市,他的小说不是写给乡下人,而是写给城里人看的。农村伢子要在高手如云的都市文坛站稳脚跟,确实需要借边地风情博人眼球。因此,沈从文注重小说的故事性,有意向读者展示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风俗人事。

在此背景下阅读《知识》可以发现此篇确是一篇奇文,奇特的取材增强了文本的陌生化效果,模糊了小说的主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忍不住反复咀嚼,试图解开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一个又一个谜团。那么,沈从文是否在借怪异的小说博人眼球,占领图书市场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短篇小说《知识》创作于1934年10月,最早收录在小说集《新与旧》中。如果将沈从文的创作进行分期,可以发现,《知识》的创作时间恰好与《边城》接近,这一阶段沈从文的写作观已从书写奇异湘西风情为主的湘西牧歌滋生阶段中走出。他对于作品在图书市场上的流行并不满意,发出买椟还珠的叹息,希望读者多关注作品背后的热情与悲痛。所以,《知识》是沈从文文字理想的延伸,传达出他对于文字的独特情感。
沈从文怀揣着“抓住手中的笔,不论个人成败”[2]的信念写作,积极进行文学实践。他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模式,《阿丽思中国游记》被称为“叙事方式大杂烩”;《凤子》有意打乱纵向线性叙事结构;《八骏图》采取了单向书信体形式。沈从文对于叙事技巧的重视也体现在《知识》中。《知识》的主线故事写的是张六吉回乡的奇遇,叙事时遵循时间行进的脉络,以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主体,以对白和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内心,较为传统。然而,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小说中对于“关键”内容的有意省略,如对张六吉和刘家后生交流的呈现:
他说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不用问,反正这件事使张六吉听到真吃了一大惊。乡下人那么诚实,毫不含糊,他不能不相信那乡下人说的话。他心想,“这是真的假的?”同先前在田里所见一样,只需再稍稍注意,就明白一切全是真事了![3]
刘家后生对张六吉说了什么?读者不得而知。但作家又告诉读者,在结束了和刘家后生的交流,到了家乡之后,张六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骂他那博学多闻、身在异国的先生,继而将所有书籍全部烧毁,最后演进为六吉和刘家后生目的不明的出走。由此可见,他们交流的内容是直接推动张六吉知识观转变的关键,十分重要。但沈从文故作神秘,对于关键情节的有意省略给张六吉清晰的回乡历程蒙上了一层迷雾。这种省略不同于《边城》结尾处为营造悲剧氛围对于傩送何时归来的留白,沈从文在《知识》中的处理更偏向于技巧实验。一句“那不用问”,显示出作者的全知优越感,却使读者陷入不可知的困惑。
沈从文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营造出难以调和的矛盾,折射出他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实力与野心。沈从文注重小说的故事性,但他的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那么简单。金介普援引A.J.普林斯的考察,认为《知识》是沈从文泛神论思想的一种反映。与郭沫若强调“泛神即是无神”不同,“沈把生命看成泛神的精灵”,“主张把生命提高到不仅仅为了生活”[4]。金介普对于《知识》主题的推断主要源于这篇小说的佛教色彩和沈从文文学创作后期越来越明显的宗教倾向和泛神论思想。
《知识》是对于佛经故事的改写,这一点通常容易被人所忽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是因为沈从文并未像写《月下小景》时那样,在每篇末尾标示佛经出处;二是因为其对佛经故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写。《知识》以《佛说五无反复经》为母本,借鉴了佛经中的情节,却模糊了原文中“流转生死。迁神不灭。死而复生。如车轮转”的佛理奥义。在改写过程中,沈从文有意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与读者拉近,将故事从印度的舍卫国拽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长江中部乡村。他将小说的主人公从梵志改为哲学硕士,又借小说中人物之口突出现实生活的不易,控诉军队、土匪对农人的折磨,并着重书写哲学硕士与其导师的决裂,剑指现代知识的无用。诚然,《知识》对于人的死生无常给予了观照,但若该文仅仅是为了体现泛神论思想,上述改写与加工又显然多余。所以,《知识》并非沈从文的改写炫技之作,小说的主题应该在泛神论之外还有其他。
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旧有的一切都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呈现出凋敝之势,努力朝帮助“寂寞地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5]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知识》记录的正是作者从生命的角度对于现代文明,及其伴生物“知识”的探讨。
二、张六吉知识观三阶段与沈从文知识考察三维度
“知识”构成了小说的标题,小说中对于知识的描述是解开谜团的关键。小说主人公张六吉知识观的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于知识的探寻阶段。20岁的张六吉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出国留学,以“人生哲学”为研究对象攻读硕士学位,希望将所学贡献给社会。文中并没有揭示张六吉对于“人生哲学”的研究结论究竟是什么,只说“离家乡越近时,他的‘超人’感觉也越浓厚”[6]。由此可以推断,他和五四时期觉悟的很多青年一样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这些使他和乡土中国格格不入。
第二个阶段是新旧知识的冲突阶段。张六吉对老农一家生命观的态度从最初的不解、震惊转变为认同与信服。这之中涉及一个新、旧知识观的对比问题。“学然后知不足”, 中国的现代进程离不开对西方知识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当中国人逐渐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上感觉不足,对于外国知识文化的憧憬也日益强盛。陈独秀主张“以欧化为是”,直言“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寸之余地”;胡适为再造文明开出“输入学理”的药方,鲁迅也提倡“多读外国书”。《知识》却反其道而行之,极言新知的无用。正如收录《知识》的小说集的标题,新与旧的关系探讨广泛地存在于沈从文的小说之中。持文化保守主义的沈从文,对于旧中国文明的依恋,使张六吉内心的天平倒向了旧的一端。“他同许多人一样,出了学校回国来无法插进社会”[7]。张六吉信奉的西方哲学离开了主体享有话语权的空间,注定是难以在中国土地上立足的。
由此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知识的重塑阶段。欲形成新的,必先使旧的灭亡。张六吉以与新知识决裂的方式,向旧知识靠拢。他写信咒骂导师,将十多年来在国外习得的“全是活人不用知道的”[8]知识付之一炬,选择留在野蛮的家乡,拜农人为师,学习来自于泥土的知识。沈从文有意隐瞒向乡土缴械投降之后的张六吉的具体情况,不交代他究竟学了什么,为什么出走,走去了哪里,却对他的未来抱有信心。乡下人的知识没有西方哲学那么玄奥,却能让人淡然面对生死,积极应对人生,助人完成从生活到生命的超越。
张六吉对知识态度的转变折射出沈从文的知识观。《知识》创作于1934年。此时,距离沈从文1923年离开湖南北上,已经过去了11年。11年前,阅读了《新潮》《改造》《创造》等报刊的沈从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走出湘西。11年后,他在高校谋得教席,出版文学作品,主持文学刊物,抱得美人归,似乎已在都市文坛站稳了脚跟,但他对知识的关注始终没有改变。
和张六吉一样,沈从文也经历过对知识的疯狂追寻阶段。但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沈从文是知识上的“弱者”。拿不出手的文凭,第一次上课时的窘态,总是让他疑心自己知识的不足。他曾努力学习和阅读,以丰富自己的知识。除佛洛依德、泰戈尔、歌德、尼采外,J.H.鲁宾逊、T.J.安格乐、J.克伦、J.G.弗里契、E.菲尔格林、龚古尔兄弟、佛楼拜、狄更斯、卡莱尔等人都是沈从文学问的来源[9]。但他渐渐发现,“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学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发牢骚”[10],于社会进步并无十分厉害之关系的。随之而来的,是他对知识的重新审视。
细读沈从文的著作可以发现,“知识”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高频词,仅在《从文自传》中就出现了14次。但沈从文对于知识的界定较为特殊,尤其注重将知识与智慧相区别。在《历史是一条河》中他临水感怀,将历史视为一条恒久流动的河流,畅言“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却强调“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11]。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他强调“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12]。对知识与智慧的区分并非沈从文行文的疏忽,而是他独特知识观的体现。

首先,知识与智慧的获得途径不同。基于沈从文的文字表述,可以发现,从好书、好话上学来的是知识,从生活上吸收消化的是智慧;在军队中学到的是知识,从印刷工人那里学到的是智慧。知识是理性的,可以从书籍中习得。智慧是感性的,来源于山头夕阳、水底原石,来源于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历史长河,来源于对世界和人类的爱。
其次,知识与智慧的作用不同。能解答疑问的是知识,为人类去设想是智慧。中国近代以来对于知识的推崇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性,即以获取知识为手段,实现民族复兴,如鲁迅远赴日本是因为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西医的事实,沈从文从湘西出走也多半是受到了新知的鼓动。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倘若知识的功利主义将知识拖拽到卑俗,则格外需要注意。因为“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13]而“人类知识到达某种程度时,能够稍稍离开日常生活中的哀乐得失而单独构思,就必然觉得生命受自然限制……到结果终必败北”。[14]沈从文不认可将知识作为争权夺利的手段,直言:“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15]与功利倾向明显的知识不同,智慧来源于对生命的感悟,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开展。智慧必然与生命相联系,而知识则未必。这也解释了沈从文为什么要借一个有关生死的故事讨论“知识”。沈从文对于智慧的青睐表明了他对待文学的态度:对知识功利主义的拒斥,对文学社会价值与生命力量的推崇。
再次,沈从文笔下的知识与智慧的关系较为复杂,不对立却也不兼容。沈从文深知知识的获得是使人享有智慧的重要途径。他说,“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6]。但智慧力量的彰显却并不依赖知识而实现。他对知识与智慧的区分恰如庄子所强调的“忘知之知”。知识、智慧和生命是沈从文考察知识有效性的三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知识的过度推崇,对原始生命力量的有意忽视,甚至会消解智慧,使知识变成无用的欲望载体。
沈从文的知识观是他生命哲学的投射,“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与真理的必然结果”[17]。对知识的特殊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沈从文在文坛中的孤立,却也为他提供了观察现代生活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角度。这个乡下人渐渐放下对知识的执念,将自己植根于泥土的智慧当作尺和秤,丈量社会,沉入人生,将证明了价值和意义的生命写入小说,引导读者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18]。
三、互为映照的知识观与文学观
沈从文对于文学,并不是秉持无功利主义。他的文学创作围绕人性展开,认为“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善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使读者“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19]。这种集对知识与生命思考于一体的文学观正是沈从文建构纯美湘西世界的重要推动力。
沈从文是超时代的,也是寂寞的,这种寂寞不亚于鲁迅在铁屋中的呐喊。沈从文身上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签,常常使人忽视了他作品中的先锋精神与批判意识。对知识的向往与批判,反映出沈从文对于文学创作与民族命运的思考。他批判一套用文字写成的无可记载的历史,进而感到无言的哀戚。因为这套历史只是无生命痕迹的知识,对于水手、拉船人、妓女、小兵俨然毫无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知识的异化,却将文笔进一步伸向抹布阶级的日常生活,在日常叙事中唤醒读者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翠翠、柏子、虎雏不仅演绎出湘西世界的好坏人事,更记录了湘西自然的生命形态。沈从文的文字世界中始终活跃着大写的人,这一点竟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文艺观不谋而合。
沈从文写人,又不仅写人。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立,在于给过热的现代知识崇拜泼一盆冷水,帮助读者看清中国社会的“常”与“变”。创作《知识》的同年,沈从文回湘西,发现在“现代”二字的影响下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却又呈现出堕落趋势。他看到许多由知识狂潮带来的生命力枯竭的明证:“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足矣。……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20]但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文明在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在消耗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呢?“对于同一事物,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知’的方法去知它。最简单最原始的‘知’是直觉(intuition),其次是知觉(perception),最后是概念(conception)。”[21]参考近代哲学对知识的讨论可以发现,知识的获取应当遵循从“知”(直觉)到“识”(概念),也即从实践出发的过程。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掌握难以做到从直觉出发,更多的是基于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实践缺席的制约。“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22],空间影响着知识的使用,离开了西方语境的知识如不能和中国社会有机结合,实难发挥作用。尽管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沈从文对于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思考,仍然让人敬佩。
他写《边城》,写《湘行散记》,写《湘西》,其实都是在用中国的文笔描述“中国故事”,寄希望于“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23],恢复中国人朴素而有力的原始生命形态。写人,赞扬人性之美;写人性,唤醒生命本质力量;写生命,重燃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沈从文尽管没有直接进行革命文学写作,对于民族、国家的关切却丝毫不弱。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借由对知识的考察所进行的文艺批判。20世纪30年代是沈从文知识观的重整与定型阶段。与“海派”的论争,使他对知识进行了更深的思考。他反对将知识作为敛财的工具。1933年沈从文作《文学者的态度》,对票友白相式文人予以批判,呼唤作家端正态度,诚实地写作,“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24];同月,作《知识阶级与进步》,借用颟顸的国王愚弄乡民的故事,表达自己对知识阶级及所肩负责任的考量;第二年春天,又发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对“海派”概念予以阐释,并直批文坛中“商业竞卖”“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冒充风雅”“邀功牟利”[25]等风气,提出作家和刊物应当“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给读者提供社会所必需的东西。这些杂文写得尖锐犀利,与描绘湘西世界时清丽健朗的文风差异明显,看似在与“海派”博弈,实际是在传达对于文学的态度。他不满为法币而忙碌的庸俗实际主义,呼唤“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认为“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较坚朴的人生观”,而“优秀的脑子”应对于“生命”有较深的认识。[26]
四、沈从文的知识观与文学观的当代价值
沈从文对于知识等问题的考察立足于时代,却又超越时代。如今离先生去世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信息的传播,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也衍生出新的文艺形态,但沈从文的知识观、文学观却并未过时。细想起来,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与沈从文探讨知识的年代仍有相似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家群体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成为了社会上一种特殊而重要的阶级,似乎作家一挥笔,就能产生比其他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大概因为较早洞悉了知识作用的有限,沈从文并没有在作家的光环中迷失,而是有感于当时作家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围绕文坛出现的“差不多”现象,批评赶时髦的作家“记着‘时代’,忘了‘艺术’”,“既想作品坐收商品利益,又欲作品产生经典意义”[27],杂念太多,使“差不多”作品横行于世,犹如八股文一般引读者嫌恶。
这种对于“差不多”现象的揭示与批判直接击中了当代文坛的病灶。《鬼吹灯》火了,盗墓文风行一时;《致青春》火了,不出国、不恋爱都不好意思叫校园小说;《步步惊心》火了,历史题材小说恨不得都穿越一把;《甄嬛传》火了,小说里的皇帝除了处理后宫问题基本上不需要干别的活儿了;《战狼2》火了,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想尽办法融入国际题材。“差不多”现象不仅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也存在于21世纪的今天。那么,“差不多”问题是否无解呢?沈从文并不这样认为。
他提出“唯一的希望是在作者本身”,作者需要端正写作态度,“得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羞辱,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失败”[28]。他拿自己的创作经历举例,提出:“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29]的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今天,文学作品不免具有经济价值与商品属性,与其他物质商品一样在货架上陈列,供人选购,但文学作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商品。文学艺术的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运行的法则对其价值进行测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是建立在艺术价值的基础上的。“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制作者还可匠心独运,不落窠臼,社会上流行的风格,流行的款式,尽可置之不问。”[30]优秀的作家应该成为新风格、新款式的创造者,而不应该成为“差不多”风格的追随者。
进而,沈从文提出文学经典的问题。他质疑文学经典的产生,将文学的商品利益和经典意义视为鱼与熊掌,认为文学创作容不得太大的野心,作家借助创作“坐收一点商品利益,作品对于大多数读者实在无多意义”[31]。他将经典产生的希望依旧投注在作家身上,希望作家努力创作“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这种经典从表达民族感情的作品中产生,能“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民族精神,也许一时难以被市场接受,“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32]。
随着文学观念的转变和媒介的发展,文学生产集创作、传播、接受、批评等环节于一身的属性更加突出。尽管近年来“作者死了”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就文学生产本身而言,作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仍不容忽视。所以,尽管沈从文将攻克“差不多”问题、创作文学经典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作者身上有一定理想主义倾向,却仍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沈从文对作者的关注有利于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学生产很难不受市场、资本等要素的影响,文学生产的权力也自然向市场和读者转移。因此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33]。沈从文针对作者所提出的建议,旨在从文学生产的初始环节帮助作家明确目的,扭转功利化的创作倾向,使文学朝符合时代潮流、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方向发展。
其次,沈从文通过阐释知识与文学的关系,引导作者关注日常生活与人生实践。与“新文人”式的作者相比,沈从文欣赏的是“乡巴佬”式的作者。这种“乡巴佬”虽然不是专家,也没有学位,但“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他的“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所以他总能用眼睛看到书本以外的一切。“乡巴佬”不排斥知识,他从书本学到了文学上的各种知识与技巧,再将这些与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一切问题结合起来。“乡巴佬”创作出来的作品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知识与智慧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34]。作者应善于学习知识,更要善于应用知识。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需要与日常生活和人生实践相结合,才能化为智慧的闪光,化为不朽的文学作品。
再次,沈从文通过对创作与个体生命关系的考察,强调文学创作要围绕人展开。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取材于“湘西山区周围一些荒僻小山城、村落”,这些地方记录着他的生命成长,也记录着小小土地上善良人民的人事哀乐。这些“历史”不屑触及的小人物,“是我国亿万人民在旧社会的缩影”[35],承载着沉淀到岁月深处的民族传统与生命力。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文学作品应该以人民为服务对象,书写人民的生活与心灵,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用文字记录人民的智慧,使中华民族优美崇高的风度长存。
最后,沈从文通过强调文学为人民服务,要求作家少一些欲望和野心。文学创作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必须扎根生活、贴近人民,要舍得花精力,要守得了清贫,耐得住寂寞,受得了非议。自作聪明地“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做经典的尊严”[36],只会使读者对文学失望、反感。创作经典应成为作家的毕生追求,“物质失败,精神胜利”的作品,在时间带走了流行偏见和愚行后,“终会不朽,永远留存”[37]。

[1] 乔以钢、罗振亚:《现代中国文学(1898—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4页。
[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4] [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324—325页。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7] 同上,第319页。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9] [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1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1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12] 同上,第252页。
[1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1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1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
[17]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19]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2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22]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5] 同上,第54页。
[2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9-311页。
[27] 同上,第102页。
[2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29]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3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3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30日。
[3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6-87页。
[3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8页。
[3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3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作者:李文浩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2期(总第3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何美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