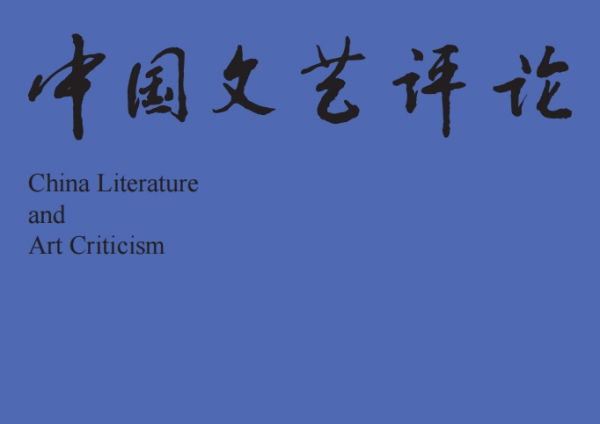

【内容摘要】 对于红色电影来说,“崇高”是重要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机制。从“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电影到新时代红色电影,一系列“崇高身体”往往同战争再现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这也形成了独特的视听语言形式及美学风格。尤其在“化动为静”和“化景为人”的作用下,红色电影中的英雄身体具有了仪式化、雕塑化和风景化等审美特征。由此可见,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体现了该类型在主题、叙事和美学等方面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关 键 词】 红色电影 战争电影 新时代 崇高 身体
“红色电影”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艺的重要构成,在记录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继承革命文艺传统的同时,形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审美品位和文化品格。从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自1942年以来,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而在广义上,它则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所有反映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电影作品。从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对普罗大众的关注,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体主义的革命激情,再到新世纪以来政治和商业交织的影像奇观,红色电影作为一类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实践,其滥觞、确立和回响的整个进程始终与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彼此交织,构成了无数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记录、反思、建构现代经验的重要场域。这其中,对战争的再现构成了红色电影的重要影像内容。从“十七年”时期的《钢铁战士》(1950)、《董存瑞》(1955)、《上甘岭》(1956)、《狼牙山五壮士》(1958)、《英雄儿女》(1964),到近年来的《智取威虎山》(2014)、《建军大业》(2017)、《八佰》(2020)、《金刚川》(2020)、《悬崖之上》(2021)、《长津湖》(2021)……大量精品化的红色电影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视听盛宴,也创造出新的叙事和美学特征。
对于红色电影来说,“崇高”(sublime)是非常重要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机制。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崇高这一范畴的古罗马哲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强调“崇高是高尚心灵的回声”,并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证崇高;而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将崇高视为“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且往往“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将崇高同“优美”相对应。受其影响,康德(Immanuel Kant)从审美判断的理性分析角度,深入到审美主体的接受层面,认为崇高是在经过个体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理性思考之后所产生的超越生命的强大的抵抗性、优越性的巨大影响力,尤其表现为数学和力学这两种崇高——数学的崇高通过表象或多或少地展现于外,进而激发个体的理性批判力;而力学的崇高是超越个人意志的强大威慑力,直接激发出个体的内在理性力量。而在中国美学体系中,从《诗经•大雅》里的“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到《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浩然之气”再到屈原《离骚》《天问》中的高贵品质与精神向度,“崇高”自有渊源与脉络,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常借由崇山峻岭来喻指德行高尚与精神引领。到了晚清,王国维借鉴西方的“崇高”,提出“壮美”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重要的起点之一。
“崇高”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和分析红色电影提供了重要的美学维度。根据王斑的说法,“崇高”的本指是一种“对人性的超越”,尤其体现为“令人们肃然起敬的超人品质”或者“肩负历史使命的民族去实施人类进步与解放的乌托邦式蓝图”。这样一种“超越”也就是一个“文化启迪与提升的过程”,通过“对个人和政治圆满的崇高极致的奋力追求、阻挡危险与威胁的身体防御机制、供大众效仿的不断更新的英雄人物、身体的傲岸形象,或者是使人形容枯槁的极端消沉与叫人振奋的无比狂喜”等,令人们得以净化并压抑带有人性色彩的特征(如食欲、情感、理智、感官、想象、恐惧、激情、欲望、自利,等等)。于是,在红色电影中,“崇高”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通过视听叙事与表达“挖掘观众情感的源泉来营造强烈的美与情感”,进而“将个体的生活和欢乐不断转移到革命体验的过程中”,这也使得“崇高”成为了红色电影重要的生产与审美机制。
本文在此论述基础上,探讨“崇高”在红色电影尤其是战争场面的人物身体塑造方面的视觉语言特征,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从红色经典电影到新时代红色电影,战争场面中“崇高身体”的塑造在视觉语言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此,本文一方面将“崇高身体”的视觉塑造问题放在中国红色电影美学史的角度进行历时性思考,并着重探讨“崇高英雄”的凸显过程与方式;另一方面则从“化动为静”和“化景为人”两个角度,分析崇高身体仪式化、雕塑化和风景化的特征,由此探索新时代红色电影对“红色经典”的传承与发展,展示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在影像美学上不断衍生、回响与创新的路径。
英雄身体:“崇高”的历时辩证呈现
陈亦水曾撰文梳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崇高审美文化流变,特别强调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崇高美学在叙事层面上被赋予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意味,尤其是“当个体呈现出超人的强大意志力和战斗力,在与恐怖的客观物象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个体转变为崇高的主体”。因此,英雄人物成为银幕上崇高美的集中表现。沿着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察红色电影的历时发展脉络,会发现这样一种突出英雄人物的崇高美学,来源于左翼电影的艺术传统,之后便成为了红色电影典型特征得以确立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狂流》(1933)、《天明》(1933)、《大路》(1934)、《渔光曲》(1934)、《马路天使》(1937)等左翼电影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以现实主义的风格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再现普罗大众的苦难与反抗,已然确立了革命进步影片的基调;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史东山、阳翰笙、郑君里、田汉、蔡楚生、赵丹、孙瑜等左翼影人所摄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万家灯火》(1948)、《乌鸦与麻雀》(1949)等进步影片,不仅继承了左翼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民众觉醒并走向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开始具有强烈的史诗气质,并有意识地以阶级话语呈现战争的历史动因,展示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从这些影片中,我们看到一种独特的电影实践在此时萌芽,这类电影并不是对革命历史的被动记录和再现,而是主动地参与战争革命历史本身的诠释和建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革命历史影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左翼电影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但是在英雄人物的身体再现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左翼电影对战争的再现往往围绕底层人物展开,强调其颠沛流离、可悲可悯的苦情境遇。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孙瑜导演的《小玩意》(1933)以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村民视角展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残酷;解放战争时期,左翼影人陈鲤庭、赵丹等人创作的影片《遥远的爱》(1948)以底层女佣余珍在战争中的苦难和觉醒为线索,展现了抗日战争以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因此在这些影片里,所谓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直接参与并改变历史的强力个体,而是在社会不公和战争磋磨中不断实现自我成长和觉醒的受难者。这些角色的“英雄性”或者“崇高性”并不来自于他们正面、积极、阳光的外在形象,反倒是借助一系列身体的残缺和创伤得以呈现。在《小玩意》里,女主人公叶大嫂因为贫穷和战争相继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唯一的女儿长大成人后投身淞沪抗战前线,并最终献出了生命。影片用一系列特写镜头对准了主人公身体的创伤和苦难:叶大嫂布满泪水的脸庞、女儿嘴角的鲜血、战士们残破的衣服和受伤的肢体……不仅如此,在影片《小玩意》的最后,历经苦难的叶大嫂在众人的搀扶下,拖着病痛虚弱的身体控诉帝国主义战争对人民的压迫。此时的她面向镜头,瘦削的面庞上显露出无比坚毅的神情,画面随之定格。在这个定格的特写镜头里,主人公身体上的脆弱衰朽反衬出精神上的崇高和永恒,悲苦柔弱的身躯最终指向了不屈而伟大的革命意志。
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左翼电影里这些“苦弱”的身体展现,一方面是对苦难战争和残酷现实的记录,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曲线救国”式的表达策略:在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制度下,这些左翼影片主人公们的身体创伤以苦情的方式揭示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进而掩盖了有关阶级和革命的电影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左翼战争电影里对身体创伤的呈现实际上具有一种双面性——这些苦弱身体并不总是指向精神上的崇高,它同样也是一种软弱和妥协。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该影片与《小玩意》《遥远的爱》类似,从一个底层妇女的视角出发,呈现了自抗日战争以来的革命历程。影片同样以苦情戏的结构呈现了战争的苦难和动荡的时局对女主人公身体的伤害,但是正如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见,影片的苦情叙事最终并没有成功地转化为革命叙事,以女主人公素芬为代表的底层民众们所遭遇的身体创伤最终成为了他们“逆来顺受”的证明:“在影片中所表现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日寇的民族压迫和国民党的阶级压迫下面,却没有成长和觉醒,对一切凌辱与苦难始终只是逆来顺受。”
因此,如果说左翼影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创作迫使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苦情人物保留述说革命的潜能,那么革命成功之后的电影人则全力驱散一切暧昧曲折的表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多电影都抛弃了战后进步电影隐晦克制的苦情故事母题。一方面,以《中华女儿》(1949)、《桥》(1949)、《钢铁战士》(1950)、《新儿女英雄传》(1951)、《南征北战》(1952)为代表的红色影片选择正面再现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与革命斗争运动;另一方面,《刘胡兰》(1950)、《赵一曼》(1950)、《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以革命先烈为原型,塑造了一系列积极投身革命的崇高英雄人物。这些作品不仅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而且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也创造了新的崇高美学——大仰角的低角度摄影、三点补光法、景别的两级匹配等,都成为再现英雄人物及其身体影像的典型方法。
举例而言,同样是使用叠映技巧呈现农民革命的战争场面,《武训传》(1950)当中使用了大量的俯拍镜头,并且将这些俯拍的战争画面快速剪辑在一起,配以节奏强烈的音乐,呈现了清末时局的动荡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艰辛;但是在电影《刘胡兰》中,叠映的战争场景由仰拍镜头构成,画面在激昂的抒情女声合唱中缓慢切换,背景处则是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身影。在这个仰拍镜头叠映的时刻,革命战争的伟大与英雄身体的伟岸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关系——革命精神的崇高最终体现为英雄人物及其身体在仰拍镜头下巨大而崇高的视觉效果。因此有论者指出,以《刘胡兰》为代表的“革命者”人物的出现,意味着此时的红色电影已经初步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这种新的美学风格要求“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以无产阶级革命观点把握和再现现实,以‘典型论’的创作手法反映和塑造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和各条战线建设中涌现出的新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强调这些人物身上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可以说,这些影片一方面采取了与战后进步电影类似的革命战争叙事,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起电影叙事及其历史阐释的根本逻辑;另一方面又用更加正面、直接的方式再现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取代了战后进步电影的苦情套路。此时的影片已经不再着力呈现底层民众在战乱中遭遇的身体创伤,而是强调革命英雄们积极昂扬、傲岸有力的身体姿态。这种创作风格和身体影像一方面克服了左翼电影模棱两可的苦情表达,在英雄人物伟岸的身体和崇高的精神之间建立起了象征性的联系;但另一方面,这种身体与精神之间直接的象征关系也使得英雄人物的身体再现沦为了一系列扁平、僵化的符号游戏,并最终在“样板戏”的创作中到达极致——以1972年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例,影片里的定焦镜头和程式化的场面调度严格遵循“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正面英雄人物始终被框定在画面中心;千篇一律的仰拍视角记录下这些英雄人物积极昂扬的面部表情;舞台化的平面置景将现实生活的复杂事物转化为抽象的舞台符号;残酷的战争场面被编码为芭蕾舞演员们整齐划一的身体动作。在《红色娘子军》的最后,所有演员面向镜头,以芭蕾舞的姿势整齐地原地踏步,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变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符号表演。
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到来,相关部门专门组织拍摄了一系列献礼影片,在当年的国庆和次年的元旦、春节分三次集中展映。其中,《吉鸿昌》(1979)、《啊!摇篮》(1979)、《小花》(1979)、《归心似箭》(1979)、《从奴隶到将军》(1979)等作品突破了“样板戏”程式化的场面调度和身体再现,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完成建构革命历史的文化使命。在战争场面与英雄人物的身体再现方面,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并没有一味地塑造英雄人物光辉、正面、伟岸的身体形象,而是重新开始关注其柔弱、苦难、创伤的一面。举例而言,《啊!摇篮》中的战士罗桂田身受枪伤,最后不治身亡,影片并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电影那样为之配上一段慷慨激昂的音乐来揭示英雄人物的牺牲精神,而是让罗桂田在孩子们日常的吵闹和童谣声中撒手人寰。而在视觉呈现方面,影片也没有用夸张的仰拍特写捕捉人物高大伟岸的身躯,而是用一个俯拍镜头呈现罗桂田躺在一席草堆上的痛苦神情,随后用特写镜头捕捉其面部因疼痛而流下的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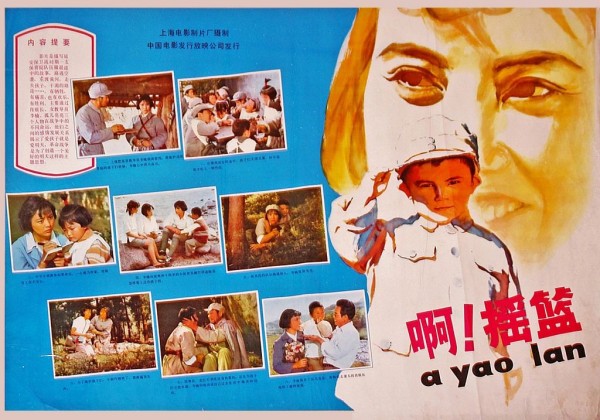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日常化的肉身影像虽然意在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色经典电影对英雄身体的符号化再现,但它本身也同样是一种“崇高”的影像形式。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左翼电影里所看到的那样,身体的苦难和创伤一直是英雄人物完成自我超越和觉醒,进而在精神上实现崇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对身体创伤的描绘实际上广泛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伤痕”文艺之中。在呈现英雄人物的身体影像时,尽管这些“伤痕”电影不再遵循“三突出”等创作原则以制造崇高的美学效果,但是这种看似“去崇高”的努力本身却有赖于大量煽情的身体特写以及歌曲——这一系列放大和过量的视听效果也同样最终诉诸“崇高”的美学形式。正如王斑所见,尽管在“文革”之后的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看似“去崇高化”的思想,但是“去崇高化也是崇高的一种形式——不是超越式的崇高,而是对宏大叙事的深刻的颠覆的崇高”。因此在这些电影里,常常存在着一种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除了宏大崇高的革命事业,革命英雄们也同样无法超脱生活世界中的种种琐事和温情。例如《啊!摇篮》里战士们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与守护、《小花》里翠姑搭救兄长赵永生的义无反顾,以及《归心似箭》里魏得胜与玉贞历经磨难的不渝爱情,等等。因此,这些“伤痕”文艺本质上用一种新的、日常化的宏大叙事取代既有的、革命化的宏大叙事,建构起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非政治化”的艺术追求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化,看似“去崇高”的身体影像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崇高。
此后,中国的电影行业一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一面又在市场化改革中主动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红色电影悄然进入了价值观与商业性相融合的全新阶段。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以《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建军大业》为代表的红色电影一次次打造豪华的明星班底,呈现出青春化、偶像化的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建国大业》并没有像既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一样,邀请大量特型演员饰演对应的历史人物,反而集结了一百七十多位知名的全球华语影星。这种差异意味着红色电影创作逻辑的根本性转变——吸引观众的并不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革命英雄,还有现实中星光熠熠的偶像,革命历史的再现由此具备了可供消费的奇观性。随后的《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更是邀请了一批青年偶像饰演青年时期的革命英雄。因此在这些电影里,革命英雄的身体影像既不是激昂傲岸的崇高符号,也不是充满伤痛的苦弱肉身,而是呈现为一系列偶像化的商业奇观。举例而言,《建军大业》在呈现南昌起义的战斗场面时,不仅以快速切换的蒙太奇将一系列青年偶像饰演的革命历史人物影像组接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还通过降格镜头,以慢动作呈现这些青年偶像饰演的革命英雄在战场上的英姿——刘昊然饰演的粟裕举枪射击,欧豪饰演的叶挺在炮火中整理衣领、发号施令,朱亚文饰演的周恩来在会议室里指挥若定……在影像剪辑节奏的快慢转换之间,电影将战场瞬息万变的殊死搏斗与青年偶像身体的动作呈现进行糅合,呈现出一种青春化、时尚化、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性视觉奇观。同时青年演员的参演,令偶像与英雄两者互为融合,更易于当代青少年观众(尤其是粉丝群体)的接受与支持。而动辄上百位豪华明星班底的演出阵容,令战争英雄更多以群像的方式进行整体呈现,于是相对于红色经典电影中个人英雄的突出,这些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凸显了群体化的特征。
因此,当代观众群体的变化以及电影工业化、产业化的制作方式,令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呈现出商业化、偶像化、群体化等特征。而由全球华语影星共同参与的商业行动,也在政治层面上完成了一次跨区域的国族文化身份建构,彰显了红色电影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走向世界的内在渴望。大量跨国和跨地域合拍的红色电影,通过一系列工业化的动作场面和视觉奇观,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商业大片的视听效果之中,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证明。
总而言之,在红色电影的历时发展过程中,英雄人物“崇高身体”的生成与变化,整体上呈现出辩证性的特征:从左翼电影中英雄的“苦弱”身体和底层再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片中革命英雄的伟岸身体与进步叙事,文艺作品的整体风格也逐渐从“批判现实主义”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从新时期的“创伤”身体和日常表达,到新时代的商业奇观与群体呈现,红色电影的工业美学特征、跨区域制作逻辑、国家战略主题和共同体意识等愈发清晰与凸显。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艺术美学上的“崇高”与“去崇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而是彼此交融、影响与转化的,这尤其体现在对英雄身体的视听语言的运用上;另一方面,从革命的“蓄势与潜能”到“爆发与彰显”,再到“创伤与反思”以及“怀旧与奇观”,不同时期红色电影的“崇高身体”一直与革命意识的表达息息相关,这不仅源自差异化的历史语境尤其是文艺政策的变化,而且同电影的制片、发行和传播模式息息相关。无论如何,银幕上的“崇高身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承担着宣传主流道德价值观并询唤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断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化动为静:刺点、丰碑与仪式
红色电影史上有很多崇高的战斗英雄形象,然而倘若只能择其一,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在《英雄儿女》中,刘世龙饰演的王成为阻止美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战略高地,准备携带炸药纵身跳入敌群。随着战场上的声音(枪声、爆炸声、冲杀声、炮火声等)沉寂下来,磅礴大气的音乐作为画外音逐渐增强,令这一场景具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之感。在交响乐声中,手持爆破筒越出战壕的王成挺身站立,仰拍的视角令其格外高大。王成背后射出的万丈霞光,从云层中照射下来,形成神圣的光环,在其脸部特写镜头中,王成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最终为国捐躯。这一“英雄牺牲”段落,在崇高美学的塑造方面具有叙事和视听语言上的典型性:一方面,英雄牺牲带给观众的悲怆感是“崇高”美学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 ——正如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中所说的:“在所有动人心弦的事情中,死亡恐惧首当其冲”,红色经典电影中的英雄牺牲往往表达了超越人性最大恐惧的理想生命建构,从而具有某种典范性和典型性;另一方面,这一姿态具有强烈的雕塑化特征,配合仰拍视角和万丈霞光,令英雄的身体具有了崇高与神圣的色彩,甚至超越时间,从而凝固为永恒的“丰碑”。
类似的“英雄牺牲”段落也出现在《董存瑞》、《刘胡兰》、《赵一曼》、《党的女儿》(1958)、《狼牙山五壮士》、《烈火中永生》(1965)等其他红色经典影片中。一方面,影片往往借由升格、停顿或配乐的置入来渲染悲怆时刻的氛围;另一方面,演员行动或表演的陡然放慢,令崇高时刻具有了超越时间的永恒性。这样一种“化动为静”的做法,是电影庄严或崇高感塑造的重要来源,而脸部特写及动作姿态的聚焦则成为“化动为静”的表现方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强调电影特写的神圣性主要来自“画格”或“剧照”而非“运动”或“影像”,例如哈库摄影工作室对于演员崇高感的塑造源于“在静止的状态中被摄入”并“被化约为一张涤尽所有动作的脸”,再如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影片《伊凡雷帝》或《战舰波将金号》的崇高性源于电影剧照的衣饰与妆发,具有超越运动和时间的“一种腔调,一种浮现的形式本身,一种标示出信息与意义重叠的褶皱”。其他电影理论家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认为静止的姿态和特写能够截断叙事,从而令“景观代替动作”;让•爱普斯坦(Jean Epstein)则强调脸部和身体特写放大了情感效果而令一切变得“异常敏感”,这种爆发之前积蓄待发的静止时刻最具力量。这样一种弱化动作、表意或叙事,侧重姿态、表情或蓄势的“化动为静”,令观众产生情感触动的“刺点”(punctum),这比起突出意义叙事的“冲击”(studium)来得更为有效,或者说能够更好地营造崇高的审美感受。
这样一种“化动为静”的做法,在新时代的红色电影对战争场景的呈现中,由于拍摄技术与特效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更加广泛的运用。在《长津湖》、《八佰》、《战狼Ⅱ》(2017)、《建军大业》等影片中,爆破与牺牲场景往往多用高速摄影,有些镜头甚至使用了类似于《黑客帝国》式的“子弹时间”和“时间静止”镜头,令爆炸、中弹、死亡等重要的悲剧性时刻得以拉长和放大,从而为观众营造崇高的审美体验。在《金刚川》的结尾处,伴随着画外音中《我的祖国》钢琴曲,冲锋、爆炸、过桥、渡河等都由于高速摄影而变得缓慢,增加了凝重的史诗氛围;同时作为平行蒙太奇的主人公张飞在壮烈牺牲后凝固为金色的雕塑,依然凝望和守护着渡江冲锋的战友们。由此,“化动为静”令英雄的身体变成了超越时间的雕塑,从而具有了某种“纪念碑性”。

据巫鸿解释,“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指的是令建筑、雕像或物件等“具有公共性纪念意义的内部元素”,或者说物质形态所包含的“集体记忆”。人的身体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和腐朽,但类似于兵马俑等塑像的方式能够对抗身体的腐朽从而拥有超越时间的“纪念碑性”。无论是《烈火中永生》《上甘岭》《英雄儿女》,还是《八佰》《金刚川》《长津湖》,红色电影往往将英雄的身体塑造为纪念碑式的雕塑,从而承载集体性、国族性的历史记忆,并拥有对抗时间流逝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纪念碑性”得以对抗时间、直抵永恒的关键在于精神性的道德力量,而这种精神性/超越性的道德力量也正是“崇高”的美学要义。正如康德所见,如果说美是道德上善者的象征,那么“在道德品性中,惟有真正的德性是崇高的”。因此,红色电影里那些具有“纪念碑性”的身体影像也总是凭借其庄严的氛围、集体性的意义和动人心魄的道德力量而具有了崇高感,令受众得到心灵的教育与净化。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在《金刚川》的结尾,影片以特效将朝鲜战场上的一切(山川、桥梁、铁路、战士等)都凝固为灰白的全景式雕塑,并配以参加过战役的年迈老兵的旁白,其中“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及“后代人的幸福,就要靠俺们每个人去拼了”等心声体现了纪念碑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借由纪念碑性的身体影像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道德之力。
红色电影中这些具有纪念碑性的崇高身体,也彰显了造型的仪式性力量。伊芙特•皮洛(Yvette Biro)指出:“仪式是一种社会约束,是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纽带,令人们遵循社会存在的一体化和规范化要求。”影片中具有仪式性的内容,往往具有放大和聚焦的双重效应,以实现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这种仪式性不仅来自于雕塑感本身的造型,而且同视听语言特别是场面调度元素(包括灯光、布景、声音、妆发等)息息相关。在红色经典电影的战争场面中,拍摄英雄丰碑(例如勇敢赴死的江姐和许云峰,或为抗日牺牲的狼牙山五壮士)时,三点布光、背景的虚化、大仰角的低位摄影等技巧创造出经典的仪式化造型,也令人们记住了这些崇高人物。这样一种技巧,令人不禁想到20世纪20年代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所开创的影像风格——例如在《圣女贞德受难记》中,导演几乎完全使用仰拍的特写来表现贞德受难的场景,演员完全不上妆,画面没有层次、没有背景、没有布景,甚至没用灯光,也没有阴影。正是这样一种极富仪式感的拍摄方式,创造了一种强调纯净、神圣与崇高的电影美学。而在红色经典电影中,这样一种雕塑化、仪式化的拍摄方式,在突出英雄人物的同时,也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诉求。
新时代的红色电影往往也通过主人公的身体塑造和成长经历造就诸多经典的仪式化造型,在仪式的美感中实现对崇高的意识形态询唤。例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动用上百位明星出镜,形成了符号化的历史镜像,完成了仪式的“特写”;《金刚川》《八佰》中被炮火烧成焦炭的“雕塑”令平凡的身体仪式化为崇高丰碑;《战狼Ⅱ》中冷锋手擎五星红旗的身体形象强化了爱国主义的仪式性——这些作品都通过特定的服装、道具、灯光和镜头,为观众创造了仪式化的人物身体,使观众如同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一般,内心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昂扬振奋之情。而这样一种宛如丰碑的身体,既表达了革命的曲折性——革命正是抵抗了压迫、经过了痛楚、超越了黑暗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又凸显了克服恐惧、超越死亡的共产主义信仰,呈现了康德“力学的崇高”之美。

总而言之,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是“化动为静”并积蓄能量的片刻,是超越时间而具有纪念碑性的雕塑,是借由惯性和约束实现教育与意识形态功能的仪式。它通过“刺点”而引发观众情感触动,通过与摄影、雕塑、戏剧等艺术的联通而具有跨媒介的特征,通过银幕内外的“情动”和“感染”促成革命和建设的积极行动。红色电影中的英雄身体,成为促进不同代际观众超越个人情感而实现国家民族价值的崇高力量。
化景为人:战争风景与崇高画意
红色电影里壮美辽阔的山水,其本身就构成了英雄人物崇高精神世界的隐喻。我们仍以《英雄儿女》中“王成牺牲”的段落为例:影片先是用一个仰拍的远景镜头展现近处的岩石和远方高耸的群山,随后王成闯入镜头,站在岩石与群山的分界线上,成为整个风景画面的视觉中心。一方面,正如康德所见,真正的崇高总是呈现为一系列“感性形式所无法容纳”的东西,因此主体外部的自然世界总是在美学上被判定为“崇高”,它直接呈现为山川、河流、海洋等自然事物在数量或体积上的无穷无尽,即所谓“数学的崇高”。从这个角度看,《英雄儿女》在王成牺牲的影像段落中所使用的那些高耸的山峦可以凭借其巨大的、宏伟的体积形式,直接引发观众“崇高”的审美经验。另一方面,从构图的角度来说,王成牺牲这一影像段落的视觉中心实际上并非那些宏伟高耸的山峦,而是点缀在远景画面中心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视觉构图令人想到《江山如此多娇》(1959)或《转战陕北》(1959)等同一时期的经典红色美术作品——不同于传统山水画中象征理想化秩序的自然山水,红色美术作品一方面竭尽全力地赋予自然山水以宏伟壮丽、难以征服的视觉形式,另一方面又让画面中的整个自然世界都臣服于主体的统摄,最终生产出一种革命意义上的崇高感。这样一种崇高感并非康德式的理性对有限感官和想象力的超越,而是能动的人类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征服,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不公的社会条件艰苦斗争的同时,人的目的也在和敌对势力、人类局限发生碰撞”,且“正是在人类战胜困难和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崇高”。因此,与绘画《转战陕北》屹立于黄土高坡之上的人物形象和构图方式如出一辙,《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身后高耸的群山和脚下坚实的土地都构成了他内在精神的外部显现——自然风景愈是壮美辽阔,画面人物的精神也愈是伟大崇高。不仅如此,在王成牺牲之后,影片立刻切换到了一组自然山水的大远景镜头:高耸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揭示了宇宙自然的恒常性,象征着英雄精神的永垂不朽。
这样一种用崇高而优美的自然风景展现战争残酷性的蒙太奇手法,令人想起同时期苏联的“诗电影”实践。例如,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导演的《雁南飞》(1957)同样是在主人公牺牲后立刻切换到白桦林的风景镜头,然而不断摇晃的镜头运动将白桦林的风景画面缝合进了主人公弥留之际的主观视点当中,因此白桦林实际上是主人公临死前所看到的实在之物。但在《英雄儿女》中,王成牺牲后的一系列山水风景并没有被缝合进任何人物的视点当中,它们并不指向任何实际的地理空间,而是引导观众在中国自身的诗画传统里寻找到风景对应的文化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样一种充满悲壮和崇高色彩的“化景为人”的做法,也时常出现在新时代红色影片中。从《八佰》到《金刚川》,从《长津湖》到《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牺牲段落同样营造了英雄魂归大地的崇高感,呼应了《英雄赞歌》中所唱的歌词:“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表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这些影片中的英雄避免了“三突出”式的样板化与“超人化”的表现方式,在人物塑造上更为有血有肉;另一方面,其牺牲场景也更为逼真和残酷,令观众更能沉浸于场景中并感同身受。同样类似于“诗电影”的表现方式,在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牺牲段落之后,影片往往以优美的音乐来提升作品的抒情性,使观众得到审美与净化。例如在《金刚川》的结尾响起谭维维所演唱的《英雄赞歌》,《芳华》(2017)在长达六分钟的一镜到底的残酷战场段落后紧接文工团表演《英雄赞歌》的场景(实际由雷佳演唱)等,这些场景中响起的《英雄赞歌》,不仅令“青山有幸埋忠骨”的崇高精神得以升华,而且作为红色经典的“回响”进入了新时代的影像中,带给观众以怀旧的力量。
这样一种借红色经典歌曲“化景为人”及“寓情于景”的做法,也常常让人想起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我的祖国》。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56年的红色电影《上甘岭》里:一组简单的摇镜头中,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们或端坐警戒,或擦拭武器,或缝补衣物,或阅读家书。接着,镜头停止了横摇,落在一名女战士身上,缓慢的推镜头将这名战士框定在了画面的中心。悠扬的乐声响起,画面中心的女战士唱起了歌谣:“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镜头随着悠扬的歌声再次横摇,坑道里的战士们深情地望向远方,同时合唱起《我的祖国》:“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顺着这些战士们的目光,镜头逐渐横移至坑道废墟外的天空,影片运用联想蒙太奇在蓝天中叠映出黄果树瀑布、华山绝顶、昆仑山脉、黄河壶口、桂林漓江等自然山水的远景。这些风景影像虽然有其各自的地理特征,但是当它们通过蒙太奇组合在一起时,却又再次指向了抽象意义上的“祖国”,一如革命山水名画《江山如此多娇》中对长城、黄河、五岳、东海等诸多景物的拼贴。由此可见,红色经典电影的山水影像虽然受到了苏联“诗电影”的影响,但却在具体的艺术表达和认知范式上呈现出与苏联“诗电影”截然不同的民族诗性。无论是画面构图,还是景物选择,抑或是剪辑方式,红色经典电影中的山水风景与同时代的革命山水画一道,总是试图在传统山水画的历史谱系中寻找可以承载其时代精神的风格形式和表达模式,建构起一种革命意义上的“崇高画意”:宏大壮美的山水风景往往并不指向实际的地理空间,而是主体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实践对象和精神象征。
在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由于拍摄技术(例如镜头、场景、特效等)的更新换代,导演往往可以使用大量的远景镜头拍摄自然山水,并将自然山水中的普通劳动者和战士置于远景画面的视觉中心。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展现战场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自然山水与画面人物的映衬和对比中塑造一种革命的崇高感。例如在《金刚川》的开头,几个大远景展示了朝鲜战场上的自然风光,并跟随一个推镜头和画面底部左侧的“一、士兵”字幕,观众看到隐蔽在树林中的志愿军战士;紧接着伴随一声“行动”的号令,远景中崇山峻岭间的战士们开始紧急行动,令画面将重点和中心还给了战士主体,而后无论是几个航拍镜头还是大量的运动镜头都强调了战士们“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力量感。这也呼应了红色经典电影中“化景为人”的塑造方式:例如在《英雄儿女》的开头,政委王文清在赶往大佛山的途中遇到了敌军轰炸遗留下的弹坑,影片以一个自下而上的摇镜头从中景画面边缘里帮助修理道路的普通民众出发,逐渐过渡为展现山川全貌的远景画面,使得原本处在画面边缘的普通群众被重置到远景镜头的中心。在最后的远景画面里,看似渺小的普通劳动者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一点点修复敌人留下的巨大弹坑——这既是普通群众改造自然世界的实践,也是他们征服敌对力量的英勇抗争。在这个远景镜头中,有限的个体借由战场上辽阔的山川风景,克服了自身的渺小和平庸,产生了崇高之感。
结语:红色经典电影的新时代“回响”
红色电影史上的“崇高身体”往往同英雄人物的塑造密不可分,这也形成了独特的视听语言形式及美学风格,尤其通过“化动为静”和“化景为人”的方式,而令英雄身体具有了仪式化、雕塑化和风景化等特征。通过分析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本文希望强调红色电影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即新时代的影片在主题、叙事、美学等各个层面都传承了红色经典电影的艺术精神,并焕发出新的光彩,展现出新的特征。
从《上甘岭》和《英雄儿女》,到《金刚川》和《长津湖》,这样一种在不同时代红色电影之间的重复、衍生、改编与再生,与其看作一种“影响”不如视为一种“回响”:作为一种“影响”,红色电影传承了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早已进入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血液之中,对普通观众具有深入人心的影响力;而作为一种“回响”,红色经典电影带来了当代艺术作品的回旋与激荡——这些文艺创作不断重复、回应、对照、发展、衍生与改写原来的经典电影文本,在传承“红色经典”精神的同时,也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性特征牢牢铭刻在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上。
红色经典电影在新时代的不断“回响”,实际上折射出当代多种社会力量、历史观念、美学追求、再现机制、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与时俱进的红色电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各种“当代化”的调整与改变,以使其能够更好地被当代观众所接受。红色电影的经典化过程,本质上既有故事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跨媒介改编,也体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影视工作者继承和弘扬革命文艺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承担起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识和使命,这本身也是崇高精神的跨时代体现。
*本文系2023年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新时代文艺崇高审美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编号:ZGWLBJKT202307)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文中海报、剧照来源于豆瓣网。
作者:陈涛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