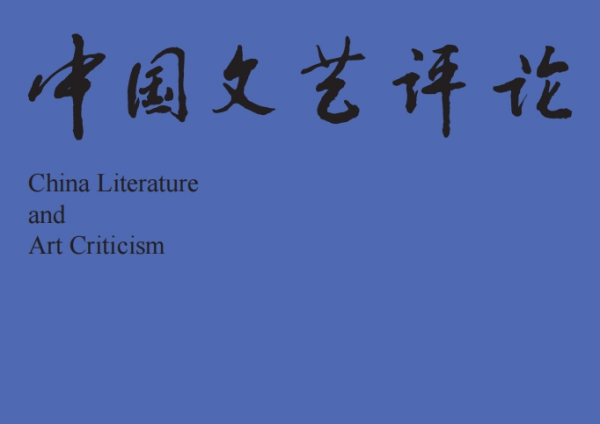
【内容摘要】 翻译常被视作一种单向的内容转换工作,即用语言B的词汇再现语言A中的信息。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这种将语言A的文本在语言B中重新呈现的方式可能在语言A中造成影响,并改变其面向原始受众的本义。虽然框架和体裁并非文本的固有部分,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如何被理解,而框架和体裁也往往取决于译者的选择。本文分析了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四书》中的三部作品翻译为拉丁文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翻译内容与翻译的框架和背景相互作用:译者希望将孔学作为礼物献给法国国王,但因此不得不淡化孔子对专制统治者的批评。结果,他们掩盖了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典型甚至至关重要的特征——谏诤。
【关 键 词】 翻译 修辞 孔学 传教士 跨文化对话
翻译是一种文字工作,但并不仅限于此。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拿出汉语中的一个词、一个句子或一本书,再找到英语(仅为举例)中与之语义相近的词、句子或书,并将其作为汉语词的等义词或替代词,那么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翻译就是一种单向行为:从我们所说的原语言,翻译到目标语言。然而,这种传统理解虽不无道理,但却未能揭示出翻译活动的全貌。翻译的过程中还会有其他事情出现,而本文旨在对翻译过程中的这些“其他事情”进行考察。
实际上,翻译并不是对原文的一种复现,而是利用另一种语言对其进行阐释。这种阐释遵循我们所说的译入语的规则——无论是明面上的还是默认的——来对原文中的信息进行梳理、分类和重组。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新阐释可能会再对原文产生影响。我认为,翻译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塑与重构。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类型差异。以《论语》为例,它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关键的文本之一。在传统的中国,这部书承担的角色是如此多样化,以至于难以将其归类为某一体裁或用途。《论语》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无论是田间劳作的农民、挥毫泼墨的诗人、权倾朝野的宰相、风尘女子还是绿林好汉,人人都能引用其中的语句。
然而,当《论语》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它就失去了那种优势,而且不得不被归入一个特定的类别,好让读者来了解这到底是一本讲什么的书。在以欧洲语言首次出版时,《论语》被称为是一本哲学著作。1687年在巴黎出版时,此书被命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家孔子”这一称谓仍被广泛采用。
显然,哲学家一词承载着独特的文学与制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时期。在《理想国》和《斐德若篇》中,柏拉图将苏格拉底描绘为一个热爱智慧、追寻智慧、但未必完全拥有智慧之人。智者,即智慧之人,总是站在权威的立场上发言,他们致力于阐明理论,并用证据加以证实。而苏格拉底对智慧的可得性持有怀疑态度。对他来说,追寻智慧中所特有的检验和质疑的过程,比智慧本身更重要。16世纪,当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耶稣会士远赴中国,开始深入研究经典之时,他们发现,许多中国古代“圣贤”也秉持着类似的观点。例如,《论语》有云:“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即强调无论是否能“及之”(获得知识),“学”(学习的过程)都是有价值的。耶稣会士还注意到,某些中国作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的思想在许多知识领域都被视作具有普遍的效力,而不仅仅只适用于某一特定领域。基于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哲学家”这一称谓,赋予那些和欧洲历史上的人物扮演过相似社会角色的人。在欧洲,自古被称为哲学家的人,必是一个勤思、善思、博思之人。因此,孔子被称为是“中国的哲学家”,而不只是“中国的老师”“中国的历史学家”或“中国的编者”。
此外,在17世纪,自然科学和数学均被归入哲学的范畴。因此,各学科皆可冠以“哲学”这一宽泛的头衔。哲学的领域一面与国家相邻,另一面与教会接壤。如果一个人被指控发表了危险的学说,他可以辩称自己并未涉足政治或神学——这些领域都是由体制内的专家严格把控的——他只是沉浸于哲学的思辨。举个例子,对伽利略和斯宾诺莎而言,尽管这种方法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总是奏效,但总归是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脱身途径。
而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会需要把孔子归入一个范畴,以避免其思想与国家或教会的权威产生竞争。对后者而言尤甚,因为罗马教会十分怀疑利玛窦试图通过创造一种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体来迎合中国人的情感。在中国,孔子和其他圣人所受到的祭祀,似乎意味着这些凡人被视为神明信仰。这是一神教所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在那种拥有三位一体和众多圣徒的宗教体系中也如此。为了避免这种思想冲击,有必要将孔子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一个人、一个具有人性光辉的老师,且并未对神圣之域提出任何主张。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接纳一位新的哲学家总归是有余地的;但如果试图将某人视为神祇或先知,则不太可能。
对于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人而言,罗马人所说的这些“哲学家”“圣人”和“先知”之类的范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天主教权威与中国君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天主教徒陷入了两难困境,这些原语言中的含义便凸显出来。国家言:“你须敬你的先祖,圣贤与君主。”教会说:“你不可崇拜任何此世之物。”于是,中国礼教的危机浮出水面。对此,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事实上,这场纷争很大程度上是翻译造成的问题,它将一种语言的范畴机械地套用在另一种语言之上。若能阐明这些分歧只是基于对文本、实践和现实的不同阐释,并非在于文本和现实本身存在对立,也许会有所帮助。但我怀疑双方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他们的实践和现实仅仅只是阐释的结果。
在汉语和拉丁语的语言领域,还潜藏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欺骗。罗马教廷声称利玛窦关于中国人的说法是一个谎言,即他们对孔子的尊崇只是世俗的和非宗教性的;他们称利玛窦欺骗了信众,让他们相信可以同时在世俗和宗教层面尊崇孔子。中国的官员们亦抨击耶稣会的主张为谎言。耶稣会认为自己完全是在从事精神范畴的活动,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且其门徒依然忠实于帝国。能够识别欺骗,意味着能够辨别真实的事态,并指出他人用语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欺骗行为,那么识别它至少需要三种知识:原语言的知识、目标语言的知识,以及两种语言所涉及的现实和实践知识。这无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但我想,从此事中吸取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而非只局限于历史范畴。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冲突距离我们现在的时代和思想状态已然十分遥远。至于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互译细节,无论这些翻译是否忠实原义,大抵也不会引起许多关注。但是,我们须看到,这些冲突矛盾所揭示出的一个关于翻译行为的事实,那就是:翻译创造关系。它是一种超越文字本身的力量,引导译者在众多词汇中作出选择。当天主教教义被翻译成汉语时,正如儒家学说被翻译成拉丁文,一种关系随之建立——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友谊、竞争、敌意、公平、不公正、诚实、欺骗、忠诚、钦佩、不敬、赞扬、指责……可以说是覆盖了所有的道德和感情。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翻译对词句的选择产生了双向的影响,即使是在那些不会说对方语言、只能通过第三方翻译进行交流的群体中亦是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翻译的互动维度,即翻译对原文及原义的反射或回归行为。
让我们将视角从宏观层面转向具体例子:如果你对修辞学和外交学感兴趣的话,1687年出版的孔子学说的拉丁文译本定会让你觉得非常有趣。这本书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全名,包含了精心编纂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精修版本,谨献给路易十四——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众所周知,路易十四的王权专制理论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也需要路易十四的支持——这是一项数目巨大的拨款申请。因此,他们深知不能疏远他们的赞助人路易十四。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论语》提出的一些观点却与他们的目的相悖。因此,就像历史上外交翻译官经常做的那样,耶稣会士介入其中、对孔子原本坦率坚定的言论进行了微妙的修改,令意思更加委婉,结果却令人发笑。以《论语》第12篇第24章为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乡亲们都喜欢某某,怎么样?”孔子说:“我还不能赞同他是好人或可亲之人。”子贡再问:“如果村民们都讨厌他,那又如何呢?”孔子说:“我仍不能赞同此言。更好的情况是,乡邻中的好人都喜欢他,不好的人们都讨厌他。”(笔者翻译)
《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相应段落是这样写的:
çu cumquaerit dicens: Si populares omnes gaudeant quopiam, quid tibi videbitur? Confucius respondet: Necdum id sufficit, ut certi quid de virtute ipsius sapientiaque statuatur. At si populares omnes oderunt quempiam, quid de illo tibi videbitur? Confucius ait: Hoc quoque necdum sufficit. Longe melius tutiusque si popularium probissimi quique gaudeant illo, et si eorumdem improbissimi quique oderint illum. De hoc ausim tutò affirmare virum esse probum et sapientem.
子贡问:“如果老百姓都喜欢某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孔子答:“这还不足以让我判断他的德行和智慧。”子贡又问:“但是,如果老百姓都憎恨一个人,在你看来又如何呢?”孔子答:“这仍不足够。如果老百姓中最好的人都喜欢他,最坏的人也讨厌他,那才是最好最安全的情况。彼时我才敢断言,他是一个善良而睿智的人。”
当然,译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扩充。它增加和填补了一些内容,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汉语中这段话可能存在假设或隐含的内容。我注意到译文中增加了一些具有法律内涵的词汇,这使得孔子的形象仿佛转变成了一位法官,他依据呈上的证据来做出裁决。譬如,“sufficit(足够)”“statuatur(确定)”和“ausim tutò affirmare(我敢肯定)”等词汇的使用,使对话不仅旨在分辨被讨论之人的品质是好是劣,更是一场达成判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去仔细思考这些被提交的证词质量:这些喜爱或憎恨当事人的人们,本身是否品德高尚,值得信赖?对某个人的判定会扩大范围到对一个更大的社会——起码有一个村庄之大——的判定。这其中是否有人的品质优秀到可以去判定别人是否优秀呢?在这种社会中,评判无处不在,对一个人的评判变成了对这个人邻里以及这些邻里是否有资格评判这个人的评判。
在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子》这部书时,这些外交官们表现得十分谨慎小心。对他们来说,这段文字因只涉及一村之事,似乎并没有显得特别敏感。但另一段围绕着“善”与“不善”的文章,却让译者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如《论语》第12篇第15章所言: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问:“是否存在一句话就能使一个国家昌盛起来?”孔子答:“一句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过,人们有一种说法,叫做:‘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一个统治者知道这种为君的难处,那么,这不就是只靠一句话让他的国家繁荣昌盛么?”定公再说:“是否有一句话可以令一个国家灭亡?”孔子答道:“一句话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不过,人们也有种说法:‘我不喜欢做君王,只是喜欢坐在王座上时,无人敢违拗我说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话是好的,那么无人反对不也很好么?但是,如果统治者的话不好,却无人反对。那么,这不就是用一句话毁掉他的国家吗?”(笔者翻译)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本一如既往地冗长,我将全文抄录在此并翻译:
RegniLuRegulus undecimusTim-cumdictus percontatur unum verbum, seu axioma brevissimum, quo possit erigi, seu efflorescere Regnum aliquod. Daturne hoc? inquit.Confuciusrespondit: Verbo nequit huiusmodi res sanè magna & operosa ita facilè determinari; conabor tamen brevibus complecti multa.
Vulgi proverbio dicitur: Agere Regem difficile est, agere Ministrum Regis non est facile.
Atque si Rex probe intelligat quod agere Regem reverà difficile sit; eam procul dubio afferet curam & vigilantiam, quâ et coeli et suorum gratiam & amorem mereatur & conservet. Nonne hîc igitur utcumque determinatur in unico veluti verbo, id quo erigatur & efflorescat Regnum?
Idem Regulus rursum ait: Unicum verbum quo pessumdetur Regnum, seu, quo explicetur id quod Regnis solet esse exitio, daturne etiam illud?Confuciusrespondet: Verbo item, nequit, eiusmodi res, quae summa malorum est, ita facile determinari. Vulgi proverbio dicitur: Ego non gaudeo, nec opto agere Regem: quod si agam, tum certè vehementer opto obtemporari meis illis verbis atque edictis Regiis, atque neminem omnium mihi adversari.
SubsumitConfucius: Si ergo haec imperantis verba bona sint, et ad aequitatem, publicamque utilitatem accommodata, & quibus adeò nemo sit omnium qui adversetur, nonne reverà praeclarum hoc erit, raraeque felicitatis? Contrà verò, si verba imperantis non bona sint, nec cum aequitate & utilitate subditorum conjuncta, & tamen rursus nemo sit omnium qui adversetur, qui arguat malè imperantem Principem; nonne jam determinatum habebis unico propè verbo id quod evertat Regnum; seu, quo contineatur exitium regni. Etenim sicut malis non adversari, pernicies Regnorum est; sic non adversari bonis, eorumdem est quies et firmamentum.
据说,鲁国的第十一任国君鲁定公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一句话或者一条精辟的箴言,可令任何国家兴荣昌盛?有这样的说法吗?”孔子答道:“这么重大艰巨的任务,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明白的。但我将设法用简短的几句话表达更多的意思。
“人们有种说法叫作:‘为王难,为王之臣不易。’
“如果一个国王充分了解做国王的艰难,他无疑会对这份职责抱有敬畏之心,并以此来获得和维持上天与子民对他的感谢和爱戴。那么,这不就是用一句话决定了王朝的振兴繁荣么?”
鲁定公又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使一个王朝灭亡,或者可以揭示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原因?有这样的说法么?”孔子回答道:“世间并无一言既出便国破家亡的谶言。但人们有种说法,叫作:‘我不喜欢做君王,也不愿意去做,但如果我必须承担此重任,那么我将明确要求大家要服从我的命令和敕令,任何人都不得违背。’”
孔子补充道:“这样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话是明智的,且合乎正义和公共利益,无人反对,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祝且难能可贵的事吗?但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的话并不明智,既不合乎正义亦无用于民,却无人反对这话,无人敢声称君主是一个不贤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我们就找到了足以毁掉一个王朝的一句话;或者说,这句话可能埋伏了亡国命运的伏笔。因为若不去反对不当之举,便会危及国家,那么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就在于不去反对好的措施。”
这段话被认为是对孔子言论的“补充”,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固执己见的君主的批评力度。在汉语文本中,重点强调一个不容忍任何异见的君王所带来的危险:正如《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所警示的那样,这样的统治者终将导致他的王国走向毁灭。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认为“孔子补充道……”的这段话出自张居正的评注。已知耶稣会之所以采用了张居正的注释,是因为它更为口语化且表意明确。然而,当看到这句评注时,你会发现其中更多表达了对拒绝听取直臣谏言的统治者的强烈谴责。
今时人有言说道:“我不是喜乐为君,只是为君时随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无敢违背,此乃其所乐也。时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从,固无敢有违者, 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于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岂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损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祸,社稷必为之危,而国不可以为国矣。然则唯言莫违之一言,岂不可期于丧邦乎!”
现在人们有种说法,叫作:“我不喜欢做统治者,只是我当政的时候,我一发话,所有的臣属都必须遵命而行,无人敢反对,这才是我的乐趣所在。这些人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情况。虽说君命臣从,人莫敢违,但是,这也取决于君命究竟如何。如果君命贤德,对老百姓有益,对国家生活亦有帮助,那么每个官员自当遵从并付诸实施,没有敢违逆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家得以太平安定,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但是,如果君命不贤,祸乱生民,动摇社稷,官员却个个都谨遵君令,不敢违背,那么老百姓必遭困厄之灾,国家将临危亡之关,到头来国而不国,家不成家。因此,(纵观前事来看),‘人莫敢违’这句话岂不是指向国家的毁灭吗?”(笔者翻译)
孔子说得更加直白:“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如果君命不善却无人反对,这难道不是以一言毁一国么?因此,国家需要拥有远见卓识、不畏上命的官员。在孔子看来,臣民应当享有直言进谏的权利,用西方的说法,就是要坚持保护举报者。他绝不会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同流去跳“忠字舞”。但译者们在孔子倡导忠言直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段话,声称统治者本质上总是正确的。反对统治者“善”的诏令会危及国家的和平安定,其蕴含的危险不亚于统治者无法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之“恶”所带来的后果。从这些译者对孔子原意的调整来看,赞同君主的言论成了理所应当,不赞同君主则被视为例外。基于这种改变,孔子的论述中平衡“善”与“不善”、“不违”与“违”的对称性被消解,而且是译者刻意如此的结果。法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国王从始至终主宰着语言的空间,而译者们所添加的这一段恰好表明了当权者被质疑的价值所在。除非特别鼓励和保护批评的声音,否则国王的话语将掩盖一切异论。尽管那段附加段落的真实性存疑,但确实向路易十四传达了他所期望的信息:当他发布敕令时,这是一件“值得庆祝和难能可贵的事”,因此这些命令自然是英明的,无人反对。如果他偶然听取了下属忠诚的谏言,那也是出于国王的恩典和仁慈。彼时,王室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分享正成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选择,耶稣会的译者以这种方式为专制主义背书,便失去了一次对17世纪西方政治理论进行有效干预的机会。
在我看来,翻译本身就隐含了一种批判性,因其改变了参照体系。在原文语言和世界中有意义的存在,对另一种语言体系和世界的读者来说则并非如此。通过翻译,我们可以通过探索局限性来界定我们母语参照体系的存在。那些惯于独断专行、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的统治者们或许也能从中获得启示:倘若总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他们对现实的控制就会松懈,就会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以至于给臣民们带来恶果。忠言逆于耳,然利于行。若批评不存在,那么赞美亦是空洞的。但是,出于安抚权势者的需要,批评常常被隐匿,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发掘和阐述才能被传达出去。耶稣会翻译的《论语》便是一例。这一文本在后世引发很多评论。这些评论全然无视译者对专制君主的奉承姿态,反而从这位“中国哲学家”身上重新挖掘出一些议题,如天命从不堪重任之人转移到可堪大任之人手中,凡人在没有超自然认可的情况下获得美德的可能性,以及官员有责任坚持直谏之举,以使统治者保持正直。
中国历史上,学者勇敢地与权势者针锋相对的那段过往,正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例子。而那些学者和官员因被贿赂或恐吓而保持沉默的时期,则不值得借鉴(除非是作为一种警告)。中国的文学和政治哲学,乃至一些最久远的国家结构,都源于统治者和他们的臣子之间的张力。中国文化之核心活力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这种行政权与谏议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充分展现臣子角色的复杂性。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君臣对话揭示了许多关于政治行为本质的关键问题:从臣子们试图驯服统治者的意志,到相对开明的君主渴望从绝顶聪慧的臣子那里获得最新的治世良策;从远见卓识的原则与修辞技巧之间的交织博弈,到屈原所遭受的“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以及苏轼为直言不讳所付出的代价,我们都能发现它的存在——而这些不过是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一些例子。而压制孔子关于“不善而莫之违”之害的警示,则并非是对路易十四或那些渴望了解中国思维与生活方式的欧洲读者真正好的做法。
* 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Haun Saussy于2024年8月6日参加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美国休斯敦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评论话语建设中美双边研讨会暨《中国文艺评论精粹(第一卷)》出版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Translation Goes Both Ways的主旨发言。本文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美] 苏源熙(Haun Saussy) 单位:芝加哥大学
译者:邹理 杨嘉宜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王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