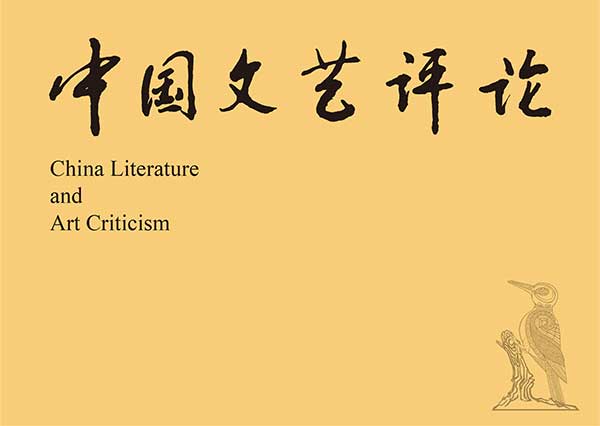
内容摘要:诗歌作为人类文学史上起源最早的一种文体,具有穿透读者灵魂的强大艺术“感染力”。诗歌语言和形式创造对于新诗有重要意义。所谓形式美,指的是音乐美、节奏美乃至分行美等。要实现音乐美及节奏美,就对诗歌语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关 键 词:朱光潜 新诗 诗歌语言 形式创造 形式美
诗歌作为人类文学史上起源最早的一种文体,较之后来的散文、小说、戏剧等,可以说最接近人类的灵魂。更干脆一点说,诗歌是距离诗人灵魂最近的一种文学话语形态,当然,优秀的诗歌也能及时融入读者的心灵,读者与诗的互动,其实就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汇与融合。读者能在优秀的诗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乃至哀愁,恰证明诗歌具有穿透读者灵魂的强大艺术“杀伤力”。
在西方,纵然发生过柏拉图驱赶诗人的误会,但诗人享有的地位一直至高无上,诗人一度被誉为是神的代言人,是为哲学命名的人等,但丁、歌德等就是铁证。在中国,诗人的地位也同样倍受推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等等,在读者心中不啻于远古圣人,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正因为诗歌拥有这样一种神圣的地位及其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后世的诗歌创作一直长盛不衰,尤其新诗的崛起与繁华,更是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但浩如繁星的新诗创作及其传世的作品,也并非都是经典之作,在不计其数的现当代诗人中,许多诗人仅因为一两首诗的出名,便让汗牛充栋的大量平庸之诗也跟着大行其道甚或传世了,因名而文,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恶性循环,此当别论。
也就是说,新诗并不容易写。笔者十分认可一种说法,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新诗的写作难度最大。朱光潜先生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的书信体随笔中,真诚地奉劝青年朋友不妨多练习散文、小说,认为把才华浪费在新诗上实在可惜。这位美学大师认为新诗的“生存理由”在于诗人“应该真正感觉到自己所感所想的非诗的方式决不能表现。如果用散文也可以表现,甚至表现得更好,那么,诗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了。”[1]朱先生还认为新诗比旧诗难做,他指出:“许多新诗人的失败都在不能创造形式,换句话说,不能把握他所想表现的情趣所应有的声音节奏,这就不啻于说他不能做诗。”[2]由此可见,侍弄新诗是多么不易!
笔者又由此联想到集诗、散文、翻译于一身的台湾大诗人之一余光中先生谈诗论学中的某些说法与朱光潜先生“新诗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疑,余光中先生也深受英国湖畔诗人的影响,故此他非常推崇柯尔律治(又译为柯立基)的一段著名论断:“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3]单就诗学理论而言,中西方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在用词讲究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诸方面,中西诗歌互为渗透之处也不胜枚举。
中西方许多诗学理论似乎都被朱光潜先生用“精妙”一词予以高度概括了。朱光潜先生说:“诗是否容易做,我没有亲切的经验,不过我研究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得到的印象来说,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这两种精妙都绝对不容易得来的,就是大诗人也往往须付出毕生的辛苦来摸索。”[4]朱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精妙”之造诣,无疑正是让中西方众多诗人难望其项背的艺术之赜,自然也是让一切诗人攻坚犯难之要塞。
如以朱光潜先生自己的诗论来阐释“精妙”之内涵,就是形式创造,形式创造自然又离不开精妙的观感并用精妙的语言来表现,这或许就是诗歌令人敬畏的难之所在。
“精妙的观感”又如何得之?朱光潜先生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理念,答案在于每个诗人的主观体验之中。以笔者之见,所谓“精妙的观感”应该就是指诗人某种内在的积淀与思考借助灵感某一时刻遭遇了外在世界的勾引而绽放,即获得了一种非诗不可表现的艺术发现,同时又需要获得同样“精妙的语言”付诸音画系统(结构形态),由此也就形成了形式创造。
可以说,“精妙的观感”与“精妙的语言”就是形式创造的重要前提。观之精妙又得之精妙,同时又能以精妙的语言呈现出来,这种精妙之妙,说说容易,得之可遇不可求。
顾城的《一代人》众所周知,广为传颂。但这首诗的确得之于作者精妙的观感又得之于精妙的语言,从而让它真的成为了一代人的共鸣。据诗人的父亲顾工回忆,这首诗就是在一种“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魂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5]

这种现象是否就意味着一种精妙的观感同时又获得了与之和谐匹配的精妙的诗语?但这种精妙的观感及其精妙的诗语,并非轻易就可得之。据顾工回忆,“文革”期间,他被打倒并被发配到农村去养猪,顾城随往,在那几年非正常的生活中,顾城整天埋头苦读,住房的四壁都被他涂满了诗。终于,有一天,墙壁上赫然出现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惊世之语。于是,一个黑色的时代造就了一个觉醒的诗人,或者说,一个缺乏精妙的时代却成就了一代诗人的精妙!
观感精妙,又匹配诗语之精妙,即便是顾城,也并非唾手可得。综观他的全部诗作,真正能达到精妙的诗作也是凤毛麟角。在他日后的创作中,虽然也不乏优秀之作,似乎再也没有哪首诗能超越《一代人》的“精妙”之“妙”。就像徐志摩之于《再别康桥》、戴望舒之于《雨巷》、雷抒雁之于《小草在歌唱》、韩翰之于《重量》,能成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对于每一个诗人纵然大诗人来说,一生中能拥有一二也就足矣。当然,也不排除古今中外确有精妙连连的诗人,近的不说,就说台湾杰出的诗人洛夫、余光中、痖弦、郑愁予等,在他们每个人的诗作中,能够赋予精妙标签的诗作绝非仅有一二,诸如洛夫的《边界望乡》、余光中的《乡愁》、痖弦的《秋歌》以及《我的灵魂》等等,都堪称饱含精妙元素的传世之作。

不过,或许观感之精妙,还是诗语之精妙,再加之形式创造之精妙,不是任何一位诗人都能望其项背的。或许朱光潜认为诗不好写,如所感所想非诗的方式不能表现当然应该以诗示人,如果散文也能表现而且还能表现得更好,又何以不用散文而偏偏要去冒诗之风险?
的确,当下所谓诗人诗作多如牛毛,多数为诗者并不懂得诗学尤其精妙之所在,以为诗既好写又好玩,就跟着起哄凑热闹,随随便便就来一首,管他是诗不是诗,有人跟着喝彩捧捧场也就满足了。也不排除确有一部分为诗者是出于一种内在需要而选择了以诗问世的方式,以充实自己的存在感。也就是说,是出于心灵深处某种积累的驱动,才选择用诗与当下这个问题世界进行碰撞乃至自我宣泄。如果属于这种情况,诗歌写得高下优劣如何,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诗离我们的灵魂最近,一首好诗的诞生,就是诗人跟自己的灵魂一场内在“搏斗厮杀”的产物。
诗歌之难,形式创造也是一大关口。纵然观感、诗语自我感觉良好,但一旦付诸形式创造,也是对诗人自身的诗艺素养的一大挑战。朱光潜先生之所以强调形式创造对于诗人表现情趣的重要性抑或致命性,无疑是因为朱先生深谙汉语言的声音与节奏是成就一首新诗的“霓裳羽衣”。所谓形式美,具体地说就是音乐美、节奏美乃至分行美等。这就对诗歌语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获取怎样精妙的观感及其精妙的语言,才能构成一首诗的音乐美及节奏美,这不完全取决于天赋乃至灵感,更取决于诗人的语言修养尤其对于汉语言韵律句法的了解与修为。如果表现情趣所应有的声音与节奏缺失,诗也就不成为诗了。倘若以这样的形式创造标准去衡量当下汗牛充栋的新诗,不知还有多少新诗能成为新诗?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以及痖弦的《秋歌——给暖暖》等优秀诗歌之所以能让人百读不厌且广泛流传渗透民间,就在于首先赢得声音与节奏的胜券,否则,即便精妙的观感有了,精妙的语句也有了,如声音与节奏不匹配,又岂能收到入心勾魂、朗朗上口的效果?新诗创作原理中所强调的抒情性作品的结构形态,其实就是强调听觉美与视觉美的统一,前者体现的就是音乐化效果,无论新诗旧诗,这一点是相通的,虽然格律诗更具有听觉视觉一统乃至诗画一体等优势,但现代新诗的形式美、音乐美也不可或缺。一首新诗的字里行间只有洋溢着生机勃勃的音响与节奏,又辅之以恰当的形式(即分行排行的恰当模式),读起来才能产生风生水起的艺术力量。

余光中先生曾经感慨当下读诗的人之所以少了,是因为当下的诗的确不好读了。许多青年诗人有诗情、有悟性,也不乏创造力,可就是语言素养跟不上,写出的新诗倒是新了,奇倒是奇了,但汉语言的韵味尤其音乐节奏感没了,于是,也就被读者抛弃了。
从没有以诗人自居的鲁迅先生,一度对新诗创造也情有独钟,他一向认为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只要顺口就好”。[6]可见,鲁迅也好,余光中也好,一谈新诗就一口咬定声音与节奏的要义。他们的新诗感言与朱光潜的新观点不谋而合,这就告诫那些盲从诗歌写作的芸芸众生,如果写出来的诗一点音响节奏感都没有,不如去写散文或小说,别让诗耽误了爱好文学的美好年华。
闻一多先生提出新诗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是中西现代诗歌所共享的。音乐美强调的就是语言的声音与节奏,绘画美强调的是视觉效果,建筑美强调的是分行与排行形式,显然,音乐美是“三美”中的核心理念。这些新诗品质不独为中国新诗所苦苦追求,西方现代诗人也同样会把“三美”视为现代诗歌的必备。从翻译过来的一些诗作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叶芝的《当我们老了》之所以能被谱曲歌唱,就证明西方现代新诗对于“三美”的创造更加精致。还有凯瑟琳•詹米的《蓝色的船》、华兹华斯的《咏水仙》、勃莱的《隐居》、萨福的《夜》、布莱克的《天真的预示》等都堪称舌尖上的音乐之作。诗画一体特征在西方现代诗歌中更是家常便饭。在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很早就赫然地推崇“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之说,叶芝的《茵纳斯弗利岛》就是一个有力的诠释,有诗韵、有画面,也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意境之美。
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那首闻名世界的《一个地铁车站》,仅有两句诗语: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白色花瓣”,可谓集精妙的观感、诗语以及“三美”于一体,无论是内容催生了形式,还是形式催生了内容,都证明朱光潜先生的新诗“创造形式”说对于中西创作都适用。这种精妙及其形式创造之美,得来并非那么容易。这首诗来自诗人偶然之间的精妙观感与灵性,但最终构成恰到好处的形式创造之完美,却经历了几番“炼狱”,在黑暗王国中苦苦探索了很久很久最终才获得一线光明。据诗人自己说,此诗一开始写了三十多句,不满意,就反复左奔右突、大刀阔斧,砍杀掉了一片又一片“语尸”,最终才凝练成两句短诗,前一句写实,后一句写虚,自觉得内容与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公开发表之后,很快名扬世界诗坛。庞德一生写诗无数,似乎没有哪一首诗的影响力能与之相提并论。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精妙的观感与诗语来之不易,就是大诗人也往往须费毕生辛苦去摸索。精妙的观感与诗语许多时候可遇不可求,也正如余光中所言,诗人往往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神龙见首不见尾。其精妙的观感与诗语似乎也就是在这种颠颠狂狂中偶尔得之,是天赐之,还是自我癫狂中不请自到?恐怕连诗人自己也说不清。
现代诗歌之所以让很多智者望而生畏而不敢亵玩,就因为新诗的精妙不易得、形式创造也难得定型,怕误了自己,也误了读者,如此,倒不如记取朱光潜先生的奉劝,对生活中的所感所悟并非非诗不可表现,如散文也可表现又能表现得更好,又何必要在诗歌的精妙与形式之难中无限“炼狱”且耗尽青春才情呢?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