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解读为例
由北纬30度的“轴心时代”说开去
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次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同时出现在北纬30度左右地区的人类文化与文明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自此,人类真正从历史的蒙昧中走了出来,开始形成各自的文明体系,尤其是文化与哲学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走向。此次论及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带便位于北纬30度这条纬线之上。
作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主要分为四期,一期属于新石器晚期,二到四期属于青铜文化时期。由于其时间长达2000余年,而且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而且,该遗址已具备考古学家夏鼐提出的考古学文化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三是“必须对于这一文化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换言之,在所发现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须至少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便了解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参考: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总34期])
时至今日,“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话题已成显学,不再局限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书斋”研究范畴之列,有着更加广阔而多元的叙事空间。甚至,对“三星堆”的考古与历史讲述,可以当作是“大众史学”的一部分。
艺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之下,不同于过去单一的媒介研究,“跨媒介性”作为一种“重构”与“统一”的艺术跨界研究(模式)形式,被纳入到多种艺术史研究的话题场域之中,并在不同的话题、不同媒介之间产生了广泛的联系,这意味着艺术史研究的转型,必然导致其叙事性方法的转向,乃至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学术性构成也会相应外延。

三星堆青铜人像(图片来源:新华社)
随着三星堆遗址艺术考古器物层的深度发掘工作展开,发掘过程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多种学科配合实现的综合纬度的深入考古,以及三星堆文物走进博物馆、走进文化节目的故事性推荐,到人工智能模拟场景“复刻”三星堆古蜀人生活等等,更是引发了国内艺术史学界以“跨媒介性”视角讨论与书写艺术历史的热度。由之,通过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解读,可以直观地认识到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轨迹”。
三星堆的特点与新发现遗迹解读
针对艺术考古与考古的区别需要进一步明晰,这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研究的区别:考古,注重于解决出土文物的定性问题,通过研究确定其在历史时空中的定位。艺术考古,则更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的资源,使之为当下艺术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文化与艺术的资源,尤其是直接转化为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弥补整个艺术学领域研究的空白与不足。目前,这一认识还不足,仅仅当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提升至整个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指向。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左图)三星堆象牙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4号“祭祀坑”内清理象牙(右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以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为例,这些“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更是不乏许多重要的发现,如在三星堆4号坑的灰烬层中,在首次提取出丝蛋白后,考古工作者又通过检测1号坑至6号坑提取的逾百个样本,在2号坑和6号坑中再次发现纺织物的遗痕。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且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丝绸蛋白,表明距今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王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而专家还在1、2、4号坑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朱砂。据考古学者推测,这些文字或符号或许附着、书写在漆器、木器、丝绸等上。也就是说,丝绸或是古文字的物质载体。更进一步,丝绸残留物存在于高层面的祭祀坑,代表这是天地人神相互沟通的一个地方,说明了丝的功能提升到了精神层面。此外,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中,还发现了新的象牙遗存。而此次对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进行保护和研究,有望勾勒出当时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揭示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和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参考:《惊喜不断,三星堆文物出土进行时》,《光明日报》2021年05月31日09版)
综上所述,三星堆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具体表现,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三星堆遗址既是一种宝藏,也是一种资源。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需要我们不断去研究和开发利用。
“跨媒介性”认知,有助于突破史学研究的“路径依赖”
根据西方学者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和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编写的《媒介考古学》一书,可以提炼出“跨媒介性”的相关认知,其中首先是“适应性预期”,这是随着“跨媒介性”介入艺术史学研究而形成的认知,即面对研究领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矩阵相互联系网络,借喻是说考古资源的网络化处理,被完全数字化后进行各种复杂的运算而产生的递增信息,从而决定研究轨迹需要持续保持这种“适应性”效能。
研究范式发生变化导致研究视域拓展可能性增加。诸如,借助“跨媒介性”的手段,可以演进出更多的范式形态,可以是视频纪录短片、或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情境再现”,以及图文互解等,构成跨媒介与跨文本研究在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有自我消化、自我筛选的知识重组的功能,这使得在对待新的研究范式形态时,尤其是带有可选择、跨越性质的“跨媒介”研究范式时,自然会阐发出不同的学术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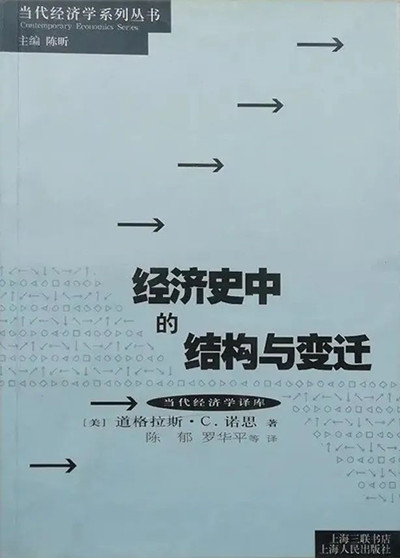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突破研究的“路径依赖”,在“跨媒介性”的研究中应是合理的主张,这是借用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1920-2015)提出的“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来解释相关史学问题的尝试。如此对照,一个史学者得出一个或多个结论指向时,便是在不同知识环境中形成的不同主观抉择。这种差异性,恰恰是能够促使研究产生多元共创的理论,且保持学术机制长期生命力的原因,这更有助于突破自己熟悉研究领域的“路径依赖”。
“跨媒介”重构三星堆文物考古的物质文化属性,引发艺术史研究新思考
2021年3月20日,在三星堆发掘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考古专家重点介绍了此次在3号祭祀坑中出土两口尊,从两口尊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的联系。其中“跨媒介性”研究引发的思考,就是要复现艺术史研究多样性视域的可能性,即借助文物、考古报告、图片与图像档案,将媒介还原为可触、可感的新的“媒介物”。以往媒介研究多将媒介视作一种既成的技术,只是用于考察文物发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的功能性作用。而媒介考古学则认为,不能脱离设备、系统、编程、平台等物质基础而侈谈媒介之运作机制或权力关系。


2021年4月12日,圆口方尊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成功提取,这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完整首件圆口方尊。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款方尊。
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中发现了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且在样土检测中又多次发现蚕丝蛋白,这基本可以证实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属地已有使用丝绸的实证。而最有力的证据是,8号坑出土一件青铜残片上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而三星堆的丝绸残留物发掘,还意味着与青铜器、丝织物、蜀锦形成的诸多关系。(参考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的《考古札记:三星堆遗址,于“无形”处寻丝绸》)
由之,针对艺术史的跨界贯通,挖掘具有跨媒介属性的艺术考古实证,可以透视出史述叙事的独特之处。艺术考古同样借助“跨媒介性”研究的多种方法,形成有效尝试。诸如,丝织物的出土挖掘,考古学家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它周边的土壤,推测其年代;而艺术考古学家则从丝织物的出土,推断其文化层与历史特殊时段,并结合人文、历史,包括陪葬位置,作出全面的史学评估。

图:8号坑日前出土一件青铜残片上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文化技艺”介入“技艺时代”:艺术史的“跨媒介性”研究
媒介里“文化技艺”概念被引入到“艺术-技艺”考古之中,从而促成艺术史的“跨媒介性”这一研究话题,即艺术考古要站在出土物的社会、文化、风俗、技术水平等多维度历史空间中,借助考古学、纺织学、科学等跨媒介性手段还原“总体艺术作品”。
例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和纺织物遗痕探寻,可以说与古代工艺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对古代“织物遗痕”的考察。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一门新兴学科——纺织考古学,属于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纺织考古学又构成艺术史特有的“跨媒介性”实证资源。随着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江西德安周氏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福建福州黄昇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辽宁省叶茂台辽墓、新疆山普拉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葬群、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等墓葬纺织品文物的出土,以及随之开展的清理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历代服饰文物实物链,是以这些早期艺术考古研究工作,也奠定了古代服饰研究的基础。可见,艺术考古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证,也是研究的重要命题,可谓大有文章可作。
当然,科学技术在艺术考古中的应用也是“跨媒介”研究方法的应用手段,也是十分突出。比如,在三星堆遗址科技考古装备的研发过程中,已经形成了30多项专利申报,包括约10个发明专利和20多个实用新型专利。事实上,关涉媒介考古学取证的话题,在近年来艺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领域已引起广泛关注,构成丰富的学术资源多样性的特质。比如,有学者提出,该项研究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有诸如新历史主义和新电影史等方面的研究。应该说,当“跨媒介性”问题的探讨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时,艺术考古与媒介考古学的融入,这些都是对跨媒介艺术史研究“轨迹”铺垫形成重要的支撑。
此外,“跨媒介性”艺术史研究必然突破传统艺术史学观念的依赖路径,拓展出不同的阐释空间。尤其是艺术史研究的推广,更是涉及多手段叙事。例如近期与三星堆博物馆联动的几款游戏:《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即将上线,纪录片改编的手游)、《消失的金面具》(即将上线,桌面考古游戏)、《全民奇迹2时空迷局》(已上线)等,不仅真实地还原了纪录片、博物馆中考古文物的形态,而且玩家在游戏中体验考古工作的流程以及难度,对文物进行清洁、抛光打蜡,并且收藏在玻璃柜里,趣味性促使玩家能够在游戏中了解到三星堆这个神秘的东方文明遗迹的历史脉络。

除了常见的文创、电影、图文、纪录片之外,三星堆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还见到了VR技术的身影,通过三维立体的全景展示,让寻常百姓也能“走进”场馆,与尘封的文物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对话。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以裸眼3D屏幕,透过生动的影像技术,向参观者呈现出世界各地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也从更广阔的视野为参观者理解三星堆青铜器提供思路。在“肃肃神宫”展区,首次展出了青铜神坛(残件),辅以多媒体手段,解读神坛的构造和内涵,让参观者看到复原后的神坛是什么样子。运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营构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意象。

重新建构史学“传主身份”,实现传主身份艺术再现
“跨媒介性”艺术史研究必然突破传统艺术史学观念的依赖路径,具有拓展阐释空间。尤其是艺术史研究的推广,更是涉及多手段叙事。诸如,与广播影视、数码网络,甚而以赛博符号、文化地理综合构成,并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以“游戏”为设计对象,以探索游戏中诸多历史情境与情节叙事为主题的艺术史阅读的延伸产品,这是重新建构史学“传主身份”,实现传主身份的艺术再现。
例如,以游戏手段再现三星堆考古、文物、场景等。一方面借助三星堆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实现自身游戏内容的创新升级,这是民族文化IP对数字文创的一种赋能;另一方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大众与充满历史感和神秘感的三星堆遗迹,来一场跨越时空界限的“对话”,这是对三星堆考古与历史文化的一种数字化、文创化的升级创新,两者的合作与碰撞,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合作,也是数字文创赋能传统文化升级的范型。“跨媒介性”艺术史研究必然突破传统艺术史学观念的依赖路径,拓展出不同的阐释空间。尤其是艺术史研究的推广,更是涉及多手段叙事。
诚然,“跨媒介性”领域的史学话语是非常多样的,有综合跨媒介性、形式/超媒介跨媒介性、转换跨媒介性和本体论跨媒介性,而这些研究方法所阐释的共同意义在于,使得艺术史研究正式从传统的、“纯粹的”以及“特定的”媒介存在中走出来,旨在探讨史学“传主身份”生成的动态过程,探讨建构“传主身份”的叙事策略,特别是揭示“记忆化历史书写价值传递”的动态过程,以新的视角衔接艺术史研究的新视域。(参考《三星堆“闯入”掌趣新游 数字文创赋能文化创新》中华网2021年7月22日)
参考文献
《华阳国志*蜀志》(方志)
陈德安主编:《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肖先进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田野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地出版社,2006年版。
《三星堆研究》辑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三联周刊/三星堆考古发现20年》专辑,2007年第2期。
朱家可、邱登成 编:《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9年版。
《三联周刊/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时代:三星堆、汉中、炭河里、盘龙城、新干大洋洲》,2021年第23期。
《国家人文历史/三星堆解谜进行时》,2022年第8期。
汤洪:《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试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14日。
赵昊:《我们在三星堆考古现场》,《人民日报》2021年5月13日。
李晓东、陈晨:《惊喜不断,三星堆文物出土进行时》(专题报道),《光明日报》2021年5月31日
周洪双、李晓东、李韵:《中国考古的当代故事——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专题报道),《光明日报》2022年3月18日。
(作者: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本文根据作者在“江苏省高水平大学高峰计划·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创新成果培育——研究生学术工作坊系列之二”线上讲坛的演讲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整理。图片来源:新华社三星堆新闻报道图片专辑;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古蜀国的神秘面具》,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