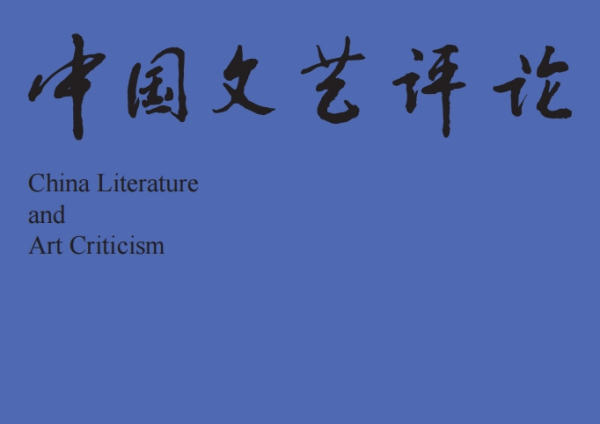
【编者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之义。而文艺作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力量和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媒介,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刊特推出“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专题系列文章,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中华文明标识艺术呈现的理论逻辑、实践意义、历史底蕴、时代品质、世界价值等,以期将这一重大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引向深入。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体认、比较与以艺术的方式
【内容摘要】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努力。首先,从本根处实现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刻体认,防止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其次,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彰显中华文明标识的世界性意义。比较是彼此带着各自问题而向对方发出的邀请,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再次,在艺术创造中实现中华文明标识的审美生成,最重要的是以艺术的方式,秉持对形式的最大尊重。最后,在阐释中实现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普遍性蕴含的提升。文艺批评家需要在贴近文本、细读文本、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考镜源流、追寻文脉、提升蕴含,实现艺术在跨文明传播中的本源性、敞开性和对话性。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
【关 键 词】 中华文明标识 本根 体认 比较 形式 普遍性蕴含
中华文明标识是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特点且具有人文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部分,包括各种物质文明标识、非物质文明标识、符号象征体系、精神性标识以及各种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命题等。它们构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和身份标志。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本根和比较的视野对中华文明标识的内涵、特征及其文化凝聚予以深刻的体认,努力做到寻根的理解与守正创新;另一方面,要在审美创造中实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生成,做到中华文明标识的思想蕴含、精神品质和审美形式的统一。同时,要在阐释中提升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形象的普遍性蕴含,向世界传达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形象。
一、从本根处实现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刻体认
“本根”原指草木的根,引申为事物的根源、根底、根本、本源、根由、根究等。《说文解字》释“本”的本义为树根,即“木下曰本”。树根深埋在地下,生长出树干、树枝、花叶乃至果实。树根虽埋于地下,却对树干、枝叶、果实的存在有根本意义。《礼记•礼器》云:“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王充把“根”引申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强调“根”对于文章价值实现的作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论衡•超奇》)韩愈也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的说法。相比于西方的本质论、本体论,中国语境里的本根论包含着对于事物根本性、本源性亦即本质性认识的强调。
对本根的重视和强调,是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特点。本根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本根里包含着万事万物始发、由自的讯息,万物皆从本根来。从本根处进入,可以获得对中华文明独特性、丰富性的“寻根”的理解。这里我们所强调的“寻根”作为一种思想和学术的方法,包含着对对象的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要求。中华文明标识的凝练与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沉潜下来,在深情地回望历史和眷注当下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特别需要在本根处问道求解,以获得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刻体认。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悠久灿烂的文明并以其可感、可触、可理解的方式散发出超越时空的迷人魅力。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华文明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标识是对中华文明根性、特征的凸显,是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也是在人为的构建中生成。无论是古代文明标识、近现代文明标识还是当代文明标识,无论是精神标识、符号象征还是各种物质文明标识和非物质文明标识,都应弄清其发生的缘由、生成的语境、原初的含义、流变中的意义增值,融入当下的时代价值。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标识既承载着从古至今的文明讯息,也具备启迪当下、引领未来的功能,需要从本根处领悟其超越时空的意义。哲学家张岱年强调研究中国哲学需从本根处考察其“基本倾向”,“基本倾向”即“基本假定,有的是明言的,更有的是默认的。默认的尤须辨识,而亦最难辨识”。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第一篇第一章为“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他认为“中国哲学最注重本根与事物之统一不离的关系,事物由本根生出,而本根即在事物之中”,此即中国哲学的“体用一致”观。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哲学那样在现象世界之外去寻找一个决定现象之所以存在的本体,用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对立方式理解中国哲学。张岱年还认为中国哲学人生论的基本倾向是“天人合一”的。“体用一致”“天人合一”遂成为中国哲学具有原创性、本源性和标识性的概念,由此带来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解:“中国本根论的根本趋向或根本假定之一,是认为本根必是超乎形质的,求本根必须求之于无形无质者中,无形无质而又非即是无的”,从而避免了对中国哲学想当然的理解,也克服了以西方观念和概念剪裁中国哲学的倾向。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但真正对中华文明标识的形成与阐释构成决定性影响的,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是一个各种思想形成、发展和交相辉映的时期,是一个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时期,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犹太教的先知,佛教的释迦牟尼以及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轴心时代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构成中华文明思想宝藏的第一座高峰,持续地影响了后世文化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走向。中华文明一些基本的理念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都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和讨论了。因此,讨论中华文明标识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标识,不能忽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轴心时代的思想更具有本源意义,值得特别重视。
今天,我们都在强调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特点,但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内涵和背后的宇宙观,在理解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着误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缺乏对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本根的把握,往往以想当然的方式规定了其中的内涵。如果不从本根处体认中华文明的特点,那么构建出来的中华文明标识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设定,远离了中华文明之根本。“天人合一”虽然没有在《道德经》里提出,但孕育这一命题的根本却逻辑地包含在《道德经》里。对宇宙本体的追问是《道德经》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如果不理解《道德经》的“道论”,那么也就很难准确把握“天人合一”观念,甚至会陷入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里。如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客观世界,把“人”理解为与自然界、客观世界对立的主体性的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主体、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这完全背离了中国哲学语境。因为“天人合一”强调的恰恰是未经分化的人“在”自然中的思想。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多歧义的概念。对“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不作寻根的理解,结论很可能就建立在不牢靠的地基上。
中华文明标识不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层面,而后者更具有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引领作用。那些构成中华文明标识性的概念,通常也是中华文明当中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与人文智慧的结晶,标识着中华文明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具备与世界文明对话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同样,中国共产党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通常用“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来标识。这些标识性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从本根处问道求解,可以避免文化上的急功近利,克服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需要深入中华文明漫长历史的腹地,探寻其起源、发生、演变及其动力机制,还要回到思想发生的现场,在对元典进行精研的基础上,找到理解中华文明标识的远古文脉和隐含讯息,使这些标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中的“守正”。没有“守正”,何来“创新”?没有厚重的文化依托,何来文明标识的现代传释?中华文明标识构建的意义,说到底是为了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维护中华民族认同,培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为了猎奇、展示,搜集一些内蕴浅薄、不具备实践意义和价值引领的文物标本,成为缺乏语境和基本规定的“漂浮的能指”。
二、在比较中彰显中华文明标识的世界性意义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构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的根性、特点和旨趣,终极目的是为当代人提供了解过去、关切现在和引领未来的价值关怀,并有能力为当今动荡的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特质的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应该具有面向全球的敞开性、对话性:一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根性、特点有清晰的了解,具备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二是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的现状及其走势有深刻的洞察,有能力从世界文明体系里汲取有价值的营养,并与之互动。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助力中华文明标识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方式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呈现出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与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过程与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中华文明才会焕发出吸引世界目光的力量。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市考察三苏祠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论述都强调文学艺术在发展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立足本土的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西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不容否认,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在反传统的浪潮里将目光投向西方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过程,是缺乏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支持的西化过程,这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化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缺陷。美学家叶朗谈到中国现代美学的尴尬处境时这样说:“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命题,基本上还都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吸收多少中国的东西。偶尔引用几句孔子的话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话,引用几句唐诗宋词,不过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引进中国传统美学的个别概念,但这些概念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这是因为整个体系是西方的,这种纯西方式的体系不可能真正包容中国美学(东方美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美学与文论患了“失语症”,所谓“失语”,当然不是没有了声音,而是指在一边倒的西化浪潮中失去了言说中国问题的能力,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丧失了阐释本土问题的效力,变得人云亦云、无所作为了。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在于“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也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化解本土现实与文化的焦虑汲取“他者”智慧,而不是封闭僵化、生硬模仿,甚至以西化中、泯灭自我。所以,要坚决摒弃那种不加思考、盲目接纳,把外国的东西奉为圭臬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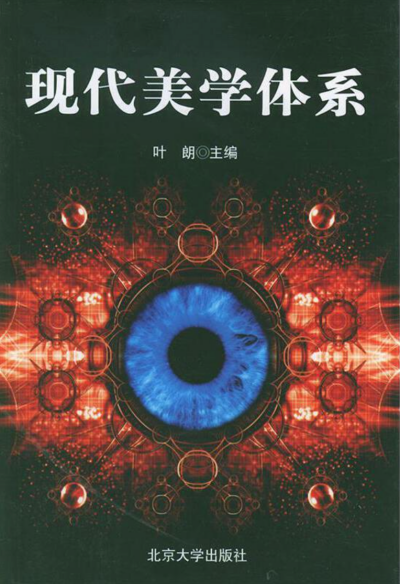
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
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文化上的不平等,也曾失去过文化自信。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是遥远的神话。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建设性的意识加入世界文明对话的行列,在向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学习的过程中也贡献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事实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带来了世界对本土的广泛影响,也刺激了本土对自身文化根性的反思。对自身文化根性的深入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他者”视野密切相关的,“他者”使我们发现了本土文化过去所不曾发现的新质。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东西论争”经常转化为“古今论争”的原因。这说明,比较从来是双向的:一方面导致外来文化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本土文化的自觉、生机与活力。
例如,中华美学崇尚言外之意,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刘勰用“隐秀”来说明,钟嵘有“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标识。中华美学的这些特征只有在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中才得以理解。同样,西方美学中的“象征”概念也只有在追求深度模式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内部才能得以说明。只有在对中西文化各自特性深刻认知的前提下,中华美学的“言外之意”与西方美学“象征”之间的“可比性”才会显现出来。但“象征”毕竟是经过理性和科学文化洗礼产生的成果,比起中华美学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等,更具备可以用概念清晰说明的特征。反过来,中华美学重经验、重感悟的言说方式,则以其丰富性、多义性和不可阐释性等,引发对西方“象征”之类的概念在阐释文学艺术时陷入的阐释学悖论的思考——文本意蕴的无限性和逻辑符号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引发阐释学的悖论。这种近于“视界融合”的认知,是在深入领会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征、对中西方美学精神作根本研究和把握的基础上实现的。法国一些汉学家将刘勰的“隐秀”与西方修辞学中的“隐喻”作对比,将“神思”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想象”作对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甚至将《文心雕龙》中的赋、比、兴、风、雅、颂,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六要素”作对比等。这些“比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比较”通向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识互证,培育了文明的富饶性。这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是中西方文化带着各自问题向对方发出的邀请,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而绝不是非此即彼、“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
比较还可以矫正西方对中华文明特点的一些误解。例如,国外一些汉学家通常把儒家之“礼”诠释为仪式主义,而忽略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情感,将“风骨”译为“Wind and Bone”(施友忠)或“Vigor and Structure”(杨国斌),将刘勰的“守正”理解为复古主义,而忽视“通变”中的创新性等。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矫正和超越西方话语的偏见,使中华文明标识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性。
我们自己也需要突破区域文化的单纯视角,避免将中华文明标识简单化、符号化。故此,比较永远属于“对话性阐释”,而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将“自我”本质化。
三、在艺术创造中实现中华文明标识的审美生成
中华文明标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来体现的。《诗经》、楚辞、汉赋、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以及近现代以来围绕启蒙和救亡产生的红色与革命文艺叙事、当代文艺中的人民叙事,都有力地丰富了中华文明标识的人文内涵和思想魅力。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及其塑造的形象,可以超越概念、逻辑表达的局限,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家园。《红楼梦》为我们塑造了琳琅满目的人物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向往,具有历久而弥新的人民性品质,成为百年来读者心中向往之地。其独特而鲜明的形象区别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也有别于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是进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桥梁和通道。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复杂性,具有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其标识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一大批在时代感召下应运而生的文艺作品,将中华文明标识的塑造和表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聚焦百姓生活,在洋溢着浓重烟火气的世俗生活中探寻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那种热爱土地、眷恋亲情、向往真善的百姓精神寄托,在丰富细腻的生活表情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电视剧《觉醒年代》《山花烂漫时》《问苍茫》《跨过鸭绿江》、电影《长津湖》《万里归途》等聚焦红色和革命主题,着力刻画体现具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先觉人物和英雄人物,将“为生民立命”这一传统文化熏染下的崇高信念与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誓言结合起来,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波谲云诡的现实交汇点上擎起民族精神的英雄火炬。长篇小说《主角》、民族舞剧《醒•狮》、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网络动画片《中国奇谭》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合当代审美意识,在视觉、听觉和跨媒介的叙事中,动情讲述中国故事,丰富中华文明标识的表征系统,实现了中华文明标识的思想性、精神性与感性、生动的形象塑造和精湛、完美的艺术呈现的统一。

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中华文明标识,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上做文章。艺术不是某种概念的传声筒,不能用“主题先行”的理念规约。从中华文明标识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经过不断的感悟、发现、浸润和升华,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群众“火热的斗争”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生活之于艺术十分重要,离开了生活,艺术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火热的斗争”只是创作的前提性条件,并不必然就是艺术。艺术在本质上是人按照理想的方式再造的“虚幻世界”,也就是“意象”。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只取决于艺术家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更取决于他对生活的艺术掌握程度,特别是对人生经验的审美开掘程度。
意象,是中华美学的一个富有标识性的概念,凝聚着中华美学对于艺术的独到理解。意象超越概念、超越逻辑,又是对概念、逻辑意涵的形象性承载。在王廷相看来,意象是诗歌的本体,有意象则有诗,无意象则无诗:“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王廷相对意象的理解,显示了中华美学对于艺术之非逻辑、非概念性质的深刻认识。意象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即“意蕴内涵其中的感性形式”。在真正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形式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形式不仅是内容的载体,也是艺术的本体,是此艺术区别于彼艺术的唯一标识。
在艺术长河中熠熠闪耀的文艺作品,其感性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19日,票房已破150亿元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塑造了哪吒、敖丙、申公豹、太乙真人、李靖、殷夫人、无量仙翁、土拨鼠等众多形象。《哪吒2》的火爆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哪吒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动漫语汇的高度契合,紧张惊悚、怦然心动的震惊体验与温情柔软、直逼人性的愉悦感深度融合。最终,成功实现了动漫艺术的人文蕴含与科技赋能的统一。据电影主创团队提供的数据,《哪吒2》单是特效镜头就多达1948个,超过了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1》)的1400个特效镜头。技术难度不断迭代升级,裂空爪撕裂天空、岩浆奔涌、海水倒灌、缠着锁链的海妖密集而惊恐的运动,都是特技效果下的形象塑造。试想,没有本质上依赖于高科技的动漫语汇,何来如此精湛的艺术呈现?单凭传统的叙述策略何以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哪吒2》是实现古典性与当代性贯通、中国性与世界性互动的成功范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平凡、魔性与人性、成仙与堕落等对立因素相互转化、互为表里,大大强化了电影在叙述和呈现上的复调性、多声部性,这些都是具有世界性特质的艺术语言。而哪吒身上所特有的含混、丑萌、善恶同体等因子,以及那金刚怒目的抵抗性是感动了无数观影者的精神内核,温暖了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们的心。哪吒虽然是魔丸转世,但他内心深处体现的却是人性,有着基于亲情的善良,在与父母、朋友的关系中,哪吒的魔性和仙性最终都通向了人性。《哪吒2》票房奇迹的背后是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独到理解、大胆突破和创造性转化,是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现实和生存经验的敏锐观照和艺术发现,也是对世界性动漫语汇非凡的吸纳与改造。最终,哪吒成为一个既蕴含着中华文明基因,又密切关联当下,并积极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标识性新形象。《哪吒2》的横空出世诠释了一个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艺术是以艺术的方式讲述故事,观念、思想进入艺术之中必得经过审美的整合。要实现中华文明标识在艺术创造中的生成,独特的形式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以这样的理念从事创作,中华文明标识就会超越单纯概念性、物性、符号性的束缚,进入艺术世界的内部,成为形象的有机构成。唯有这样的创作才是“基于文化自觉和自信而实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表达”,才能“转化为新时代作家艺术家充满文化自信的创造能力”。

中华文明标识进入文学艺术之中,会带来文学艺术蓬勃的创造伟力。但如前所述,标识不应该成为艺术形象贴上去的标签,不应该是被猎奇、观摩、置于橱窗里的美学标本。这就要求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创造与新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以及价值取向相契合。唯有如此,这些标识才能成为活在现代人心里的文化记忆,不仅澡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2024年12月,新华网发布了《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年度热词报告》,十个入选的年度热词中,“黑神话:悟空”赫然在列。《黑神话:悟空》借用家喻户晓的悟空故事,演绎了现实人间真实的生存内容。孙悟空虽号称齐天大圣,但并非无所不能。面对现实困境,孙悟空也常常陷入伤痕累累、紧箍破碎等尴尬处境。孙悟空在反抗,但暗处常常涌动起近于悖论的追问:单纯的颠覆秩序是否会带来真的自由?如果不是,那这种颠覆是否也产生新的压迫?显然,《黑神话:悟空》是中华文明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生成,是以“游戏”的方式对全球语境下的人与社会、人与机器、人与人等现代命题的崭新思考。
中国元素是蕴含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形象中最值得挖掘的部分,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文学艺术形象也一定包含着中国元素。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将民族形式与现代经验有机融合,其中的服饰、器具、布景无不体现中国元素,更是借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的交往完成了一次现代人的心灵对话,将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细心的观众甚至看出了《哪吒2》中隐藏着的大量中国元素——结界兽的灵感来自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珍贵文物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商铜鹰形铃;神器天元鼎的原型来自商朝的龙纹扁足鼎;玉虚宫屋顶的场景体现了宋徽宗赵佶的传世名作《瑞鹤图》的意境;包裹着哪吒重生的七色宝莲的原型来自西汉的错金铜博山炉;太乙真人的“酒罐子”取自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罐(《哪吒1》);酒器和乐器真实还原了商代的酒器觚和乐器铙;殷夫人使用的青铜剑原型为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东海龙王敖光那把帅气的关刀,造型取自大洋洲商墓青铜刀;玉虚宫内的仙池花园与山西晋祠的“鱼沼飞梁”的设计密切相关。每一处中国元素都诉说着中华文明历史的厚重以及艺术的灵动,而哪吒身上飞扬的红色飘带传递出的也是“气韵生动”的东方美感。《黑神话:悟空》从建筑到服饰、从音乐到对白都极富东方神韵,将中国元素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碰撞、融汇,形成了契合当代人心理的艺术形式。舞剧《只此青绿》将宋代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意境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舞蹈艺术形式。笔、墨、绢、颜料等非遗技艺与舞蹈艺术相结合,展示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独特意味。

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形象,携带着本土文化的基因与世界文明对话,进而产生“世界可见性”。许多观众意识到了一种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青年亚文化中反权威的朋克精神与哪吒抽龙筋的决绝姿态具有跨文化的契合性。摇滚痛仰乐队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不》的封面,正是《哪吒闹海》里“哪吒自刎”的画面。《哪吒2》里哪吒的烟熏眼妆,也让人联想到来自西方的朋克元素。其实,像中国动漫这样的后发艺术,首先是世界性的影响,然后才是民族性的建构和对世界产生影响,这正好也验证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的预言。
四、在阐释中实现中华文明标识普遍性蕴含的提升
通过文学艺术展示中华文明标识,始终是与作为阐释的文艺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创作与批评是文艺活动的两翼,缺一不可。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认为,在现代社会,“批评有其谦卑但重要的位置”,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没有批评,创作本身或许会陷入沉默。”加拿大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作品自己不能跳出来说话,它是文本呈现出的沉默的语言:“批评可以讲话,而所有艺术都是沉默的。在绘画、雕塑或音乐中,很容易看到艺术在显示什么,但它们却不能说出任何东西。”可见,批评是文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艺创作一道,承担着阐释、推进和繁荣文艺的任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为开展积极有益的文艺批评指明了方向。面对当前良莠不齐的媒体文化生态,批评被置于喧哗的舆论漩涡的中心,承担着培育良好的文艺生态、建构正确的文艺价值导向的责任。
呈现中华文明标识不是艺术活动的终极目标,标识不过是构成文艺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助力文艺形成特色、引导受众领悟其妙的功能。但文艺的最高境界,是创造真、善、美的理想生活,是通过植入中华文明标识性的元素,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守护人的精神与心灵世界。强调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生成,是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文艺创作的母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黑神话:悟空》《哪吒2》《只此青绿》《醒•狮》《长安三万里》《三体》《流浪地球》等作品,几乎都是在对中华文明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不断吸纳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审美观深刻影响了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呈现。而对于这些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文艺作品,批评是不应该缺席的。这不仅因为批评是引导或推动文艺走向繁荣的力量,更因为批评以其独立的思想、学识、眼界、美学与艺术的修养,能为这些艺术提供富有阐释效力的话语,从而抵制那种率性随意、制造流量、网络水军的批评以及“饭圈文化”。例如《哪吒2》传播神话的塑造,自媒体功不可没,自媒体助推了《哪吒2》的大火与热议,但也存在着浅表化、流量化、煽情化等问题。自媒体感兴趣的是拼贴、戏仿哪吒“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以及“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理不容,我便逆转这乾坤”的豪迈格言,热衷于谈论票房破百亿(人民币)的社会热点和商业效应,却往往无暇深掘其中蕴含着的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制作与传播的现代生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介入就显得十分必要。文艺批评家的介入更多体现为对作品的理性思考,它要回答基于热爱的创作热情何以转换为精益求精、制作精良的视听饕餮盛宴;回答中华文明元素如何构成电影内容的文化软实力并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与艺术含量;回答电影是如何楔入青年亚文化心理,青年亚文化心理又是如何参与大众文化产品的塑造并改变了电影的生成机制;回答动漫这一后发艺术如何在参与世界文明体系的过程中书写崭新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关系,等等。显然,来自文艺批评家的阐释是帮助观众以更为积极的方式走进《哪吒2》、以更加接近艺术的方式参与到艺术的接受之中的桥梁。
在阐释中的批评也是跨文化、跨文明对话的积极方式,可以矫正西方之于东方想象的偏见和片面性。艺术中的中华文明标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感性特征,是世界文明体系中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往往与误读和偏见结伴而行。例如,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深受全球喜爱,中国制造的“软萌可爱”熊猫既传达着对于熊猫感性特征的喜悦,也喻示着中国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和文化理念。在跨文化的传播中,很多人注意到了前者却有意无意地选择忽视后者,这带来了中华文明的理念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和意蕴的衰减;同样,“龙”在中国文化中是智慧、力量和祥瑞的象征,西方自中世纪之后则常常把龙视为邪恶与异端的化身。带着这样的“前见”,对《哪吒2》的解读必然带来意义生成的差异甚至对立。同样的形象,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在对话中阐释中国文化关于龙的塑造过程、其谱系和流变等,以纠正西方文化的误读和偏见。
总之,在全球化的文化艺术实践中,仅仅在艺术中展示中国元素、中国标识,还不足以向世界诉说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中国文艺批评家需要做的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在贴近文本、细读文本、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考镜源流,追寻文脉,提升体现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的普遍性蕴含,以实现中华文明在跨文明传播中的本源性、敞开性和对话性。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性工程,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既不能离开自己的传统,也不能脱离本土问题情境而凭空杜撰。无论是对中华文明标识根性的体认,还是在比较中实现中华文明标识意义的生成,都应该在着眼于化解本土问题焦虑的地基上展开。文学艺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最重要的方式和载体,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关键是要提升文学艺术的审美品质,并且以艺术的方式来实现。而无论哪个环节,作为意义阐释者的文艺批评家始终应该是在场的。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邢建昌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王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