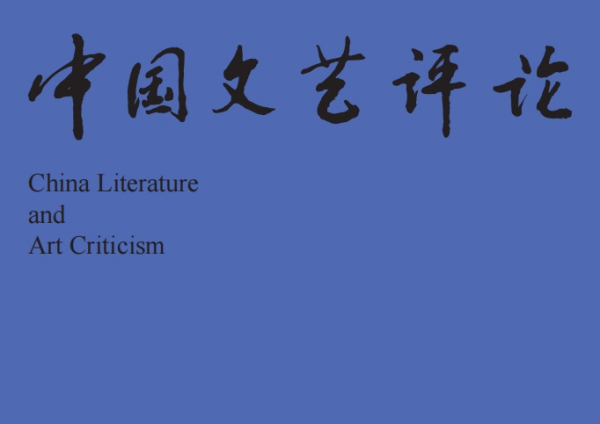
【编者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之义。而文艺作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力量和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媒介,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刊特推出“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专题系列文章,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中华文明标识艺术呈现的理论逻辑、实践意义、历史底蕴、时代品质、世界价值等,以期将这一重大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引向深入。
论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构成与艺术呈现
【内容摘要】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全国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完成。本文从文明、文化整体系统中艺术这一特定领域着眼,探讨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构成与艺术呈现问题。本文认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广大文艺工作者肩负使命,责任重大。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艺术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有直接而深刻的内在关联: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包含着大量属于艺术范畴的内容;其他领域的各种各类的文明标识,则需要以丰富多样、鲜活生动、以情感人的艺术的形式予以呈现和传播。
【关 键 词】 中华文明 文明标识 艺术构成 艺术呈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第十部分阐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时提出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大战略构想,成为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与宏大光荣的使命。新近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指出:“要加强研究阐释,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更好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这一阐述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进一步明晰化、具体化。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十分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全国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完成的一项伟大事业。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文明、文化整体系统中艺术这一特定领域着眼,探讨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构成与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问题。
毫无疑问,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广大文艺研究群体、文艺评论工作者来说,都可谓肩负使命,责任重大,与有荣焉。这是因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艺术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内在关联: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包含着大量属于艺术范畴的内容;而其他领域的各种各类的文明标识,则同样需要以丰富多样、鲜活生动、以情感人的艺术的形式予以呈现和传播。
一、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构成
必须指出,艺术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且独具自身特色的领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超巨系统,有其基本的要素构成、逻辑层次与结构形态。它应该包括各种古代典籍、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思想观念、理论学说、伦理规范、人文精神、科学技术成就,也应该包括那些灿若繁星的历史文化名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能工巧匠,等等。在这一超巨系统内部,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出许许多多的子系统;而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还可以划分出各自的次一级的子系统,更次一级的子系统,等等。其中,有一个子系统或曰分支系统,是本文要着重予以分析阐发的对象,这就是人类的“艺术系统”。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基本观念来看,艺术是人们能动地、形象地认识、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又能积极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一种属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一种基本的、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我国魏晋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指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章即今日所说的文学,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一有关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价值判断,当然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所有的文艺领域。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深刻阐发了文艺的重要价值。他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些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论述,都雄辩地说明:中华艺术必然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极具自身特色的分支系统;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不能缺少艺术系统这一基本结构构成。
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的结晶成果,中华艺术与中华民族的其他文明领域、文明成果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价值体系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系统整体。在精神文明系统中,艺术又因其本身具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要素、层次、结构的体系,从而与中华民族的其他精神文明领域如科学、伦理、信仰、哲学等领域相并立,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世界。而就艺术这一文明领域以及从艺术世界的要素、层次、结构来看,中国古代业已建构起一个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体系。到了现当代,这一传统艺术体系发生了现代转型,开始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
从中华艺术乃至从整个人类艺术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按照艺术类型学的理论范式,不妨把中华艺术乃至整个人类艺术的家族类型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如下三大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两大系列齐头并进,艺术世界一分为二。这里说的是上古时期,人类的艺术天然地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其一是乐舞艺术的系列,它主要以人体本身作为艺术呈现的媒介手段,摹仿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大自然的大千世界,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愿望等;其二是造型艺术的系列,它主要以人体以外的各式各样的物质材料如泥土、玉石、竹木为媒介,以及到了使用金属的青铜时代后,还以金属等作为艺术传达的媒介手段,来摹仿现实,抒情达意。这两大艺术系列并肩前行的历史是十分漫长的,自人类最早期的艺术萌芽时期开始,一直到人类文明诞生之前,具体地说是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形成之前,人类艺术的格局一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早有艺术学者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与阐发,并已成为艺术史领域的普遍共识。而且,“原始时期以及上古时代的艺术自然而然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系列,这并不是中华艺术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各民族艺术发展的共同现象。如古希腊艺术,就存在着上述两个系列的区别。他们把第一个系列称为‘缪斯’艺术,把第二个系列称为‘应用’艺术”。中华艺术在上古时期遵循着人类艺术发展的这一共同规律,只不过拥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面貌、要素与构成罢了。
第二阶段:语言艺术即文学昂然登场,艺术世界由二而三。这里指的是,由于人类发明创造了语言(主要指人类在以往的口头语言基础上创造的书面语言系统)这一新的传达思想感情的符号系统,人们便将这一伟大的文明成果的功用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运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在艺术创造领域,以语言这一全新的媒介手段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即文学体裁:最初,可能是神话传说,也可能是语言精练、讲究节奏、富有韵律的诗歌,之后还有更为成熟的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等。如此一来,人类的艺术世界便由以往的两大系列扩展为三大类型:原始的乐舞艺术发展为包括舞蹈、音乐、戏剧、曲艺、杂技等艺术门类的“演出艺术”类型或曰艺术家族;造型艺术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绘画、雕塑、工艺、建筑、园林(在中国还有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在内的独特艺术类型/艺术家族;再加上新形成的语言艺术即文学的家族,人类艺术世界的总体构成已是三分天下、三足鼎立。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整个人类艺术的漫长演进历程而言,语言艺术(文学)从原始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独立出来自成一个艺术类型/艺术家族,实在是太晚才发生的事情,其历史是非常短暂的。就中国而言,恐怕是到了商周时期甲骨文字日益构成了系统的成熟的语言,方才有了语言(书面语言)艺术即文学的形成,并有了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条件。从那时到现在,仅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类艺术的历史则要比这3000年长得多。
第三阶段:映像艺术姗姗来迟,艺术世界形成四大家族。这里指的是,自19世纪30年代摄影术诞生以来,人类艺术进入“复制技术”时代,或者说是依靠机械技术手段进行“光与影”的艺术创作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艺术以摄影艺术为起点,陆续诞生了电影艺术、电视艺术、网络—多媒体艺术及人工智能艺术等新兴艺术样式。它们因共同的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与媒介上的家族相似性,而在人类艺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类型/艺术家族,我们将其命名为“映像艺术”。由于这一新兴艺术家族的出现,人类艺术由古典时期的三足鼎立格局发展为今日的四大家族共存并立、互促互进。
概而论之,从艺术类型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华艺术从远古至今,走过了由上古的两大系列(人体媒介的传统表演艺术与物媒的造型艺术)、到语言文字出现后的三大类型(上述两大系列+语言媒介的文学艺术)、再到现当代的四大家族(上述三大类型+影音技术媒介的映像艺术)的演进过程。这样的艺术演进过程,世界各民族都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对于中华艺术来说,在每个艺术类型/艺术家族的内部要素中,都具有中国独自的传统与特色。如在人体媒介的传统表演艺术中,中国的乐舞艺术、五声音乐体系、曲艺、杂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戏曲等,均具有鲜明突出的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精神与艺术特点;在物媒的造型艺术中,中国的玉石工艺、陶瓷工艺、青铜礼器、书法艺术、篆刻艺术、中国画、写意雕塑、建筑园林、其他工艺门类等,都独具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艺术风范;就语言艺术/文学而言,中国的散文、辞赋、格律诗词、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孕育了无数的诗人、辞赋名家、散文家、小说家,诞生了灿若繁星的经典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而自摄影、电影、电视及新兴的多媒体艺术等现代映像艺术家族的新成员进入中国现代艺术体系之后,它们立足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土壤,表达着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传承着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传统,成为了现代化历史语境下现代形态的艺术的代表性样式。而上述三种传统艺术类型也在现当代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现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续写着各自的辉煌,创造着新的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这些不同门类、不同类型的艺术所创造的那些辉耀古今的经典名作,极大地充盈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并在这个超巨系统中独放异彩。
二、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
上文我们着重阐发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属于艺术的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那些本身并非艺术的,实际上在数量、体量等方面都更加庞大的其他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中华文明标识,如古代与现代那些标志性的自然科学成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认知水平、道德水准的思想、观念,那些各行各业以各种方式影响或推进了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著名人物——那些彪炳史册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工匠名师、医神医圣,等等,尽管他(它)们本身并不属于艺术的范围,并非以艺术的形式而存在,却也都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予以呈现。
那么,这些中华文明标识何以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予以呈现呢?盖因艺术具有感性直观、具体可感、情感充盈等审美特点,能够让接受者在作品生动形象之魅力的吸引下,在作品动之以情的感染下,在潜移默化之中理解文明的成就,接受文明的化育,提高文明的自觉程度与意识水平,从而成为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成就的传承者与未来新文明的创造者。
对于艺术所独有的这些魅力与特点,我国古今许多艺术理论家都有精辟的论述。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在其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理论名篇《乐论》中,谈到先秦时期的“乐”的功用、效果时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他这里所说的“乐”,可以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其文论代表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小说这一语言艺术样式不仅具有“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以及“感人之深,莫此为甚”这两大艺术效果,而且还具有“熏”“浸”“刺”“提”四大特殊功效:“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具化者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意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梁启超的“四力说”虽然谈的是属于语言艺术的小说,但对于理解其他艺术样式的艺术效果也具有参考意义。
以上这些论述都表明,艺术能够以其特有的功用效果,即诉诸生动具体、感情丰沛、感性直观的艺术意象,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对其他各种文明成果、文明标识予以全新的诠释、阐发,给予新的艺术的表现、表达,以利于人们对这些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接受。这一点,对于古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普通民众而言,其效果就更加明显: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其传播力远胜于那些书面文字的、玄学理学的等更具知性理性色彩的呈现方式。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上,以各种艺术的方式非常成功地呈现这些文明成果、文明标识的实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分别作为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的孔子与老子,就被历代的画家、雕塑家们绘入丹青水墨,塑于名山大川,让他们的思想学说,借助于这些感性具体的艺术形象,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如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诸葛亮,不仅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到活灵活现的艺术呈现,而且也在诗歌、戏曲、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形式中得到各具异彩的艺术表现。再如,明代铁面无私、清廉公正、闻名遐迩的清官典型包拯,在历代(包括现当代)的诗词、小说、戏曲、曲艺等艺术门类中,都得到了极为生动传神、淋漓尽致的呈现,以至于人们一谈起为官清廉的话题,不自觉地就会想起“包青天”的形象。笔者认为,我们古代包括语言艺术/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样式,在以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再现、呈现、重释、重构中华文明中那些具有标识性、典范性意义的文明成就、历史人物、伟大事件时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所形成的创作范式、所诞生的经典作品,为今天的人们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可资学习的难得的范本,需要我们给予认真细致的总结,潜心诚恳的学习借鉴。
我们欣喜地发现,到了现当代,文艺工作者们更为自觉地、更具创造性地将那些代表性、标志性的中华文明成果和标识,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所独有的审美的形式予以全新呈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以孔子为例,在当代就有长篇小说、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对其予以生动呈现。其中,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倾情打造、孔子第77代孙、著名导演孔德辛执导,2013年首演的民族舞剧《孔子》,尝试以舞剧的形式将儒家学说创始人——其思想给中国历史以极深刻的影响达2500年之久的孔子的故事、形象、人格、理想搬上舞台,一经上演便获得巨大成功,历经十多年仍备受追捧,称得上是以孔子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中的突出代表。而由山东省话剧院编创、著名导演张继刚执导的大型话剧《孔子》,自上演以来,也备受欢迎,长演不衰,与舞剧《孔子》相映生辉,堪称孔子题材舞台艺术之双璧。除此之外,在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样式中,孔子也经常成为被表现、被阐释的对象。如当代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塑造的《孔子》雕像,巍然耸立在国家博物馆、孔子故里等空间场所,每当人们看到这些庄重伟岸的雕像,都会感受到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光辉与人格魅力。可以说,像孔子这样的在中华文明中极具标志性的人物,在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得到过现代的多维立体的艺术呈现,这对于传播孔子的伟大人格及其思想学说,功莫大焉。再如吴为山的其他雕塑作品《老子》《李白》《苏东坡》《鲁迅》《齐白石》等,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成功实践。近来,由电影导演陆川跨界执导的舞剧《天工开物》广受观众追捧,也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像这样的探索、实践在今天还有很多很多,其中蕴含的实践经验及理论问题,均有待于我们认真的梳理与总结。

吴为山《画家齐白石》雕塑 青铜 维也纳世界博物馆藏(来源:“中国美术馆”微信公号)
在探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及其艺术构成、艺术呈现等问题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明晰的回答。这就是梳理、总结中华文明标识的时候,是否应该将中国现当代所创造的那些具有突出标识性意义的文明成果、文化成就、历史人物等纳入其中,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呢?笔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完全应该的。像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历史事件;像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像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这样的伟大的军事家;像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文学家;像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聂耳、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等等,都是极具标识性意义的中华现代文明的突出代表。他们既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在现代的自然接续,也是在现代生活土壤上盛开的富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中华文明的鲜艳花朵。对此,我们当然应该怀着饱满充盈的热情,以最鲜活生动的艺术语言、最具创造性和感染力的艺术方式,予以充分的艺术阐释与艺术呈现。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当代的文艺家们在这方面已经或正在作出他们的努力与探索,已经或正在取得不凡的收获,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李心峰 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