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对宇宙存在及其文明的深刻思考。其观察宇宙的方法论不是对宇宙的仰望,而是一种从宇宙出发的平视。他并不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多元的。宇宙一直处于运动之中。不同的宇宙存在相互联系作用,形成宇宙的统一体。在这样的运动之中,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存在微不足道。但是,这并不等于人类没有价值,没有希望。相反,人类由于具有理性、情感、好奇心与创造力、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对宇宙而言具有独特价值。也正因此,人类总是拥有未来与希望的。

民族歌剧《尘埃落定》改编自小说家阿来的同名长篇小说,全剧经过主创团队的精心创作和反复锤炼,最终实现了由小说向歌剧的巧妙转化,使得全剧具有了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民族歌剧《尘埃落定》于2018年在重庆首演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歌剧院院长将此作品献礼新中国,于2019年3月17日在北京上演。本文就剧情编创、舞台空间、音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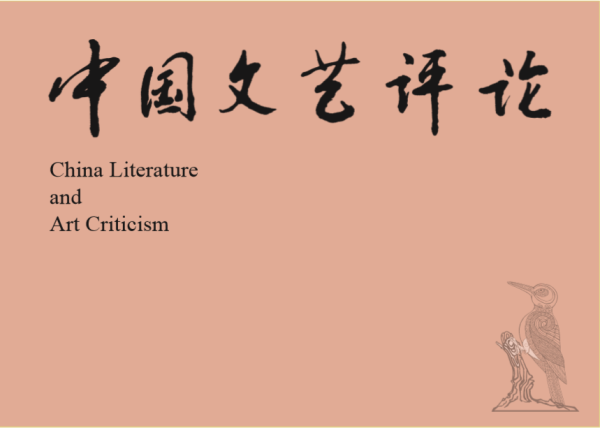
现实题材话剧《小镇琴声》以轻喜剧的方式呈现了一群农民为了生活和梦想而拼搏和追求的一生。伴随着追梦的过程,编剧在主题选择上做了精心而独到的提炼,二度创作的轻喜剧风格鲜明,舞台美术灵活、唯美而诗意,实现了从题材“现实”到表达“现实”的跨越。该剧对现实题材话剧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同类题材的“泛”,采取更加聚焦、更加提炼的“典型”故事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价值;二是较好地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从文本到舞台的整体表达,有利于话剧艺术总体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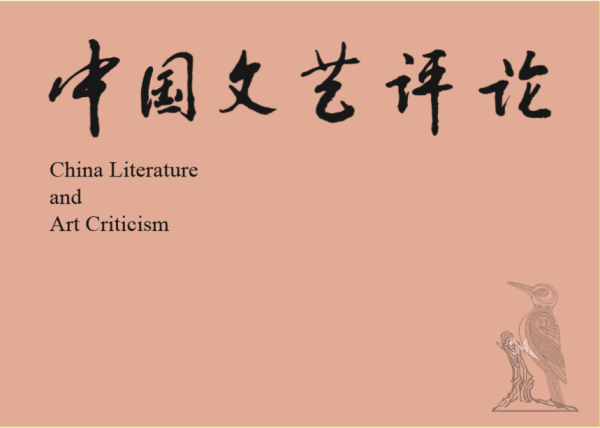
“现时”的现实题材舞剧以何种态度面对现实,是当下舞剧创作亟待重视的议题。舞剧《记忆深处》对这个难题予以回应,且做出了表率。该剧不以“美”为前提,而是以“真”为前提。编导借由张纯如的“真”,从不同视角共同揭示历史真相,为我们彰显出“求真精神”的可贵,也表达了真实的生命态度。与张纯如的专著《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第一部分类似,《记忆深处》也借鉴了电影《罗生门》的叙事结构,但《记忆深处》又不是“罗生门”。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无解的悬念,而是基于探寻社会正义的明确的历史判断和事实。那么,何谓当代现实题材舞剧之“真”呢?我们的编导不仅要有选材上的锐气和立意上的“深度和高度”,还应进行结构和语言等艺术表达层面的整合。这体现了编导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人性层面的深度探

话剧《生命行歌》是一出表现临终关怀的人类主题剧目。在老龄社会特征日益明显的当下,临终关怀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里的焦点话题,无法回避的生离死别悄然成为千家万户有切肤之痛、割至亲之爱的民生问题,活的体面与死的尊严都成为了人类生命同等重要的观测点,作品告诉了观众创演者的观察、感受、颖悟。一个宣传题材被提炼为艺术作品,一些个别事例被塑造成生活典型,一种难以表达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被渲染为细腻抒情、象征写意的生命行歌,同时泰戈尔与白居易诗句里的生命意象充盈于演出中,创作者们用精巧设计的舞台叙述抓住观众的欣赏心理,体现了剧目创演的诗意充实性与叙述形式感。

因执导电影《十八洞村》(2017)而为人熟知的女导演苗月,新近执导的影片《大路朝天》(2018)可谓继《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后又一部较为成功的坚守艺术尺度的类型化电影,它是对“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序列中新时代工匠精神伦理传承的思考。影片本身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有益探索以及浪漫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都使该片具有感人至深的审美魅力。

大型民族舞剧《醒•狮》以反思的态度与对话的立场观照了乡土与国家,对接了历史与当下,升华了本土故事蕴含的大中华精神,体现出这个以“民族舞剧”定位的作品所具有的身份意涵与开放态度,立意深刻而意蕴丰厚。全剧以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演进作为舞段安排与演绎的核心,舞蹈技术性、功能性的表达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度,既凸显了舞剧的舞蹈本体美,也忠实了戏剧必须坚持的“剧”的质感和内涵。《醒•狮》团队以自觉而深情的文化自省演绎本土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体现出传统文化复兴进程中应秉持的态度与担当。

本文以花鼓戏《桃花烟雨》为个案,从它生活化的喜剧样式、散文化的结构特点、角色反差的喜剧技巧、回归本体的民间趣味出发,分析了戏曲地方剧种发展的喜剧路径,认为化合剧种特点、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对探索现代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作家柳青是扎根生活、深入群众的作家典型。由剧作家唐栋编剧、西安市话剧院创作排演的话剧《柳青》为“人民作家”立传,生动地塑造了当代舞台新形象。该剧通过选取典型的戏剧动作、设置精准的人物关系,开掘人物身份的多重性,塑造了柳青“人民作家”的生动形象,表现了主人公“身入、心入”群众的艺术追求与情怀。然而,该剧对柳青潜心投入《创业史》创作过程的开掘还欠深入。作品可进一步突显柳青的主观视点,通过《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中生活原型的对比映照,强化对柳青的艺术思维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表现。

由北京京剧院演出的小剧场京剧《好汉武松》颠覆以往小剧场戏曲过度创新、实验的属性,在情节、主题、表演上“致敬”传统:情节上保留传统剧目的核心情节;主题专注于深化原著中的武松精神;表演承袭传统武生戏的表演程式和审美特点。《好汉武松》指出了小剧场戏曲如何在古典形式和现代理念之间寻找一条平衡的途径:用先锋的外壳,符合现代观演习惯的节奏和视觉效果,以达吸引观众的目的;尊重传统京剧的精神内核,以守住戏曲本体。

近年多部西藏题材电影进入院线后取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引起了话题讨论。尤其是以公路片形式表现“朝圣”内容而实现心灵救赎主题的电影,因为汉族和藏族导演地域身份的差异,呈现出的电影类型风格和传递出的题旨意念很不同。汉族导演往往以“他者”视角,延续西藏“香格里拉”的神话形象,为当下现代化却也荒原化的城市精神文化提供了疗伤的途径和审美救赎。藏文化源地导演则去魅西藏的宗教神秘和地域奇观,还原当代社会生活场景中藏族人民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复杂,开拓了西藏题材电影的类型,改变着大众传播媒介中西藏形象的既有模式和印象。

就个体角度来说,郑浩天的形象充满了悲剧性。无论在大阅兵的活动中如何表现,有多么重要,他仍然是悲剧性的。而正是这种悲剧色彩使郑浩天形象得以在舞台上矗立,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落的经典写照。

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融合的作品。小说借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元素,结合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具有清晰的历时性表层结构和内容繁复的深层结构,对戊戌变法发生的全过程做了详尽描述。小说试图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捡拼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铭记为社会转型、历史进步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以凸显其现实意义。

本文紧密结合歌剧理论、循着歌剧艺术特殊规律,对四幕歌剧《兰花花》进行了学术性研究。论文基于歌剧总谱分析,围绕戏剧冲突所关联的人物与环节、主题设计布局和整体结构间的关系,以及运用现代作曲技法讲述中国故事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对作品运用西方歌剧形式,充分发挥歌剧音乐表现的结构与戏剧张力作了深刻阐述,并指出作品不仅为现代中国歌剧创作开拓了新的天地,也为歌剧创作提供了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

2018年3月小剧场戏剧《最后的卡伦》首演,反响热烈。这部喜剧寓庄于谐,既有深刻丰厚的内在意蕴,又不乏诙谐荒诞的喜剧形式,在解构与重构的舞台叙事中充分强化了喜剧的游戏性、表演的身体性和形式感,在质朴的美学趣味中回归了戏剧的本质。特别是,喜剧演出挑战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既有观念和美学风格,在继承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更契合了新时代和观众新的审美需求。

对于所有艺术工作者来说,“飞天”形象是中国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不断生化的可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相继出现了以“飞天”为主题的舞蹈作品,如双人舞《飞天》和《丝路花雨》中的“飞天”群像等,后期又出现了独舞版《飞天》《大梦敦煌》中“飞天”舞段,春晚版《飞天》,奥运会版《丝路》等不同舞蹈作品。同一个形象的“飞天”,可以有众多不同版本的舞蹈艺术创作。在整整70年的历史长河中,一部部经典的《飞天》作品见证了中国舞蹈的蓬勃发展,以及编导们不取苟同、多歧为贵的创作手法。

话剧 《广陵散》的“选择”命题超具有独特的人生况味,剧作家从“竹林七贤”的人生选择中提炼的是独立的个体人格;导演从古典戏曲中借鉴的表现方法,体现于《广陵散》的是创造性的话剧转换;演员的创造性表演则是突破戏曲的范式在手段转换上的精神性追求。《广陵散》的现代性气质是现时期中国戏剧的一个成功范例。

本文从创作美学层面对暑期播出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这一深受欢迎与赞誉的现实主义力作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典型人物与人物群像塑造、影像风格与意境等方面的精神启示与艺术创新。文章还对新时代现实题材主旋律剧的艺术经验与不足展开思考,围绕创作在开掘生活与艺术转化、事理逻辑与情理逻辑的把握、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审美价值倾向、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利于今后该类创作的长足发展。

2018年5月国家京剧院在合肥上演京剧《伏生》,对比以往中国古典戏曲里呈现的悲剧“大团圆”结局,该剧本质上颠覆了长久以来传统戏曲在悲剧范畴内依存的圆融之美。这是一部尊重史实、富有思想进步意义、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艺术作品。从学者们对于中国悲剧理念的摘要评述来看,《伏生》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悲剧。实践表明,它的悲剧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大致体现在观众获得悲剧快感、与主人公产生反抗意识的共鸣之后,接下来产生的自我净化、自我审视与自我升华。

新编越剧《游子吟》以唐代诗人孟郊和母亲的情感关系为主线,于寻常生活中提取戏剧情节,以诗化的意境、舒缓的节奏展示剧中人物真实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体验,呈现出永恒不变又具有时代质感的母爱主题,吸引观众在对剧情产生强烈共鸣的同时,对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进行观照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