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文艺创作生产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从“高原”跃上“高峰”的重要举措。主题文艺创作作为捕捉时代脉搏、反映社会发展、描写人民生活、体现民族精神、传递真善美的重要艺术创作形式,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呈现出新的气象和变化。同时要清晰地看到,当前主题文艺创作依然存在题材扎堆、形式趋同、表达模式化等突出问题,部分创作者热衷于堆技术、堆舞美而忽视剧本,热衷于改编而忽视原创,热衷于“帽子”“奖项”而忽视创作过程和作品本身,既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也难以承载新时代文艺精品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为了深入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引导文艺创作者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主题文艺精品力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策划“艺见”系列专题,特邀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创作如何打造精品”撰写系列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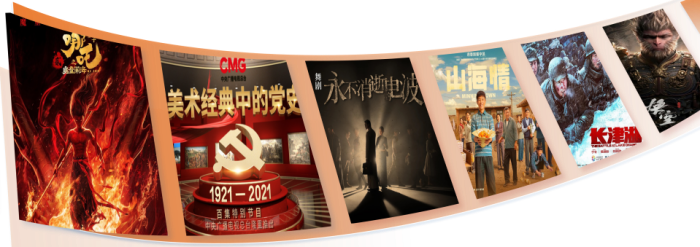
主题创作不应忽略艺术创造的想象性

尚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主题。主题本无大小,但约定俗成的是把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作为重大主题,其余均被视作一般性主题。显然,一般性主题表现较为自由,也易个性张扬;而重大主题因涉及历史或现实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创造性的束缚,相反,只有充分激发艺术创造的想象性、充分发挥艺术表现力,甚至强化艺术个性,才能使重大主题创作突破历史与现实的限度而成为艺术之作。
自2005年第一个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以来,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美术创作工程、创作项目不下10多项,由此也促成了一些地方美术创作工程的兴盛。这些创作工程或项目确定的选题,不是美术家根据自己兴趣自选的创作题材,而是由历史学者编制的有关中华文明史、中共党史以及各地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题材目录,然后再开展创作者层面的选题招标或选题委约。不言而喻,这些选题具有命题创作的属性,而艺术家未必熟悉这些选题内容,却要在选题设定的内容范畴里进行规定性的创作。工程实施推进过程中,一般由史学家、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跟进和督导。历史真实重要,还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动性重要,在创作推进中常发生争论和争议。
创作工程作品的验收最直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毋庸讳言,经工程或项目验收所产出的众多作品,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量的精品佳作总不如期待的多。那些虽通过验收,但不是造型有缺陷,就是缺乏巧思的作品也总占多数。那些作品看似符合选题内容的要求,但让人总觉得缺了艺术感染力。强调历史真实没有错,但历史真实不应是生硬的照片形象拼贴,更不该是多场景搬移的P图。以真实的名义束缚了创作的手脚,以文本说明作为创作的背书,这样的主题创作怎么能发挥艺术的创造性?许多作品从构思阶段就被捆住了创作思维,错把题材目录的选题说明当作完成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常常为了表达选题字面意思而成为内容空洞的图解。把选题当画题,还导致了作品常因缺乏画龙点睛的题目,而暴露出作者人文修养不足的短板。
作为历史画的主题创作,主题来自对历史真实的锤炼。任何对客观历史的描写都未必能够形成因再现了这个历史场景而可能被忽略了的主题提炼,何况很多主题画面只能算作历史场景的碎片。从这个角度讲,曾经的新闻摄影,只能是历史第一现场的某一瞬间,而要把这一历史瞬间升华为艺术性的历史画,则不能离开作者的主体意识——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历史的判断,这便形成了历史画之中的主题性。因而,在这些历史画创作中,艺术家必须在历史学家提供的文字提示基础上,做更加扎实的历史研究功课,艺术家甚至比历史学家还要深入到某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他既要深入其里,寻找所有的可视历史物料——从人物形体、面孔、表情到服装、环境和道具,又要加深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加深层的人文理解,形成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认知与判断。虽然,许多历史是通识,但只有在这个深入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自己对历史对象的形象化理解,尤其是不断增进自己对这个历史对象的情感积淀。就像当年周思聪创作《人民和总理》那样,画面上的题词:“俺们舍不得总理走。他说:‘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如今灾区变成了新村,俺们大伙等啊盼啊,就盼着那一天……”这段题记也可看作是艺术家创作此画的深情寄寓。作者为百姓的这段话而感动,画作里也无不充满了这句悲伤的话语体现出的敬爱情感,笔墨的沉重正是这情感的转化与放大。可见,所有的历史细节如果不能被精神情感所调动,那么,创作只能沦为无情感冲动的制作,更谈不上深刻发掘了。
深入历史研究,还要探寻符合历史情境的表现视角,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富有画面感的构思。当下许多主题创作之所以缺乏构思的新意,在许多情形下,是被项目文字表述限制住了想象。比如,这些工程项目中,要求表现会议或会议决策的选题不在少数。但会议题材仅仅局限在会议本身的再现上吗?可否把某个会议决策的呈现,转换为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如转化成对某个富有生活质感的情节或富有感染力的现实场景的呈现呢?即便是正面描写会议,也不应只能像新闻摄影那样选择“决定性瞬间”,而应当对会议进行戏剧性的人物编剧。在此,调动或充分发挥艺术创造的想象力,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比如,“遵义会议”这个选题,彭彬、刘向平的作品都富有想象性地把与会人员放在会址二楼的过道上。刘向平的作品还通过会间休息的生动描写,反衬这个决定了红军命运的会议是如此的凝重。这两幅画面的会外场景描写,都是画家艺术想象的虚构,甚至两幅作品还隐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视点。就正面描写而言,人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沈尧伊创作的《遵义会议》。此作看似描写会议场景,但绝不是真实会议的再现,而是以会址现场为背景进行绘画独特的艺术再现——群体肖像创作。如果说,这幅画作最富有历史的真实质感,是因为作者半生为创作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而多次重走长征路,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视觉素材,而使画面上的每个历史人物都符合他们特定的身份形象,甚至主席抽烟的动作及烟盒商标的细节。这幅画作的主题,还通过人物排列的中心与非中心、表情与情态、人物性格与体态造型,以及墙壁上的马克思像与窗外黑沉的夜色等设计,暗示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所表达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深层寓意。

沈尧伊 遵义会议 布面油彩 300cm×600cm 2006 中国美术馆藏
或许,“遵义会议”这一历史题材没有留下多少图像素材,反而倒逼画家去充分调动艺术创造的想象性来弥补。摄影、影像对当代史的记录无处不在,看似给艺术创作提供了便利,却反倒让作者追踪现成图像、拼贴图像,成了摄影图像或AI数字软件的俘虏,艺术创造的想象力被严重挤压排斥掉了。新时代主题创作的选题编目,不乏较多的重大会议及决策,不乏重大事件与英模人物,不乏重大科技成果问世,但表现这些题材的主题创作反而缺少了绘画、雕塑的艺术性建构,缺少了艺术家主体性的主题发掘,甚至远没有纪实摄影对历史瞬间刻录的那份原初的朴素。有的作者曾悄悄地询问笔者,他对这些自己的创作没有底气,甚至觉得他的画就是摄影的放大或摄影AI图像再生,主题性绘画的意义似乎在图像时代已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确,如果没有画面感的构思,没有绘画、雕塑因不同材质、技巧和历史沉淀的艺术语言所形成的造型形象魅力,没有作者自己对历史与现实深刻的人文理解并由此形成带着情感的释读与判断的话,那么,这些主题创作只能是二流、三流的摄影图像了。主题创作在当代必须接受多种机械或数字图像生成的挑战。虽被图像包围,却要勇于并能够破其所束。许多作者深入生活是带着摄影器材去的,镜头替代了他们肉眼的形象感知力,更替代了他们通过画笔去传递和勾画心之所悟的形象。他们的创作已沦为电脑编程的图像合成,似乎AI完全能够替代他们所感知的形象。一个画家丢掉了画笔,就像战士丢掉了武器。其实,艺术创造的想象性,对画家而言,就是他笔下的想象力。艺术家所有的主体形象重建,都需借助于自己所擅长的媒介或语言来实现,犹如作曲家的旋律、声乐家的歌喉、舞蹈家的身形。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不能用摄影去替代,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感染力是源自画笔完成的艺术想象造型。在那些看似真实的所谓再现性绘画上,无不是艺术家对现实形象的主观再造,无不是符合美的原理的想象性建构。就此而言,主题创作的历史真实只有通过艺术想象性的创造,才能跨越真实与图像的限度,真正实现艺术的升华。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4月16日第6/7版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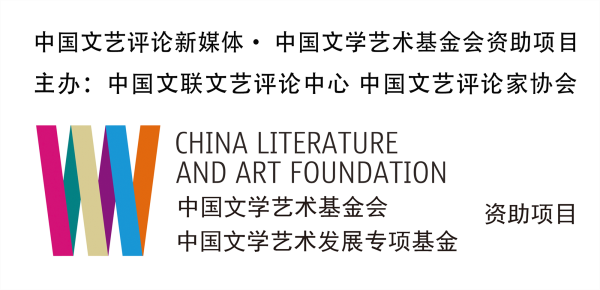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