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档备受关注的影片《不说话的爱》聚焦听障人士生活,在上映伊始便取得预售第一的好成绩,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影片讲述了独自照顾女儿的听障患者“小马”,为了在与听人(影片中以听障人群对听力健全大众的称呼)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的官司上证明自己的抚养能力,受不法团伙诱骗,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并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该电影通过展现家庭情感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复杂矛盾,揭示了听障人群艰难的生活现状,呼唤观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居高临下的同情听障人群的苦难,而是在银幕中建构出更加接近听障人群视角的“听障世界”,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得以代入、共情并最终沉浸故事当中,更加直观地与听障人群“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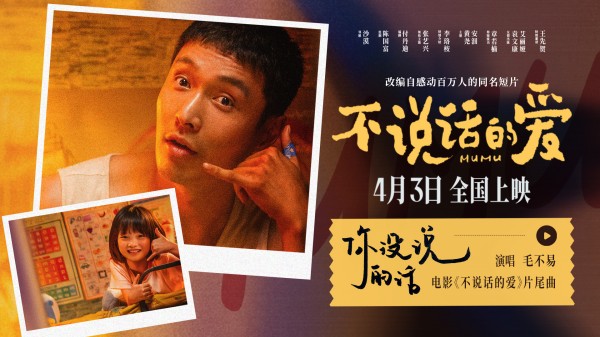
代入:视听感官的错位认同
在观影过程中,作为观看者的观众和作为被观看者的主人公小马在视觉权力上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而小马听障患者的身份则会使这种不平等更易显现。观众往往会成为怀着侥幸与同情心理的旁观者,而难以代入角色的第一视角。因此,导演首先使用大量的平视镜头给予了小马和观众在视觉地位上的平等身份。不同的拍摄角度会给予角色不同的视觉地位,导演在影片中没有为了渲染苦难或人物情绪而使用戏剧性更强的俯仰镜头,而是用平视镜头表达对于小马乃至影片中所有弱势群体的真诚与尊重。尽管这种角度有时候是反直觉的:在影片前半段小马和女儿在家中透过镜子对话的一场戏中,父女两人分坐上下铺,为了使主观视角符合观众习惯认知,一般都会采用相应的俯仰镜头。但导演在此处仍旧将父女两人的主观视角都以平视展现出来,这段镜头既是听障患者小马与听人木木平等身份的见证,也是一个听障父亲与健全女儿彼此之间忽略差异、真诚沟通的亲情注脚。
在观众心理上为小马取得了平等的视觉地位后,导演还运用视听语言使观众在感官体验上接近小马。首先在视觉层面上,导演在拍摄听障患者互相“对话”时采用了大量的中近景单人镜,将镜头对准了人物的“手语”以及面部表情,限制了画面中的视觉信息。这种小景别镜头使观众不得不像小马一样在“听”手语时强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手部动作。因为在听障患者眼中,只有注视,才能倾听,这种景别选择无疑是对小马视角的模仿。
相比于视觉上的代入,声音层面的处理则更加直观。导演不止一次对影片中的角色台词、音响效果等进行消音,从而在短时间内将观众的听觉体验无限拉近小马的听觉感受。在小马因听障而在工作时闯入女客人的酒店房间时,导演将女客人的谩骂消音。那一刻开始,观众与小马一样,虽然听不到女客人讲话的具体内容,但却更能体验角色身上的那种窘迫与无助。这种视听上的接近,使观众得以跨越与小马生理上的客观差异,完成对于听障患者的错位代入。
共情:角色形象的道德审判
影片中的小马为了证明自己具有对女儿木木的抚养能力,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做“大生意”的赵老板。赵老板以帮小马开具资产证明为条件,威逼利诱小马参与犯罪活动,通过伪造撞车现场骗取保险金额。让主人公从事犯罪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是违背人物形象的创作逻辑的——犯罪行为往往意味着道德的严重偏离,会导致观众在观看时拉远与角色的心理距离,难以对角色共情,进而无法进入由该角色主导的故事。因此,导演在叙事时有意识地弱化了小马因生活困境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中年人身份,相应地,强化了其为了维系家庭生活而不惜自损身体健康乃至道德准则的父亲身份。遵纪守法是社会共识,而做一个好父亲同样也是社会共识。两种身份所产生的道德挣扎与心理矛盾,丰富了对于小马道德判断的维度。小马的犯罪行为从为了留住女儿开始,到为了女儿能够拥有更好未来结束。以女儿的幸福成长作为全部犯罪动机的小马,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隐忍、付出、不求回报的“慈父”形象的建立。
此外,无论是初次目睹犯罪现场时下意识的阻拦行为,还是犯罪结束后决裂式的自首意愿,都表现了小马身上强烈的正义感,不仅使其明显区别于一般犯罪分子,而且更加强化了小马作为一个父亲所做出的牺牲。诚然,针对小马的犯罪事实,法律的判决无法逃避且不容置疑。但当法官在法庭上的宣判坐实小马违法身份的同时,女儿木木在法庭上撕心裂肺地哭喊无疑是对小马父亲身份的肯定。这种针对其双重身份所做出的不同道德判断,势必随着家庭叙事线索的强化而使小马作为父亲获得更多观众的道德认同与心理共情。
沉浸:回避苦难的温情世界
当观众能够顺利代入小马的听障角色并共情其父亲身份后,便会开始关注该角色所处的故事世界。值得肯定的是,导演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关于苦难的书写与贩卖。不同于沙漠本人执导的同名短片中以灰黄色主导的低影调的影像表达,影片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都采用了高影调的表达方式,为观众在视觉上营造出了一个明亮、温暖的银幕世界。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听障人群能够与健全的听人同样在生活中克服困境、乐观向上的温情期盼。
除此之外,导演多次借用木木的视角,对听障人群在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完成了孩童视角的全新建构。在木木眼中,灯光下不断变换成各种小动物的手影代替了生硬冷漠的手语动作,因听力障碍引发的“打斗”也成了溢满笑脸的游戏场景。在游乐场里,木木送给小马一只鲸鱼造型的玩具口哨。小马发出“鲸鱼没有声音”的疑问,而木木则是用充满童真的语言回答“它的朋友可以听到”。这不仅是木木与小马挚友般父女情感的佐证,亦是导演对听障人群根本困境提出的解决方式——只要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耐心交流,听人和听障人群就可以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这种充满童话色彩的叙事方式,必然吸引着观众沉浸其中,体验属于听障人群的温情世界。
导演通过影片所建构的“听障世界”,能够让更多听人看见并关注听障人群的生活,能够使更多听障患者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就已然为那片无声的阴郁天空,涂上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作者:郝静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泽甫,山西大学文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