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之新
——凡一平的《四季书》及其上岭村系列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凡一平以长于讲故事,以及文学与影视互文而著称。他常以机智、幽默乃至调侃的语调表达庄重的主题,在似乎漫不经心中,步步引人深入他创造的神奇莫测、泥沙俱下又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乐生又悲凉,喜感而忧伤,幽默与机智,富有现实中国的时代性和当下性。近15年,凡一平专注建构他的精神原乡:上岭村。在此,他的文学视野、情感和审美方式饱含人文关怀和艺术理想,《上岭村的谋杀》《顶牛爷百岁史》《上岭恋人》《四季书》等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韦正年、顶牛爷,以及小偷师傅、侦探、产婆、裁缝、说客、保姆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个群体既是上岭传奇人物图谱,也是现代乡土中国的人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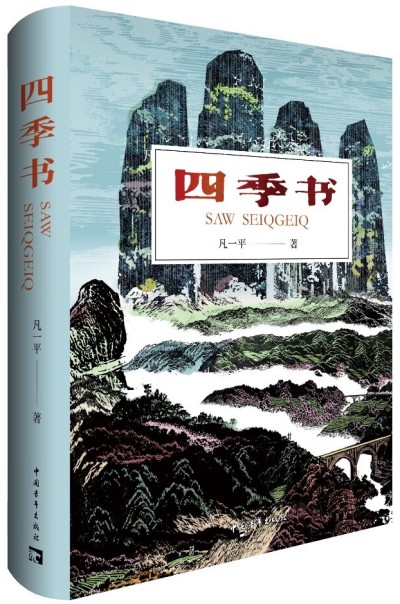
我们知道,今天的关于农村题材的书写,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写作者具有现实关切和忧患意识,需要作家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尤其与自我建立起一种关系。因为乡土中国的书写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阶段,“新乡土叙事”之新,在于无论表达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美学样貌,这不仅是时代巨变带来的乡村变化,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形态、自然生态,尤其精神需求和矛盾问题,都期待写作者的艺术挖掘与表现。因此“新乡土叙事”需要在日常经验美学与宏大史诗美学的融汇再造,从而建构一个开放包容的现实主义美学。这一有难度的文学创作,在凡一平新长篇小说《四季书》中,成为一个立足乡土现实又超越生活的人生寓言,他视人生重要的四要素:生、自由、爱与死,分别融汇对应着主人公韦正年的冬、夏、秋、春。小说既讲述了上岭村人韦正年至善至义、灵异而不凡、坎坷而中正的一生,还讲述了作者的精神原乡上岭村近百年的历史巨变和时代图景,尤其成功塑造了孤勇者韦正年的形象,写出了这个在每个时代都追求光明、为民请命、舍生忘死而又性格倔强的生动人物形象。虽然小说叙述的散文化,以及每章结尾的卒章显志,似有画蛇添足之嫌,但瑕不掩瑜,可以说《四季书》是作者上岭村系列的用心之作,也是当下新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首先,凡一平新乡土叙事之新,在于他创造了系列新乡土人物,这些自幼就种植在他心底的传奇人物,有着乡土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伦理和民间文化的各种形态,如村村寨寨都有的产婆、名偷、裁缝、族长等,如代表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顶牛爷,作者与这些人物对话,并以平等视角切入和塑造人物,使人物既散发人间烟火气,又可感可触,栩栩如生。如《我们的师傅》是凡一平近年完成度较高的好短篇,是作者在小说样貌上不断自我突破,从俗世欲望化写作进入节制内敛的美学建构,并为当代文学新添了一位富有个性的有情有义的新人形象“小偷师傅”。《我们的师傅》讲述因羞于少时偷盗而不相往来的“我们”,最终相聚在偷盗技能师傅的葬礼上,演绎了一场“小偷家族”追忆昔日少年曾经沧海的人生顿悟,死者韦建邦自幼聪慧好学,多才多艺,心怀理想和爱情,坚持15年给心中恋人写信,在面临被命运作弄和没钱买邮票的双重打击下,为了生存和写信专偷为富不仁的人,还不断教育“我”等小徒弟,一定要通过读书走上正道。小说成功塑造了这位被迫沦为小偷师傅的人物,及其在泥潭也谨记“盗亦有道”“偷是为了不偷”的规训。小说中师傅韦建邦从未现身,却在“我们”的追忆与顿悟中,成为一个处处引领我们向善向上的文学存在,成为一个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行文走笔幽默机智,令人莞尔;字里行间饱含同情之理解,一种对特殊年代野草般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忧伤悲悯,回味绵长。
凡一平还以写“我们的师傅”之笔力,成功塑造了“顶牛爷”的形象。短篇小说集《顶牛爷百岁史》9个短篇,视角新颖,9个关于顶牛爷樊宝笛的故事,从旧军人到阉猪佬、船工,到交公粮、暴富花钱,走桃花运,一个个充满人间烟火,又多角度塑造了一位与中国百年同行而富有传奇色彩、顶天立地的“顶牛爷”形象。“喜欢与人顶牛”、喜欢讲理的农民,当然是复杂而独特的。他贫穷不缺勤劳,倔强却不损人,固执不失宽厚,娶不了媳妇也不乘人之危,以媳妇之名收养难民覃小英,早年单身壮汉的良行,才有晚年覃小英的报恩。《花钱》相当出彩,描写村民亲戚的狡黠偏狭和贪婪自私、顶牛爷的斗智斗勇,作者写活了顶牛爷在欲望洪流的艰难和机智。“他虽年愈八十,却中流砥柱。哪怕众叛亲离,他也要坚守底线和情操。他孤独一生,也清白了一生。他是上岭村形单影只的男人,也是有情义的男人、最长寿的男人。”淳朴厚道,乐观乐生。
凡一平为我们勾勒了上岭村不一样的乡土和乡土之上的风景,他不止于旧乡土写作关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不止于对国民性的批判,而是着眼于新乡土对文明的向往。尤其,乡土中国的变化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凡一平发掘出这个变化。尽管贫苦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无论如何,淳朴厚道和乐观乐生却是上岭人的常态,也是上岭人的精神。因此,他不断重写和发现现代上岭,也不断重写和发现历史和当下的乡土中国,更钟情于现代乡土中国的新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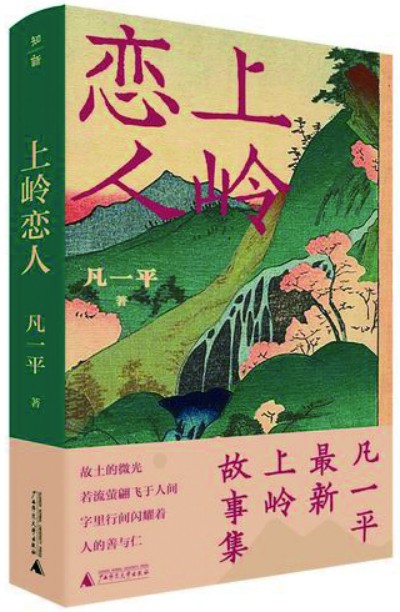
其次,《四季书》也是作者上岭村系列的情感之作。其叙事之新,在于作者不是乡土的访问者,而是乡村之子,或者说有一颗故乡赤子之心,既有故乡之情(他大多数作品都是从故乡出发),更有历经文明教育之后回望者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所以,凡一平的叙述不同于一般游子还乡的乡土叙事,而是以同情理解的文心,以与人物对话的平视切入,在日常生活的、历史的、文化的乡土叙事中,不断通过现代与传统、中国与世界的碰撞融汇,走出一条新的乡土文学的叙事之路,并练就了自己的叙事腔调,这相当不容易。于是在《四季书》里,凡一平调动过往的文学经验,不再沿用他过去长篇小说的线性结构,而是巧妙地选取主人公韦正年生命中的重要年份,以四个季节、四个章节结构着人物的命运和故事,颇具叙述策略。
《四季书》小说从冬季写起,以韦正年死而复生起笔,仿佛预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于是,故事人物有了生机,叙述平实沉静,哀而不悲。开卷没有令我们失望,徐徐打开一幅有活力的乡村冬季图,凡一平停下过去故事追故事的脚步,从容淡定地白描工笔,图中多了过去凡一平作品少有的精细和山川风雨,多了南方蓬勃的万物生灵,植物、喀斯特岩洞,成群结队的蚂蚁、野狗、乌鸦,尤其在壮民族图腾青蛙神奇护佑下,五岁神童不仅重获生命,还新生特异功能一对神奇的眼睛。韦正年从开天眼的神奇,走向腥风血雨的百年岁月,走向大地的冬夏秋春,走向接受一切也超越一切(包括为属下、为战友受难与忍辱负重)的世道人心,走向澄明之境,聪慧至善,坚定英勇,清正而圆满。韦正年走过的一生,立体地凸显了广西百年的山乡巨变,凸显了百姓百年的人间烟火,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近百年的人间镜像与时代镜像。
是的,《四季书》饱含作者的赤子之情,深沉叙述着韦正年的出生入死,亲人们一一离去又纷纷回来……隔阂20年的儿子女儿相继回来,认父亲了。如果说父子相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儿子上江以爱救醒了韦正年,而父女相见就更细腻真切,也更感人了。“韦新梅的眼睛一瞪。眼泪瞬时就冒出来了,快于她的呼叫:爸。他们就地搂抱、啼哭,在县委大院,在苍翠的云松树下。有好长一会,他们只仅仅搂抱,只知道哭,像两个哑巴,通过搂抱和哭来表达彼此的想念、委屈、爱与和解。父亲的胸膛和肩胛雄厚、坚强,他的哭声苍劲、凄凉。女儿的头发、脊背柔顺、秀美,她的眼泪寒冷、晶莹。终于知道说话了。接受拥抱的父亲退后一步,像是为了方便女儿看他,他也要好好看女儿。”这份情感不仅长于上岭人的空间,还融入了作者生命中重要的时空,一个个细节更显示出作者的深情:何菊是复旦大学生,对应着凡一平复旦作家班学员的出处,当年入学后第一件事,也是像恋爱中的韦正年何菊去扫鲁迅墓。还有,那些作者人生的重要场所、事物,如《上海文学》、柳州螺蛳粉、治病的上岭岩洞泉水、从省报记者到广西文联资料员的郑亚琴、电影《刘三姐》版权纠纷、随时都会滚落的上岭的石头隐患,乃至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等,关于历史的大量个体记忆烙印,涉及韦正年长达80多年的人生,凡一平把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揉在一起,使人物成为现代乡土中国的一个鲜明形象。
第三,《四季书》可谓是作者上岭村系列的戏剧之作。在此,凡一平继续自己的叙述腔调,继续其富于传奇性、戏剧化的表现手法,常常采用浅焦镜头描写人物、悬念式的叙述手法、蒙太奇和嵌套式的结构、散文化的旁白,富于画面感,机智幽默,引人入胜。小说的叙述以时间线来体现人物一生的不平凡,那些对人物意义非凡的年份按季节结构,以蒙太奇手法,跳跃在不同年份的不同画面中。凡一平的浅焦镜头,焦点很浅,但镜头清清楚楚直接对着主人公韦正年,他身后的背景——他的上岭村以及景深部分多是模糊的,就像描写晚年的他出狱时为何孤身一人,镜头移动才把虚化的部分倒叙,传达出背景的社会和家庭的变故,以及人物和作者的世界观所展示的现实,深刻凸显了主人公一个人的直面担当、至善至义和沉郁忧伤。凡一平清楚地知道以此强调韦正年人生的坎坷, 专注于一个主题,即韦正年的人生四季,使不同年龄的读者可以在这些年份里,联想到发生在各自身上或身边的事情,看到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既共情共鸣,又深刻宽广。
以浅焦镜头突出悬念的叙述手法,常见于凡一平的作品。比如,《我们的师傅》开头:“我们的师傅死了”;《顶牛爷百岁史》第一句:“顶牛爷八十一岁这年,飞来横祸”等等。开卷就引人入胜,颇具艺术张力。可见,善于把图像思维化用到自己的文学写作中来,凡一平是幸运的;而更重视小说叙述的绵密和内敛的艺术魅力,可能又是凡一平需努力的。
是的,凡一平小说与影视有着互文的意义,这也影响着他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美学形态。我们知道,电影《寻枪》《理发师》等的文学母本都源自凡一平小说。这令人联想到话剧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整体性的意义,如现代文学的曹禺和老舍,如当下的牟森话剧《零档案》《一句顶一万句》《红高粱家族》有着经典性的中国当代文学母本,分别出自诗人于坚、小说家刘震云和莫言。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文学性的漫溢或者蔓延,溢出我们原有的那个固定的小说、散文、诗歌那样一种纯文学的类别界限,它正在向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门类蔓延,甚至远大于文艺起源时诗乐舞的三位一体,文学性的泛化已是新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有论者提出要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一种行动和实践,理解为一种不断的生成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学、对文学性有一个新的开放性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也需要做更好的自己,以开放的、双向赋能的姿态拥抱各个艺术门类。
是重新考虑把戏剧文学回归文学版图的时候了。当下,不少学者都在做拓展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构建一个与传统中国文学史贯通相契的结构体系。比如吴俊的四维视阈说,他把翻译文学重纳文学版图;比如何平关于戏剧文学重归文学版图的倡导等等。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学科细化的纠偏,狭义性的细化其实是伤害文学创造力。
年轻时代受分工精细影响,我一直认为作家过于参与影视不仅会失却文学的叙事魅力,还会极大地消耗作家的才情和资源。重新考量史识和现实,以今日之我,超越昨日之我,这也是我个人新的选择和学习。
今天,凡一平不仅以小说虚构、揭示和反思巨变中的现代乡土中国,及其乡情的世俗社会和人间烟火,也自我检视反思并不断精进,获得“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平衡能力和理性自觉,在雅俗之间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以及自己的广泛读者群。显示了诗人出生的凡一平既沟通小说与影视,又融琴棋书画于一家的多才多艺,以及与多元化文学格局的契合和破圈的艺术创造力,多向赋能,独此一家,凡一平终于百炼成钢。
(作者:张燕玲,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书籍作者:凡一平)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