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是诗人胡弦的一本主题性诗集。如同诗集的封面所提示的那样,这是一部书写、吟咏大运河的作品:“追寻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探究那流淌的活着的运河文化。”但是,与当下已经成为重大主题写作热门题材的大运河作品不一样,该书没有想象中的惯性书写,更没有阅读期待中已经成为定势的语义表达。准确地说,《水调歌头》的重点是“水”,是以大运河为中心的“泛大运河”写作。因此,它没有许多大运河作品那样看上去严谨或从古到今的时间结构,或从南到北的空间结构,而是从诗人理解的大运河的人文精神着眼,从这次主题性作品的书写性出发,确立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在外观上又显得随性的诗性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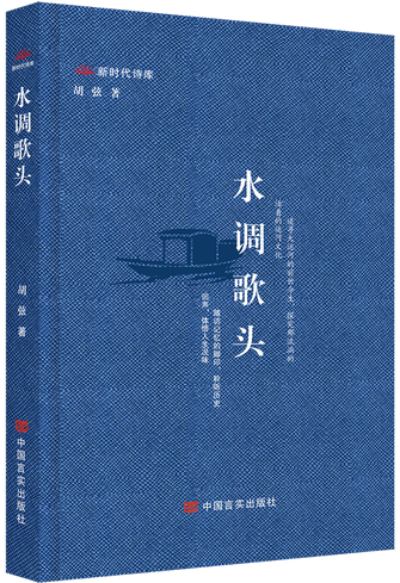
作品以《庇护》为起始,不但定义了大运河的人文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我们在大自然中安家,/在河流拐弯处安家,/在险处狩猎,在平处种田,/在儿孙的繁衍中忘却时间。”从而也为作品的整体表达定下了基调:“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一个/所有碎片般的手寻找和散去的地方。”最后闭环于《流变,或讲述的尽头》,诗人用开放的讲述为这次书写按下了暂停键:“如同生活在答案中,所有问题都像小小的漩涡,/已被流淌随手解开。繁华,一程又一程,/无穷尽,一座青山做了上阙,必有/另一座青山愿意做下阙。”诗人知道,或者说在他的设计里,讲述或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更无法抵达所谓的终点。“所有讲述,都像是对/无法再触碰的讲述的讲述。”因为“讲述的尽头,是语言/建造的另一座博物馆。/而摆放在博物馆里的一艘帆船,/却早已穿过千山万水,静静泊在/那些失踪的情节里”。在这起讫之中的是自由而洒脱的灵性书写。限于篇幅,即使从下面列举的一些诗题中也可以想象出作品的内容,这些内容既与大运河有关,如《压舱石》《临流而居》《断流,或步道开始的地方》《在游船上,又舍舟登岸》《江都的月亮》《垂钓研究》等等,又似乎与大运河无关,如《器识》《大麓记》《寻墨记》《画卷录》《沉香》《鼓》《酒变》《醒木》《青瓦颂》《秘境》《寻味记》等。胡弦的话题或开始于运河,或结穴于运河,在收放之中,他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大”运河,一个“大”的运河,一条似是而非的运河。
胡弦瞩目于运河已非一日,至少从2019年的《运河活页》就已经开始了,这组诗有20多首,大体上是以空间来结构的。第一首《传说》可以作为引子,然后是《咖啡馆》,这首诗又题《杭州,咖啡馆》,接着是《史公祠》《镇江,运河入江口》等等,一路北上,直到《北京东四十条,南新仓》《积水潭》,基本上依照“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完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叙事。最后以《骑行》作结,如同电影的尾声一样,将镜头从对历史的追忆切回到现实。大概也是从这组诗开始,胡弦有了对大运河进行大规模写作的野心。而《运河活页》可以看作这个项目的一次试水,一个诸多方案中相对成型的“底稿”与“小样”。看得出,这个小样的思路还是常规性的,没有走出人们对大运河书写的直觉性考虑,那就是将具体的大运河作为表现对象,以时空为线索,一路铺陈开去。现在,这组诗经过增删修改后以《活页》为题出现在了《水调歌头》里,一个本来完整的大运河书写现在成了大运河作品中的一章,整体的、具象的大运河成为新方案中的一个单元,可见胡弦的大运河诗学构思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胡弦的大运河写作跳出了具体的大运河。
大运河不仅仅是历史与现实中的“京杭大运河”,它在胡弦新的认知视野中被重新解读了,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大运河成为一个庞大的水系,而从诗性上说,大运河是一个意象,被充分审美化、人文化了。这是对大运河诗歌写作的解放,由此,写作对象不再是大运河从古至今流过的一个个码头,而是与大运河有关的意义成为胡弦这部长诗的核心与线索。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博物馆式的知识性写作,也不是大运河经济与政治的全景式叙述,而是生活,是“河”的存在,是“水”的精神,是因“人”而生的生命景观,是凝聚在“物”上面岁月的斑痕,是大运河古往今来历经沧桑、病蚌成珠的一面面镜像……虽然,相对于实体大运河提供的时空线索,这一构思看上去显得松散,但是,它却在更高的人文精神层面获得了审美的统一,并且在开放的语义场域建构了富有吸附力的召唤结构。
这一书写方式还有价值不菲的审美增值,那就是对长诗的认识与实践。因为《水调歌头》的诗性结构不仅存在于这部作品的整体性上,而且同构于这次大规模写作的局部,同构于它的不少长诗创作上,从而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的阐释循环。从作品中的《压舱石》《临河而居》《莫须有的脸》《画卷录》《江都的月亮》《秘境》等诗作上都可以看到胡弦长诗创作上的新意。长诗从写作上说是一个大工程。中国现代诗的长诗传统并不成熟,更谈不上坚固。如果说短诗大抵上形成了与古代诗歌具有本质区别的形制与审美特质的话,那么长诗则还留有许多古诗与民间叙事诗的审美残存与艺术惯例,而且一旦进入长诗的写作实践,还会受到其他文体的干扰。几乎所有叙事性文体都可以对长诗指手画脚,比如结构、线索、节奏、组元等等。所以,长诗一方面是对诗人积累、能力、耐力甚至抗击打能力的考验,也给诗人提供了一次思考、创新甚至蜕变的机会。
胡弦这些年来一直在琢磨长诗,也在一些作品包括小长诗上有不少心得,但近年来较为成熟的还是《水调歌头》中的这批作品。它们在内容上挣脱了传统长诗观念上的束缚,摆脱了叙事对长诗的纠缠,它们告诉我们,通过联想、想象与发散性思维,照样可以结构出长诗,除了人物构件与事件构件,意象、情绪、理念等都可以成为长诗的组件,也都可以支撑起长诗的结构。尤其是对一些具体写作对象的把握与处理,我们如何化实为虚、化整为零,如何摆脱外在的形而下的束缚,进入事物的内部,对事物进行形而上的解读与表现成为关键。包括在体式上,像《江都的月亮》何其洒脱,古今交融,从宫廷到市井,从帝王将相到平头百姓,化用戏剧元素,将旁观者、叙事人、角色与扮演者进行视点上交叉变换,切换、并置、虚拟、空白……在真实与虚拟中撑起巨大的话语舞台,众声喧哗,在建构与解构中筑起意义的迷宫。而《临河而居》《莫须有的脸》等作品中“副歌”的加入,则颠覆了长诗传统的严谨,开辟了诗作主体以外的疆域,甚至改变了主体的抒情方向,复调之间的张力建起了更具挑战的阐释空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新的“长诗思维”。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水调歌头》在运河题材诗歌表达上的新意,更要看到它对胡弦的意义、对当下诗歌的意义,正是这一类长诗创作的过程使胡弦的诗歌产生了许多新质,而且,这些新质既因这部主题写作而起,却又不止于此,不止于长诗文体。它们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建设性可能在今后还会更加显现出来。
在当今中国诗歌界,胡弦是一位执着于语言、甚至有些唯美的诗人,他信任语言的力量,能够用语言击穿事物,又能以语言之力使事物飞扬。因此,他的诗歌世界是内敛、纯净、结实而空灵的,他总能以语言重塑经验,使其陌生化。胡弦的诗歌有着内在贵族气,从不迁就,他是一位有诗歌洁癖与诗性自律的诗人。正因为如此,《水调歌头》对胡弦而言具有标志性,他让我们明白,只有解放世界才能解放自己这个道理对诗歌写作同样有效。也就是说,《水调歌头》不仅解放了大运河的惯性写作,更解放了诗人自己,呈现了诗人新的可能性。《水调歌头》让我们惊讶,因为我们看到了诗人行走在大地上,下沉到日常生活中,在烟火缭绕中探寻历史、社会、自然与生命的秘密。如果说以前的胡弦是节制的,那么《水调歌头》则呈现出少有的放松。本来,胡弦就自有其力量,所以当手下的缰辔稍微一松,立马就带来了奔腾、雄阔的气象。
胡弦说:“相对于熟悉的生活与作品,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地带,一直是我的追求。或者说,我重视的是一直是‘感觉’——相对于既有,我试图感觉那‘缺失’的部分。”《水调歌头》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解。
(作者:汪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