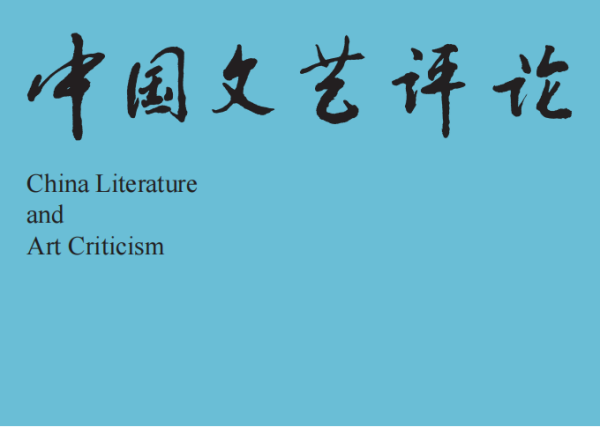
【内容摘要】 话剧《惊梦》是近期在国内各大城市巡演并取得较大成功的一部作品。《惊梦》通过昆曲大班和春社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段戏剧性演出经历,把中华文明古典文化的美学形式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革命文化的美学形式在一个具体的戏剧性事件中结合起来,较为成功地把已经程式化的美学形式在戏剧演出活动中重新激活,从而呈现出具有当代性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惊梦》的创作是成功的。另外,作为《惊梦》的一种艺术追求,编导用喜剧化的形式来表达和呈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悲剧性冲突,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艺术探索,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值得学术界重视。
【关 键 词】 《惊梦》 《白毛女》 悲剧的喜剧化表达 话剧评论

2023年6月1日,笔者在中国海洋大学讲学,晚上在青岛大剧院观看了话剧《惊梦》,有些感受和随想。陈佩斯是笔者年轻时十分喜欢的喜剧演员,他在春晚演出中曾经表演过《吃面条》(1984)、《主角与配角》(1990)、《警察与小偷》(1991)、《姐夫与小舅子》(1992)、《王爷与邮差》(1998)等小品,令人难以忘怀,这些都成为笔者生命中十分深刻的记忆。那几年笔者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对未来充满憧憬,陈佩斯的喜剧以特有的普通人的幽默,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情感结构的一部分。
话剧《惊梦》以一个戏迷的自我炫耀开场。在中华文化中,戏剧是一种民族特征十分鲜明的艺术形式,在仪式化和程式化的基础上,中国戏剧具有十分突出的形式化的特征,成为许多票友的人生乐趣。《惊梦》的开场明确地告诉观众:戏剧本是一个有钱和有闲的人们把玩的世界。当枪炮声突然响起,一场大战猛烈地撞向平静的中原大地。
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佩斯饰演的昆曲大班和春社班主童孝璋,为保戏班上下一大家子的口粮生计,特率众人绕道来平州(一个虚构的地名)演出。他们刚踏进平州,一场激烈的拉锯战骤然打响——计划好的演出和东家的酬劳、口粮立时化为泡影。本为活命而来,却瞬间命悬一线,老班主一筹莫展。
就在此时,一线生机意外传来:刚刚解放了平州的解放军部队慕名上门,诚意省出粮食邀请戏班排演一出劳军大戏。看着质朴的小战士热情地将救命粮一股脑儿地送到门口,老班主感动在心,当下便满口答应。不料,拿到手的剧本是出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新编现代歌剧《白毛女》,对于一个传统昆曲剧团而言,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既没有人能唱,也没有人愿意演。老班主童孝璋用古训教育戏班演员:我们在舞台上演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要讲信用和规矩。没有诚信和规矩,戏班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没有了。在战乱的条件下,戏班仍然坚守中国文化中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规矩),显现了一种现代生活中的崇高。在戏班中两位老生借故拒绝演出之后,老班主担纲《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率众人竭尽全力,艰难地完成了编排。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老班主童孝璋因为把《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演得太坏了”或者说“演得太像了”,被观众中的战士开枪打伤。舞台上的陈佩斯/黄世仁的表演充满了喜剧性,红色经典《白毛女》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了。生活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竟然是以融为一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在《惊梦》中,听到剧中剧社要演出的剧本是《白毛女》时,笔者心中暗暗吃了一惊,也燃起了很大的悬念:这个以演传统昆曲为业的戏班,如何在舞台上呈现现代形态的新编歌剧《白毛女》?这样的拼接和嫁接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呢?在舞台上,我们看到演员的拒绝和挣扎,《惊梦》用舞台关系颠倒的方式,将剧场演出虚拟化,让剧团其他人员以边看戏边议论的方式,将演员变成观众,我们这些现实中的观众一下子获得了俯视某种现实关系的“上帝视角”。在我们这些观众的想象中,以昆曲的唱腔和舞台表演程式表演性地呈现出《白毛女》的叙事和情感的逻辑,在一瞬间,历史、传统、古老的仪式和当代语境的叠合关系都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融合在一起,不仅传统的“昆曲程式”变成了新仪式,而且人的革命性改变也具有了某种复杂而丰富的意义。这种“程式化”的编剧和表演形式,事实上把叠合着的多重不同的文化语境戏剧性地呈现出来,使《白毛女》获得了新的意义,《牡丹亭》也获得了新的意义。这种新的复合性意义,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在《白毛女》中,通过“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情感逻辑和叙事线索,把压迫、掠夺、革命、爱情、解放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悲剧”,在革命进程中实现了人的解放和改变。
第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欣赏园中春天美景而情窦初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触景生情。自然青春生命的美好艳丽,与现实生活的禁锢锁闭,使杜丽娘的浪漫主义冲动只能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呈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理想的爱情之不可得,阻隔之网看不见摸不着,却深不可测,十分强大。殉情的悲剧终于感天动地,使“鬼”得以转变成人,而且获得了极其幸福的美好姻缘。这是一个世俗世界把怀春痴情的美少女变成“鬼”,众神仙齐努力,使阴间鬼魂再获新生的“传奇”故事,用“惊梦”的戏剧形式,把梦幻中的想象与现实中的存在结合起来、缝合起来,人间不可能的事情,在众神仙的帮助下转变成真切的现实生活。《牡丹亭》是一个中国古典悲剧的典型案例:现实中的爱情在戏剧中仪式性地颠倒,以实现现实中不可能获得的幸福,当然这是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得以实现。

话剧《惊梦》演出照
第三,当代话剧《惊梦》在舞台上、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情感逻辑和戏剧叙事程式巧妙地缝合起来,这种缝合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审美变形:在戏剧中,将杜丽娘与柳梦梅活活拆散的“坏人”——这个一直被历史的复杂现象隐蔽起来的“仁者”被历史地还原,黄世仁作为喜儿转变成“白毛女”的历史黑手被曝光在舞台中央的强烈灯光下,历史真相的呈现,产生了强烈的情感震荡。观众席上的解放军战士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是国民党将士,包括和春社的演职员们都因为这种情感冲击而产生了某种改变。童孝璋则因为把黄世仁“演得太坏了”而两次被观众开枪击中受伤。在这里,戏剧因为它的“艺术真实”而从虚构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昆曲戏班和春社因此也走出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困境。生活中的悲剧因为戏剧性的叙述和改编而显现为喜剧性的形态,这是《惊梦》出彩的地方。
《惊梦》的演出并没有结束。平州战事继续,而且愈来愈激烈。十分有趣也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交战双方的指挥官均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曾经都喜爱昆曲,他们在平州这块土地上为了各自的人生理想展开了一场决战。
不久,装备精良、气焰高涨的国民党部队夺取了平州。为了庆祝胜利和鼓舞士气,其长官找到了和春社老班主,要求排演一场劳军大戏。在对不同话语体系相叠合造成的误解之中,长官们一致决定上演的剧目也是《白毛女》。历史老人在拿当事人开玩笑了。在这一个叙事阶段,《惊梦》剧情的推动因素从解决吃饭问题到在战乱中挣扎着活下去,转换为不同境遇中的各类人物对美貌和爱情的追求:地主儿子常少坤一会儿疯、一会儿痴地追求着和春社花旦童佩云,国民党军官挟战场得胜者之威苦苦追求着花旦童佩云,和春社台柱子之一的小生何凤岐与童佩云青梅竹马的恋情在战火纷飞中也迎来了一系列变故和生死考验……
昆曲版的《白毛女》如期上演。仍然是和春社的演职员们作为观众在观赏着“新昆曲”《白毛女》的“想象性”演出,仍然是我们作为观众有机会获得局外人和“上帝视角”而生长出一种优越感和审美愉悦。“砰”的一声,枪声又一次骤然响起。慌乱中几天前刚刚“中弹”的“黄世仁”被一众演员簇拥着来到前台,“黄世仁”再次“中弹”,这次子弹是国民党军官射出的,把“黄世仁”的帽子打飞了。童孝璋万分恐惧,难以承受。早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就说过,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虚构性和程式化演出的《白毛女》因为和春社老班主童孝璋将黄世仁“演得太坏了”或者说“演得太像了”,而两次被现实中的将士、而且是现实中处于对立和激战中的战斗者分别拔枪射击。历史中复杂而诡秘的某种“基源性幻象”,以这种十分“陌生化”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笔者看到青岛大剧院歌剧厅的观众席上,有的观众泪流满面,有的观众则大笑不止。
《惊梦》的演出仍然不慌不忙地继续着。枪声响起后,《惊梦》的演出现场自然一片混乱,本来作为“战前动员”而组织昆曲《白毛女》演出,不料,观众中两个营的士兵因观剧而乡愁病发作,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的“喜儿”去了,致使长官大发雷霆、追究责任……
《惊梦》中的“平州战事”以国民党军战败、主帅掏枪自杀、解放军主帅中弹身受重伤,在送去后方医院前掏出几十年前和春社在他家演出昆曲的剧目单托人转交给和春社班主童孝璋而告终。童孝璋悲痛欲绝、仰天长叹。于是,和春社郑重决定:为所有在平州战事中死去的将士亡灵举行一场隆重的祭奠仪式,献上的是昆曲《牡丹亭》。在美轮美奂的《惊梦》表演中,大雪悄然落下,漫山遍野,大雪纷飞,古城肃立,梨园之曲回响,悠远而绵长。英灵不孤,戏剧再次成为仪式。吾等众人则“惊梦”于苍然回望中的《白毛女》和《牡丹亭》的优美化呈现……
如果说昆曲《牡丹亭》是中国传统悲剧,《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悲剧,那么,《惊梦》也许是一种新的悲剧类型。该剧由喜剧演员主演,戏剧的表演过程充满了各种喜剧性元素,但是戏剧情节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冲突却是悲剧性的,这种反讽性的悲剧显然是一种具有当代性的悲剧新类型,在理论上值得当代学者关注。
中国美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西方学者从雅斯贝斯、黑格尔,到当代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肯尼斯•苏林都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中国学者从鲁迅、胡适到朱光潜也都认同中国没有悲剧。这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我们在文化上不自信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作为一个产生了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曹雪芹、鲁迅、曹禺、冼星海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中应该有自己对人生悲剧性现象的思考和艺术的表达。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信仰体系的不同和文化表征机制的不同,导致对于悲剧观念的表达和悲剧形态的认知会存在着较为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华文明对终极关怀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人生境遇中不可化解的悲剧性冲突的解决方式和途径,的确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存在着某种不同。
在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农耕文明中的“自然”和“天”的观念被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在“天”或者“道”的层次上,“阴”和“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生命中的悲剧性或者说不可解决的矛盾不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命运”或者“性格”,而是来自“妖怪”“非人类”或者“坏人”的干扰和破坏,使人间的正常秩序被打破或颠倒,使现实中滋生出不可化解的悲剧性冲突。在《牡丹亭》中,怀春少女不能实现世俗性的婚姻,抑郁而死,变成了“鬼”;在《白毛女》中,喜儿因黄世仁(谐音“不是人”)的欺压而变成了“白毛女”,人的正常生命都被巨大的外在力量摧残而极度异化。在中华文明中,悲剧冲突的存在就像自然机体会患病一样,悲剧性作品的演出就是用悲剧性表演“震惊”在尘世中陷入迷途的人们,让他们在“惊梦”中觉醒,去勇敢地面对自己或者社会机体的疾病,从而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观看悲剧演出就像病患服药一样,只有相信药到病除才会愿意服下“苦口良药”。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悲剧作品中,正义、善良、美好、和谐等总是以某种极端化的方式呈现出它的必然性存在,是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受到“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哀伤?”(马克思引用歌德的诗句)的一种十分悲壮的历史悲剧性。
我们认为,中华文明是有强大悲剧观念的文明,但不是一种静态的祭酒神仪式性的悲剧观念或者悲剧文化,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是在一个更高、更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层面上,现实中不可化解的悲剧性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和想象性解决,从而呈现出喜剧性的形态。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中,“绝地天通”的悲剧性冲突和“断裂”是在“天人合一”的总体性文化框架之内的。正如人类学家张光直的研究所表明的,在中华文明的艺术表征中,断裂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断裂,个体或具体现象的毁灭,并不意味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毁灭。杜丽娘因“怀春”而悲惨地死去,但是杜太守的政治生涯和社会治理仍然正常地发展;书生柳梦梅的发愤读书也在波澜不惊地进行中,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杜丽娘个人的悲剧并不意味着整个宇宙的崩塌。与此相类似,《白毛女》中的喜儿,虽然在黑暗的社会中被巨大的力量摧残,但是不合理的恶势力因为它的反人性以及严重的不合理性,终于被正义和光明所战胜,在“换了人间”的条件下,喜儿获得新生,并最终完成了报仇雪恨,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由于社会结构的重要区别,《牡丹亭》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古典悲剧的经典形态,《白毛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孕育出来的中国现代悲剧,在“中国式悲剧”的范畴下,它们是中国悲剧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类型。当代话剧《惊梦》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这两种已经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悲剧观念在一个当代语境中以“平州战事”为叙事框架叠合在一起,结合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语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激情化的想象中,在对“历史的必然要求”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有了一种“蓦然回首”的历史优越感的情境中,将黄世仁置于叙事的中心而反复暴力“抽打”。因此,在《惊梦》的结尾部分,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美丽形象和程式化的戏曲形式在演唱和表演的一瞬间里,“平州战事”的叙事形式与我们当代生活语境相结合,使昆曲《牡丹亭》的表演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审美意义。在这里,“历史的必然要求”不再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而是在悲剧的喜剧化呈现中,用戏剧的形式把美好而必然会实现的“未来”朦胧地呈现出来。就像杜丽娘在春天的“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中“惊梦”般感受到美好生活一样,观众席中的我们,在《牡丹亭》的场景和唱腔中,在漫天大雪的肃然仪式中,感受到历史的责任和人类美好感情的强大力量。

话剧《惊梦》演出照
在歌剧《白毛女》首演将近80年之后的新时代文化语境中,话剧《惊梦》用喜剧的方式呈现出一个悲剧性的现代故事,把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期早期阶段的新型歌剧《白毛女》与中国传统戏剧《牡丹亭》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悲剧形态:悲剧冲突的喜剧性呈现。就像给苦药加了蜂蜜一样,《惊梦》为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直面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中,中国文艺现代化在悲剧的形式和表达机制方面也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延安时期鲁艺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用“乡愁乌托邦”和革命的乌托邦的激烈冲突表达了“革命悲剧”(历史悲剧)的崇高感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话剧《惊梦》把中国式“现代悲剧”中的中华文化基因进一步激活,用“悲剧冲突的喜剧化表达”,把“历史的必然要求”难以直接实现的崇高表达出来了,同时也把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必然会实现的美学逻辑表达出来了。只要“梦”的要求是合理的和美好的,它就总有一天会实现。这是昆曲《牡丹亭》的叙事逻辑,也是当代话剧《惊梦》的情感逻辑。
离开青岛大剧院的《惊梦》演出现场已经二十多天了,昆曲大班和春社的经历和演出中的场景一直在笔者脑海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笔者想,戏剧真是一个奇特的艺术形式:和春社作为战乱时期昆曲艺术的守护者,童孝璋的形象是崇高的,也是悲剧性的,在“戏中戏”里,童孝璋表演“黄世仁”,因为把黄世仁的“坏”演得“太像了”而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开枪射击。历史因为复杂和阴差阳错而呈现出了喜剧性的特点,在笑声中,观众与黄世仁的“坏”告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不时会遇到黄世仁一样的人物,笔者十分好奇,他们会不会去看《惊梦》?他们会不会在“坏人”的生活轨道中惊醒呢?……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左联’文论及其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杰 单位: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8期(总第95期)
责任编辑:王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