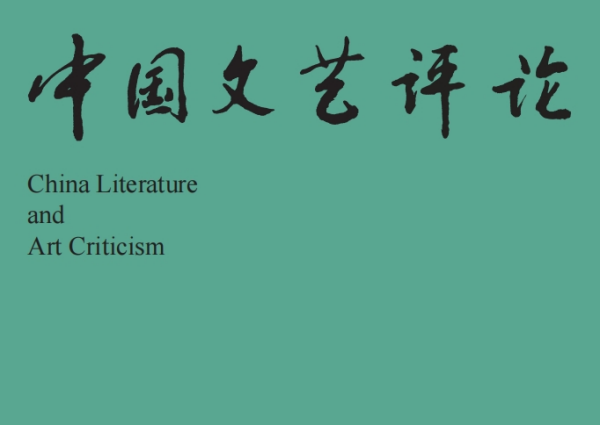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在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文艺界涌现了一大批展现新时代崇高之美的精品力作,广受人民群众喜爱和好评,但同时存在着调侃崇高、扭曲经典,脱离人民群众等问题。为此,本刊以“崇高之美的时代表达”为题,约请专家学者从新时代文艺在美学层面上的崇高表达这一角度切入,结合代表性文艺作品,挖掘并阐述新时代崇高美的样式与特征,彰显新时代文艺对崇高之美的追求与张扬。
论崇高范畴的形成与新变
【内容摘要】 崇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美学范畴。它源于古代,定型于近代,推动了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并在当代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崇高范畴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当代重新审视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推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发展。
【关 键 词】 崇高 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先锋派 当代性
崇高范畴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考察崇高:首先,崇高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相似的概念。其次,现代美学体系,正是由于崇高范畴的确定而得以形成。欧洲人对自然的一种超出田园式的欣赏,是与崇高范畴联系在一起的。在欧洲艺术从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而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崇高范畴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在当代社会,“崇高”的思想渗透到自然、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面对当代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社会变化,崇高范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新的意义。
一、作为一种风格或境界的“崇高”的形成
在欧洲,最早的“崇高”形象也许要从神话时代说起。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为人类而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勇猛无比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犹太神话中的摩西、大卫,都是崇高的形象。中国神话也是如此,射日的后羿、逐日的夸父、怒触不周之山的共工、补天的女娲、填海的精卫、移山的愚公、治水的大禹,等等,都以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和激励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崇高”的历史极其久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
但是,与美构成对立的崇高作为美学范畴的形成,却要晚得多。面对自然中的各种环境和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欣赏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试图对这些感受进行分类,则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大致说来,是先有美以及相应的美感,后来各种偏离美的感受汇聚起来,而形成崇高感,并因此形成崇高的范畴。
在欧洲,崇高一词来源于一本书,这就是古罗马时期被冠名朗吉努斯的《论崇高》(Peri Hypsous)。朗吉努斯的这篇文章是用希腊文写的,Hypsous的意思是“高”。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有很多考证文章出现。有说法认为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作品,也有说法认为这是公元三世纪的作品。在残留下来的手稿上,注明作者是朗吉努斯,究竟是哪一个朗吉努斯,也众说纷纭。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是公元三世纪的卡西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但近年来有人挑战这种说法,认为更可能是公元一世纪的丢尼斯•朗吉努斯(Dionysius Longin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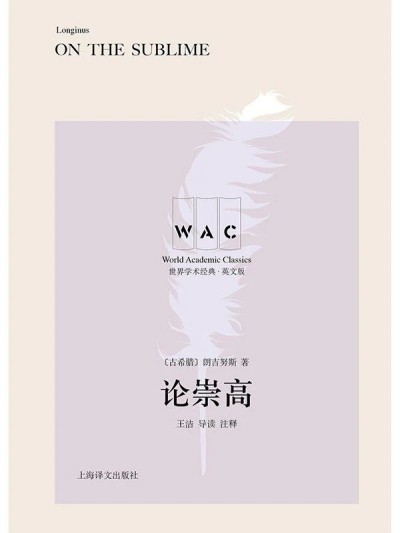
[古希腊] 朗吉努斯著《论崇高》
从希腊文的hypsous,到拉丁文的sublīmis,到法语和英语的sublime,再到中文的崇高,都各有其译名多样并最终被选定的过程。在古罗马时期,朗吉努斯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被不少人提过,应该是很有名,但后来就丢失了。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公元十世纪的抄本,据说后来的各种版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这个版本。到了16世纪,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三个以希腊文原文出版的版本,即1554年在巴塞尔、1555年在威尼斯和1569年至15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版本。同时,也有一些拉丁文的译本。拉丁文译成sublīmis并非是自动形成的,在当时也有不同的译法,如译成相当于grand、height、great、loftiness等,后来才逐渐统一起来。
朗吉努斯的这篇文章,论述了崇高风格构成的五个源泉:“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这两个崇高因素主要是依赖天赋的。其余三者则来自技巧。第三是构想辞格的藻饰,藻饰有两种:思想的藻饰和语言的藻饰。此外,是使用高雅的措辞,这又可以分为用词的选择,象喻的词采和声喻的词采。第五个崇高因素包括上述四者,就是尊严和高雅的结构。”要实现崇高的风格,必须要有天赋与技巧的结合。这里所讲的五点,前两点是伟大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第三、四点讲辞格的藻饰和高雅的措辞,第五点则是前四点的结合以形成的尊严和高雅的结构。这种对崇高的描述,是针对诗而言的,但又给后来的人留下了多种阐释的空间。
在这里,崇高是指伟大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要有天赋,而且要有技巧。汉语用“崇高”两个字来翻译the sublime,这是现代形成的。王国维在翻译时用的是“宏壮”或“壮美”,朱光潜、缪灵珠等人的翻译才用“崇高”。谁是最早用“崇高”两字来翻译sublime的,这还需要作一番考证。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个翻译很合原文,不管在希腊文中,还是在拉丁文中,都强调了“高”,强调具有“高大”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也有“崇高”使用的记载。《国语》中记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这里在说,楚灵王建造章华之台,请来了伍举,问他台美不美。伍举反对靡费钱财,批评说,不要以台的“崇高”为美。这里是在说,楚灵王以台的“崇高”为美,而伍举说太费人力和财力了,不要以此为美。值得注意的是,不以此为美,不等于不美,而是说,审美要服从于伦理,这种美固然是美的,但太靡费钱财和人力,以此为美不妥。在《周易•系辞上》有“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这里指的是人的地位富贵而“崇高”,像日月一样耀眼。这两处都用了“崇高”两个字,但它们与今天作为sublime一词翻译的“崇高”在意义上是不同的,这也类似于古代中国用“艺”和“术”字,但不用来指现代艺术概念。
中国古代常常用单个的字来表达概念。与“崇高”概念接近的,主要有“大”字。孟子有一段名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在这里,他作出了“善”“信”“美”“大”“圣”“神”的六等级之分,“美”与“大”都作为形容词被命名,分别表明具有伦理性质的两个等级。《庄子•知北游》中谈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被用来形容“美”的一种。
除了“大”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不少类似于“崇高”的词,例如,刘勰《文心雕龙》中讲“风骨”,谢赫《古画品录》中讲“骨法”,司空图《诗品》中讲“雄浑”与“劲健”、“豪放”与“悲慨”。这一类概念在后世越来越丰富。古代中国人受“阴阳”相对而相生的思想影响,从而很早就有了类似于“崇高”的“阳刚”美学传统。这种传统构成了中华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
二、美学上的“崇高”范畴的形成
前面说到,朗吉努斯的这篇文章,在16世纪开始重新流行,有了几个希腊文的印刷本,又有了拉丁文翻译,并在那不勒斯等一些地方出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575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这本书的意大利文版。在英国,也开始有人关注“崇高”概念,例如弥尔顿在他的诗中提到这个概念。
朗吉努斯的这个概念在近代受到重视,与法国文论家布瓦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布瓦洛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者,他的《诗的艺术》一书成了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经典。他还将朗吉努斯的这篇《论崇高》译成了法文,使这篇古代文献在启蒙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他为这篇翻译所写的译者序言中,却展现出一种对崇高理解上的进步。朗吉努斯重视崇高的语言、修辞手段的运用和结构,以及它们与思想和情感的结合。布瓦洛则认为,崇高的风格还不是崇高本身。崇高存在于单一的思想、意象和转折之中,存在于重大的、辉煌的事件之中,也存在于简单而朴素的语言之中。
在这篇序言中,他特别强调书中的一句话,即《圣经•创世纪》中的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指出这句话无比崇高,却没有华丽的词藻,也不具有高昂的声调。真正的崇高不依赖于修辞,而在于其思想和意象本身。布瓦洛的这一论述意义深远,可总结成一句布瓦洛的名言: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伟大的思想构成最高形式的崇高。
布瓦洛的表述在“崇高”概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思想传遍欧洲的学术界,也使得这个概念在文艺评论界被普遍接受。
“崇高”概念的下一步发展是在英国完成的。英国人接受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一书并不比法国人晚。例如,荷马翻译者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在他出版于1611年的《论翻译和捍卫荷马》一书中,就引用了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然而,崇高概念在英国产生重大影响,仍然要归功于布瓦洛于1674年将它翻译成法文,发表译者序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三位著名的英国人,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了对自然的描绘上。这就是艾迪生、丹尼斯和夏夫茨伯里。他们三人在这段时间里分别去了阿尔卑斯山,写下了对阿尔卑斯山的感受。在他们所写的感受中,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这是一种对自然物的反应,而不再是对诗歌风格的评价;第二,崇高是一种痛感后的快感。
无论是布瓦洛,还是这些英国自然主义的美学家们,在谈到“崇高”时,都只是将它看成是一种最终会带来愉悦的美。到了1757年,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出版了《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思想起源的哲学探索》一书,将“崇高”与“美”明确地对立起来。在这本书中,伯克说:美是小的、光滑的、轻盈的、精巧的,使我们的神经放松,具有“女性的”性质;而崇高是巨大、无限、充满力量的,使人恐惧,产生自我保存的欲望,并引起神经紧张,因而与“男性的”性质联系在一起。
伯克的书发表后,很快就被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以德文作出呼应,他于1761年发表了《论高雅科学中的崇高与素朴》一文,将崇高的讨论带到了德国。短短三年后,即1764年,康德就出版了《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一书。康德的这本书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像伯克一样,该书处处显示出“崇高”与“美”的对立;第二,将“崇高”概念进一步泛化,显示出“崇高”在生活中的无所不在性。例如,该书举例道:“高大的橡树、神圣丛林中孤独的阴影是崇高的,花坛、低矮的篱笆和修剪得很整齐的树木则是优美的;黑夜是崇高的,白昼则是优美的。……崇高使人感动,优美则使人迷恋。”他甚至接着列举:“悟性是崇高的,机智是优美的。勇敢是崇高而伟大的,巧妙是渺小的但却是优美的。”他还把崇高与优美的对立和悲剧与喜剧的对立联系起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地就在于前者触动了崇高感,后者则触动了优美感。”他的这些描述,尽管还没有深入的理论阐释,但显然是接过了伯克的理论,将之看成了在生活和艺术中普遍存在着的对立范畴。
此后,在1790年,康德发表了《判断力批判》一书。对于“崇高”范畴的发展来说,这本书的论述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本书中,康德做了两件事:第一,对崇高与美作出了区分。他提出,美在对象的形式,而崇高在于对象的无形式。美在于对象的“质的表象”,而崇高在于对象的“量的表象”。美的愉悦是直接促进生命的情感,而崇高是间接产生的愉快,是对生命力的瞬间的阻挠,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力的更强烈的涌流而产生。并且,美是“合目的性”的,而崇高则“反目的性”。与《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一书相比,这本书对“美”与“崇高”的对立的论述,不再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崇高”的本质之中。第二,在这本书中,康德区分了“数的崇高“和“力的崇高”。数的崇高是指对象的无限大,超出了人的想象,需要用理性来把握它;力的崇高是指对象具有使人恐惧的力,需要人用内在的勇气来克服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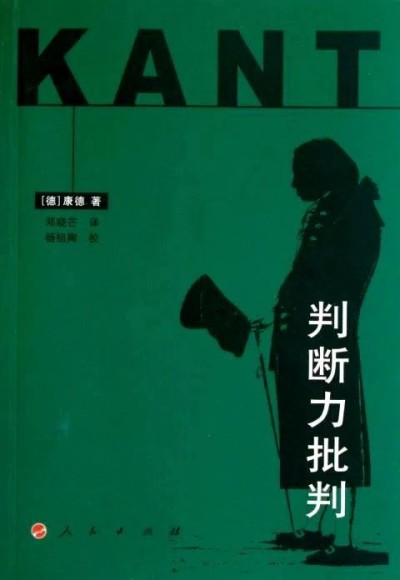
[德] 康德著 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
康德关于崇高的理论,成为古典崇高理论的总结,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古典主义的总结,也启发了浪漫主义的兴起。
三、崇高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正如前面所说,“崇高”概念原本是通过著名的古典主义者布瓦洛而得以传播,从而进入到欧洲学术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崇高”原本具有古典的精神,并且在古典主义的戏剧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例如,在高乃依的一些戏剧如《贺拉斯》《西拿》中,就是如此。
“崇高”作为风格和技巧,原本是古典主义重视形式、以典雅的宫廷趣味为代表的。布瓦洛所强调的重视精神性和强烈情感的精神,恰恰被后来的浪漫主义所发挥。这就是说,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崇高的风格并不等于崇高精神,而崇高的精神是由浪漫主义运动所发扬光大的。
浪漫主义所弘扬的精神中的第一点,是对自然的热爱。正如前面所说,英国人丹尼斯、夏夫茨伯里和艾迪生对阿尔卑斯山的崇高感受,启发了英国人对自然的崇高意识,正是这三位著名人士在18世纪初对sublime一词在英语中的使用,使得在英国,一种在自然欣赏时所经历的惊恐、艰困,以及克服这一切后的狂喜被当成“崇高”。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伯克将“崇高”与“美”对立的论述。这种对立,仍是一种对自然欣赏的抽象。古典主义的乡村是美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葡萄园、薰衣草和向日葵,被农民们精心耕作,整齐而有序。零星有一些农舍,依丘陵而建,其间有一个高高耸立的教堂。丘陵那一边是大片的草地,草地上有牛羊在放牧,上面是蓝天白云。这是一种田园之美。与此相反,高山、大川、大海、风雨雷电,再加上异域的情调,这是浪漫主义所喜爱的自然,给人以崇高感。康德笔下的数的崇高和力的崇高,也是以自然为对象。数的崇高是对无限大的自然界之物的理性上的克服,力的崇高是对无限猛烈的自然界之物的理性上的克服。通过康德,这种自然界崇高的思想得以确立。
这种思想反过来对英国产生着影响。1798年,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谈论了自然中的“崇高”:
惟有自然,主宰着我的全部的身心。——那时的我呵,委实是难以描摹。轰鸣的瀑布似汹涌激情,将我纠缠不舍;高山,巨石,幽深昏暗的丛林,它们的形态和色彩,都成了我强烈的嗜欲;那种爱,那种感情,本身已令人餍足,无需要由思想给它添几分韵味,也无需要另加不是由目睹得来的佳趣。
对此,华兹华斯写道:“我感到仿佛有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欣把我惊动;我还庄严地感到,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地运转。”
这种崇高的精神,存在于拜伦《唐璜》对异国情调的描写,也存在于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所描写的大海中水手们对命运的抗争之中。
浪漫主义绘画也是如此。在谈到透纳(J.M.W.Turner)的画时,英国泰特博物馆策展人伊丽莎白•布鲁克(Elizabeth Brooke)提出:“‘崇高’是贯穿透纳毕生创作的一条观念主线。”透纳以他的山间、海上、天空、威尼斯城的风景,很好地阐释了崇高概念。
在音乐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通过气势恢弘的音调展示对英雄的礼敬,在《命运交响曲》中是与命运搏斗,让光明战胜黑暗。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拉斯金这样定义“崇高”:“任何提升心灵的事物都是崇高的,而心灵的提升源自对一切‘伟大’的沉思。”人所面临的,不再只是自然的巨大或力量,也不只是对自然的抗拒,而是通过这个过程使自身的心灵得到提升。
四、新崇高、伪崇高、负崇高与崇高的未来
“崇高”这个概念当然并不仅仅属于古代和近代。到了20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问题,也同样出现了新的崇高范畴。
首先,当年的那一座阿尔卑斯山就引得一批著名的英国人感到崇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代登山设备的成熟,使得攀登那样的山不再是难事,也无法提供曾经有过的那种刺激。人类早已征服比阿尔卑斯山更高得多的山、更令人恐惧的荒漠和极地世界。康德在谈到数的崇高时认为,崇高并不只是普通的“巨大”,而是无限的大,大到超越人的感性能力,使人感到威压,从而迫使感受者运用内在的理性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威压。然而在当代,人们掌握了现代测量方法和定位手段,再高的山也能量出它的大小,因此它们不再是无限的。人们不再需要内在的理性,只需要测量技术和对登山设备的了解,就能克服那种威压感。透纳所画的大海的景色,暗藏着对人的威压,呼唤着人征服大海的勇气。大海曾经是可怕的威胁,变幻无常的天气,冰山海啸,对人类来说是可怕的对象。人需要一种内在的意志力量来征服大海,以人定胜天的气魄作为心理支撑,从而能欣赏风浪中的大海。到了现代社会,这些海浪不再是威胁。人们早已掌握了各种气象预测的手段和航海工具来避开它、征服它、利用它。然而,世界是无限的,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天外有天,高山和大海所带来的崇高感仍会存在。更进一步说,当人们要探索浩瀚的宇宙和无尽的深海时,仍会带有崇高之情,从而形成深空和深海探索时代的崇高感。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给人提供了多种便利,使人具有了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当我们看到高高耸立的三峡大坝,看到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穿梭而行的高铁线路时,也会从中感受到人类的伟力,从而产生崇高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给人类带来威胁。人类如何使用核能?核时代的战争如何带来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基因编辑工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未来?是祸还是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带来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的恐惧?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这种迅速变化着的世界所带给人的震憾,一些人为此感到悲观,更有一些人在此情况下坚信人类的未来。
这些崇高的体验,也会进入到当代的艺术之中。伯克所列举的崇高的例证,康德笔下所论证的两类崇高,即数的崇高和力的崇高,都以自然物为例,这继承了18世纪英国的传统。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崇高又回归了艺术,并在诗歌、绘画、音乐等方面展示出来。
到了20世纪,先锋派艺术赋予了崇高以全新的含义。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艺术仍是摹仿与叙事、再现与表现,保留着艺术的形式。即使是冲破旧有形式,仍在创造新形式。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则认为,20世纪先锋派艺术的特征,就在于“崇高”。他认为,这种“崇高”体现在对“不可呈现物”的呈现,使自身成为“不确定性的见证”。这可以通过一些抽象艺术,如波洛克和纽曼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也可以通过其他各种脱离美、打破形式的追求、克服趣味的束缚的先锋派艺术表现出来。
在西方美学史上,美与形式的结缘是一个大传统。从柏拉图开始,就提出了美的形式观。托马斯•阿奎那总结了古典的形式美传统,提出美的三个要素:“完整或完善(integritas sive perfectio)……;合适的比例或和谐(debit aproportio sive consonantia);以及最后一点,明亮或清晰(claritas),被称为美的事物都有鲜明的颜色。”崇高概念正是要反这个传统。只要存在着形式以外的欣赏,只要存在着趣味以外的吸引,崇高就会出现。于是,崇高又成为当代先锋派艺术的特点。
当代的崇高,还体现在巨大的规模、光与色所造就的宏伟的气势之上。这不仅体现在人造的产品中,也体现在艺术之中。恢弘庞大的场面,高亢的声调,凭借现代技术和资金支持所带来的规模效应,都会给人带来震撼的感觉。但是,如果其中没有真实的意义,不能将人的情感代入,就会带来虚幻感,形成伪崇高。
当代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对灾难的呈现。一些艺术品打破乐观主义的幻想,揭示人类社会所面临着的种种灾难,呈现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诸如核战争、生物基因编辑带来的恐怖、人工智能的挑战、小行星撞向地球、地球本身以至太阳的毁灭,等等。以这一类题材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揭示了人的当下处境,但需要展示人在灾难面前的态度。因为灾难本身构成了负崇高,而人的顽强抗拒精神,为人类创造未来的顽强努力,恰恰构成了一种新的崇高。
结语
崇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在近代,它形成了一个与美相对的重要美学范畴。到了当代,崇高范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渗透到各种艺术门类、各种艺术类型之中,起着重要作用。崇高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艺术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崇高所包含的强调人文精神、强调人内在强大精神性的特点不会改变。随着时代前进,崇高从在美学上起着补充作用的概念,逐渐演化为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高建平 单位: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总第114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