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从郭文斌的《中国之美》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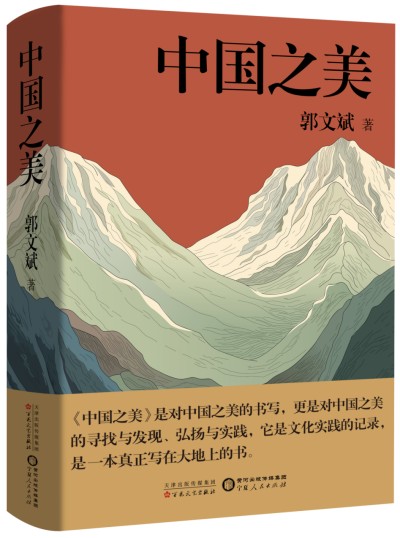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在读郭文斌的《中国之美》,它既有细致入微的感性体悟,又有深远宏阔的理论构建。这本书中,除了“中国”是一个关键词之外,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贯通全篇的“美”——风俗之美、节气之美、礼仪之美、乡愁之美等。无疑,“何为中国之美”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重要话题,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思。
《中国之美》以“中国之中”为方法,以“中国之美”为旨归,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即它是一种通观式的写作、一种全景式的写作、一种立体化的写作。它以一种特别的诗意情思与文化幽怀,以一种动人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表达,涉及哲学、美学、文化学、教育学等等多个领域。它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而是以文学为根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与回归。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郭文斌关于“中国之美”的表述,是建基于他的故乡西海固,特别是西海固的天道伦常、文化习俗、历史地理。在早年的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郭文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停留在乡土经验的表层上,而是借这种经验开启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更为丰厚广阔的意蕴空间——由此,他的文字直接潜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中。换句话说,作为地域背景的‘西海固’,只是郭文斌的一种叙事策略,它一方面牵动着人们猎奇般的‘期待视野’(譬如乡村的偏远与落后、乡土的神秘与新奇),另一方面却企图引领人们走向归乡之路,回归源头,去追寻生命原初的光亮。而后者,才是郭文斌的真正目标。”因此,恰恰是那个被称作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却因为它背后的文化滋养而变成了郭文斌笔下无可替代的福地与圣地。对于西海固,郭文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狂欢、自在、率性”,“那片土地,有一种原始性的文学气质,是上苍专为生产诗情而生的”,那里有一种“大纯净、大富有、大善良、大审美”。如此,对“西海固之美”的执着与深情,正是郭文斌“安详诗学”的发生源头,也是其“中国之美”的现实之基。如此,由西海固而宁夏而中国,从一颗谦卑温润的种子最终长成郁郁苍苍的大树。
我们再来看看,郭文斌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中是如何诗意地解读“美”的。小说中两个小主人公五月、六月对“美”的发现和体味,可谓若虚若实,如诗如梦。他们带着端午的“神秘的味道”跑到巷道的尽头时,“六月问,姐你觉到啥了吗?五月说,觉到啥?六月说,说不明白,但我觉到了。五月说,你是说雾?六月失望地摇了摇头,觉得姐姐和他感觉到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五月说,那就是柳枝嘛,再能有啥?六月还是摇了摇头。突然,五月说,我知道了,你是说美?”在这段简短的对话里,姐弟两人通过充满童真的问难与争辩,最终以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觉到”了“美”。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对“美”的发现与追寻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美”不仅是一种快乐和幸福,更具有一种涉世之初的“诗意启蒙”的力量,同时它也将成为灵魂的终极滋养。从《吉祥如意》中的“美”,再到《中国之美》中的“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之美”之于郭文斌,不是自上而下的、自外而内的,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概念、书斋,不是来自于强制的道德意志;而是自下而上的、自内而外的,生之于乡土与故土之中,长成于乡土与故土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与美学话语,更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体验。
通读《中国之美》,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书中第二辑关于“乡愁”的理解和阐释。“乡愁”是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的永恒命题,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含义。大体说来,在当代社会背景之下,我们对“乡愁”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作为个体情感与心理情结的“乡愁”;作为文学和美学意象的“乡愁”;作为美丽中国建设、诗化政治目标的“乡愁”(譬如新型城镇建设中的“乡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愁”等)。在郭文斌看来,“乡愁”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和谐力、建设力,“它是生机,是春意,是真理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是四两拨千斤的‘四两’,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那个‘本’”。于是,“乡愁”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范畴,而是一个全新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对各种优秀文化兼收并蓄的新概念。于是,“乡愁”最终“承担起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寻找中华文化的基因链,寻找中华文明有机体的中气”。在关于“乡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之美”的另一番独特韵味。
总之,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执着追寻和探究“中国之美”,本质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化的再造。因此,无论是“记住乡愁”也好,还是“中国之美”也好,无一不是大命题,它直指我们的“民族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它不仅关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归依与精神原乡,更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境遇下的美学实践与文化行动。
(作者:张富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