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困惑与坚守
——读杜斌小说集《天眼》
对很多人来说,杜斌是一个“新人”。也就是最近几年,他似乎有些突然地活跃在文坛。长、中、短篇小说接二连三地发表,并被转载。有的还获得了比较重要的奖项。而他极度贴近现实的表达又令人惊叹。这也证明,在当下,在中国文坛,仍然有一种突出的创作现象,这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直面与关注。但事实是,杜斌是一个“旧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如果从出现的时间点来看,应该与被称为狭义的“晋军”是差不多时代的人。正在逐渐被人关注的时刻,杜斌突然“消失”。直至今天,当他重新拿起笔时,人们才发现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并为他旺盛的创作力而感叹。我们很难说清楚,在那些“消失”了的日子里杜斌干了些什么。人们知道的是他当过兵,开过矿,经过商,在市场的大潮中翻波逐浪,在转型的历史必然中成为一名亲历者——直接参与的亲历者,而不是理论上的观察者。无论如何,文学的情结仍然在他内心跃动,并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不能遏止。那些文学之外的经历恰恰又成就了他的文学——为他的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素材、人物、细节、灵感等等。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归文学时,新的定位与旧的积累纷至沓来,“归隐”的杜斌成为“回归”的杜斌。当人们还在谈论他的一部新作时,他又完成了一部更新的作品。时光渐离散,新作已成旧。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小说。

杜斌的重新登场,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在他这个年龄,大多数人已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或者才华散尽,无可奈何。但杜斌却掀开了人生崭新的篇章。他重新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现,不停地书写,并表现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也许,这与山西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特性有关。有论者言,山西文学有一种“衰年变法”的现象,就是说很多人在退休之后焕发出了创作的“第二春”。他们并不因为年龄老大就再写不出东西来。恰恰相反,他们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更旺盛的创造力。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点文化上的异样,就是非同一般地执着。认准了是干这个的,就要一直干下去,直到真的干不动为止。比如李国涛先生,本来以理论与评论为名。但因为眼疾,不能长时间阅读,就转向回忆,以“高岸”的笔名创作小说,也是长、中、短篇联袂接续,以至于不明就里的人以为“高岸”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文学新人。后来不再能写长一点的东西,就不停地写各种读书小品。直至离开我们,仍然有书在出版。在山西,像李国涛先生这样的人,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们说,称之为“衰年变法”不准确。因为他们虽然年岁有长,但生命力并未进入“衰”状,反而日见其盛。所以,应该是“长年变法”或“高年变法”更形象。虽然从年龄的角度来看,杜斌当然是大幼于李国涛等人。但从对文学的执着而言,他们实在是同一种人。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杜斌创作的艺术追求,亦与山西的文化有着沾血带肉的联系。一直以来,山西文化品格中对现实的关注是十分突出的。从思想源流来看,山西地域的哲人贤者特别强调“用”,就是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也正因此,能够在儒家中析出法家,壮大兵家,成长出纵横捭阖的纵横家;能够在学理中强调“致用”,身体力行西行求法,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考察辨识,兴盛一派。从文学的意义讲,关注现实成为悠久绵长的传统。从《击壤歌》《南风歌》到《唐风》《魏风》,到中国戏曲的兴盛与小说的蔚为大观,乃至于中国新文学的革命、民族化的完成,均一脉相传,承接有致。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山西文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坛拥有重要的地位,与其呼唤改革、表现民生,关注国运、直面现实,并在艺术表达上不断变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西一代一代的作家成长起来。不论艺术表达如何多变,基本精神没有变。表现在杜斌这里,似乎更为突出。他的文字粗犷凌厉,一泻千里;结构以纷至沓来的生活细节为重;描写注重情节与细节;描写的人物是生活中有具体身份的、可触可摸的行动着的人。凡此种种,杜斌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历史情状——带有生活意味的、烟火气息的、生命质感的,以及价值判断的现实世态。
如果说杜斌的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似乎还应该再准确一些。他其实描写的并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社会进入实质性转型之初的“现实”,也即上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间,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最终实现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时期。这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一转型停顿,现代化将被迟滞。而要完成这样一个具有超长历史文化传统、超大国土幅员、超多人口的国度的转型,确非易事。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呈现出所有国家转型时期的多样性——顺应历史必然的社会变革动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非理性、非道德行为。资本成为十分活跃的因素,逐利被更多的人视为目标,竞争不再羞羞答答,而是转化为可以言说的手段与工具。旧的规则被打乱、打破,新的、有序的规则尚未建立、健全。但是,在这样的变革与纷乱之中,良心悠久,道德依然。人们到底该如何面对现实,如何走向更远的未来,面临考验。

杜斌
尽管不是全部,但仍然可以说收录在这部集子中的小说比较集中地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从事太阳能热水器工程的“世界”,与杜斌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一以贯之。其从业者来自四面八方,汇聚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珠海。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各有神通——并不是按照有序的竞争规则,而是在此之后的利润角逐。利润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些市场中的“弄潮儿”用尽了手段,耍尽了花样,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甚至不惜制造事端,嫁祸他人。在这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竞争”中,资本与利润展示了其赤裸裸的本性。但是,生活并不仅仅属于“利润”,仍然需要对构成生活的“人”之情感与精神的拯救。获取了更多的金钱亦难以跳出金钱的诅咒。在这种转型初期的困惑与紊乱中,仍然需要人的自省与自救——源于道德自觉与法的意识的约束与超越。杜斌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设计了一个相对而言不屑于此道,或者对人生有了感悟的形象王高峰。他对这种恶性竞争充满忧虑,希望大家能够和睦相处,甚至希望从商战的一线退出。他的人生观是不浮不躁,不计较浮华之事,只想做一个淡淡的人,淡淡地为工作和生活努力。而在《天眼》中,作者使用了“魔幻”的手法,让一个带着三千年沧桑的声音不断地、神秘地出现,告诫因金钱而痴迷的张高美:人在地上做,神在天上监察。这似乎是一种来自“天”的警示,是对无序现实及其人生的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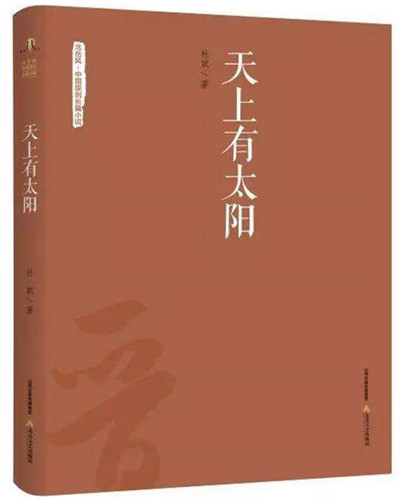
在《天眼》中收录的作品,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思考。这些小说是对中国社会实质性转型初期现实形态的表现。从某种意义讲,也揭示出了人类社会转型中的阵痛与迷茫。以先发国家言,均经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阶段。在距今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这个新出现的国家完成转型的关键时刻。原住民已经不再是美洲的社会中坚。他们对整个时代与这块土地的影响已不复存在。新移民带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在美洲的土地上左冲右突,以获取最多的金钱。经济生活极度混乱,造假、垄断,官商合流、腐败成风,财富、金钱、利润、利益成为那一时代的中心。在疯狂的利益追逐中,人迷失了自我。以至于在美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人们呼唤:上帝,救救我们的共和国吧!在这样的混乱之中,促成了美国的变革。但是,资本的本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资本的贪婪以新的形式不断膨胀,以至于“贪婪是个好东西”成为里根时代的名言。他们认为越是贪婪就越能努力赚钱。当这种不顾一切的贪婪在某一刻爆发时,危机来临。2008年,雷曼兄弟等一系列举足轻重的公司就要倒闭。英国学者哈里·宾厄姆在他的《资本主义万恶吗?》一书中,借用一位在摩根大通任职者之口说道:美国资本主义失败了!哈里·宾厄姆认为,这种资本主义不值得尊敬。但是,他希望有另一种“资本主义”存在。这就是富于创造力、不断推陈出新,活力十足、遵守道德、满怀激情的“资本主义”。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能够存在,或者仅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形态是与遵守道德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并不能够仅仅以获取财富为唯一目标、唯一手段。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人所组成的社会还必须依靠金钱之外的道德、道义、伦理、奉献、同情与爱心等来维护、协调社会的有序性。人的生活并不是仅仅以获取完成的。在金钱之外,仍然有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存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动物可以获取食物为维持生存的绝对目标。而人则是超越了这一目标的社会生物,是具有情感与意志、理性的生命体。他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不甘于匍匐在欲望的泥沼中喘息,而是希望能够在广阔的田野中仰望、升腾。杜斌所言的“天眼”充满了象征与隐喻,是人的理性与情操在无序现实中的警示与拯救之眼。它的一瞥一睁,熠熠闪光,直击人心。
应该说,杜斌的这些小说是很好看的。首先是他为我们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另一面——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并不相同而让我们感到讶异的行为——在激烈竞争中的不择手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后果。胜者未胜,且不可能是长久的胜。在道德与法律面前,这些手段只是一种将要被时代抛弃的存在。但是,它的确存在着,或者存在过。其次,他很会设计情节。或者使故事逆转,一切皆在预料之外;或者让人物进入莫名的连环套中,使读者急欲了解之后的故事;或者不断地铺陈一个又一个使人感到新鲜的“手段”。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你总是会被他的故事牵引。最后是不断地向读者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性”内容,如某种美食的特点、做法,甚至吃法,某种材料的性能、功用等等。他不知道节制自己的素材,也不注意调整叙述的节奏,不精雕细刻锤炼自己的语言。他就像用语言来给读者下一场接连不断的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直泻而下,雨花四溅,直至故事结束。这既是他的特点,也形成了他的局限。常常令人感到,杜斌真是奢侈啊!他竟然如此毫不顾惜自己的素材,竟然如此任性不忌。虽然相对而言,他的生活积累比较厚实,但是,也不能这样张扬吧?
在这部集子中,有一篇《清明吟》的小说,写一位早早离开家乡,在珠海打工的农民张宝贵。他不属于前述的商海中的“弄潮儿”,而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普通人。他胆小、老实,没文化,缺乏超前的眼光。在珠海二十多年也没有赚够可以买一套商品房的钱,以至于一家人一直挤住在租来的民房中。与他身边的很多人比,他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却又是一个回不了故乡的人。在离开家乡若干年后,突然想在清明时节回去给父母上坟,以表达他对故乡、对父母的怀念之情,但是,故乡已非昨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连自己的家也找不到了,甚至连自己父母的坟也没有找到。但是,这并不是张宝贵一个人的悲哀。因为,找不到家或者找不到坟的人即使是在他曾经的故乡也绝非自己。他只能望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坟地,一脸茫然,束手无策。人虽在,家已无,根亦断。他那被荒草覆盖的家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一种心结,一种回亦无可留,走又无可处的惆怅。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大潮中,张宝贵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社会转型时期给每一个人带来的迷茫。但是,四月,春色正浓。张宝贵的生活仍然在变化。他的儿子似乎在另一个城市闯荡得渐有起色,并且给他生了孙子,即将上学。他改变自己、改变生活的希望也没有消失,甚至更为强烈。像更多的普通人那样,张宝贵没有失去做人的底色,而是在这越来越浓的春色中面对自己。也许,从对时代表现的深刻性而言,我更尊重这种变化中的惆怅。这是一个时代的阵痛,是即将迎来新生活的前奏,是千千万万的人们在困惑与迷茫中的坚守与追求。
(刊发于《黄河》2020年第2期)
(杜斌简介:1956年生,山西永济人,中国作协会员。1973年开始创作,作品散见于《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黄河》《山西文学》等刊物。其中,中篇小说《天眼》获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并荣获“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特别推荐奖”;中篇小说《风烈》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荣获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出版小说集《天眼》。)
(杜学文简介: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创作,已发表研究成果300多万字。出版有文艺评论集《寂寞的爱心》《人民作家西戎》《生命因你而美丽》《艺术的精神》《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历史文化著作《追思文化大师》《我们的文明》《被遮蔽的文明》等。主编的作品有《聚焦山西电影》等。曾先后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艺术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西省出版奖等多种奖项。)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