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不管是出版数量,还是文学消费市场,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大国。这一方面与中国把文学作为人民事业的管理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建立了一套文学市场制度有关。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文学生产与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网络文学、电子阅读的普及,已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格局和生态。无论是口语、文字、印刷媒介还是数字媒介,媒介作为文学的载体,也作为文学传播语境的形构力量,塑造着文学的表现形态与内在审美机制,重组着作者、读者、编辑等文学生产和传播主体的结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大方向。在这场深刻的媒介与信息革命中,数字时代的文学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文学的纸媒时代
自文学产生之初,文学的媒介载体与传播机制便深刻地参与着文学形态的塑造,而在现代社会,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更加紧密。美国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中指出,印刷革命催生了早期现代世界,也使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得以确立。而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发生,也与报纸、杂志这一西方传入的“新媒体”有关,促进新文学、新文化在中国传递科学、民主、个人、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可见,处于发展与变迁中的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建构物,媒介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媒介的技术、经济、政治属性以及媒介所建构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考察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传播与媒介的视角同样不可或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以各级作协、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这种文学期刊的发表、传播机制,生产端以专业作家为中心,传播端以编辑为中心,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基层作家的培养体系和多层次的文学刊物发表系统。80年代是一个知识群体占社会变革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这场社会思想的巨变中,文学再次扮演了思想文化变革的先锋角色,引领着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文化、文化热等一次次文化思潮。在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专业文学期刊发挥着巨大作用。文学界在新启蒙、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共识下,文学期刊的政治宣传属性降低,回到文学自身、回到语言自身成为新的文学规范。期刊编辑不再只是既定文艺政策的贯彻者,而成为新的文学思潮的发现、组织力量,形成了与作家紧密协作的“伯乐”传统。文学刊物、文学编辑在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兴起过程中都发挥着制度性力量。
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结束,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开始,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生产圈子化的问题突显,一部分文学走向纯文学,变成都市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一部分文学转向通俗文学,追求文化市场的青睐。伴随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文艺作品传播的对象由作为政治主体的“群众”转变为作为市场消费者的“受众”。在报纸、电影、图书等多种媒体逐步转型的过程中,1999年文学期刊开始尝试改版,但由于入场晚、产业基础薄弱、体制限制、内部争论等多方面原因,这种改革没有取得太大成功,依然依靠各级文学组织,维持纯文学的发表与传播。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牢牢把握住了作为消费者的文学读者群,凭借市场的力量,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主流文坛的文学生产、传播机制,这就是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文学。如以郭敬明、韩寒等“新概念”获奖作家为代表,他们成为新的文学偶像,取得畅销书市场和文学销量上的成功。
这一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重心并非创作环节,而是营销传播环节,也就是传播端的主导者是新兴文化消费主体,他们的年龄、购买能力、阅读趣味决定着这一文学工业的产品形态。其生产端的核心虽然仍然是作者,但作者的主体身份不再只是专业作家,而是具有粉丝效应的大众明星和偶像,借助多种媒介渠道将作家本人经营成最重要的作品,向读者提供可以帮助其确认自我、进而产生认同的消费符号。有的作家本身也转型为文化商人,以郭敬明为例,他是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常年榜上有名者。作为文化商人的作者掌控的是文学的再生产机制,他成为文学市场的把关人,根据市场的偏好,管理、经营、包装更年轻的作者,生产特定类型的漫画、电影等文学衍生产品,形成庞大的“最世”作者群,打造青春文学的商业帝国。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大众媒体的广告、营销、议程设置等功能也被整合进这一文学生产和传播的链条中,通过曝光、命名、评奖、媒体批评等方式制造文学传播的大众效果,市场调控与媒体传播取代了知识分子编辑的把关作用,成为主导文学与读者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样两种“纯文学”和“商业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背后是两套迥异的作者、读者和作品的关系网络,它们之间是既排斥又合作的微妙关系,一方面体制内的文艺生产会吸纳体制外的市场资源,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创作者也需要体制内来背书。如后来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和《收获》也开始刊登其作品,便是这种合作的写照。尽管这种合作颇有争议,但至少说明这两套不同的文学制度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它们都建立在中心化的纸面读物生产与传播机制中,都有一套严密的、层级化的文学生产秩序和规范。不过,无论是纯文学还是消费文学,都是少数精英主导下(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商业精英)的文学,并由他们定义文学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在这样中心化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体制下,来自社会更广泛阶层的表达诉求以及文学反规范、反束缚的巨大能量,正由一场前所未有的网络媒介革命所释放。
文学的数字化转型
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媒介革命,在中国迅速催生了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学革命”。互联网自身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为文学创造了独立于传统文学机制之外的创作空间,激发了沉淀在社会各个层面创作主体的力量。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中指出,1997年底文学网站“榕树下”建立,短短20年间,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便已超过4亿,并产生了超过1000万的网络作者群体。如今受到高度认可的网络文学作家“猫腻”在2003年开始连载时是被退学回家的学生,2001年的“上品寒士”是因病致残的职员,2011年的“独上阁楼”是年近花甲搁笔已久的老编辑。正是网络去中心化的自主力量,为这些普通人甚至“边缘人”的文学表达与创作赋权;也正是网络“连接一切”的技术特性,塑造了重新“部落化”的兴趣圈层,使作者和读者间的认同与交流成为可能。
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论述传播媒介的“偏向性”时指出,新的传播媒介可以改变社会形态,重塑社会传播权力结构,网络就是这种改变文学、文化生态的媒介。从新世纪初的网络文学网站,到移动互联时代人人拥有的自媒体,这些网络平台赋予了各个社会群体(无论是青少年、性少数群体、工人还是都市白领)创作和传播文学的权力。从传播权力结构的角度而言,互联网对文学最革命性的改变,并不在于创造出新形态的“经典”文学艺术,而在于文学创作与传播权力的民主化与社会化。不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拥有巨大生产能量的网络文学不可能避免资本的介入。2003年后,网络文学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在互联网双向传播的结构下,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是由读者主导的,从读者即时评论,到反馈介入到作者创作,再到读者付费阅读,这成为文学平台盈利的机制,而阅读量、转发量、点击率、粉丝数等各项数据也构成网络写手和粉丝审美、评价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粉丝的读者,他们是“过度的消费者”,是网络文学商业价值的衡量尺度,是文学为商业增殖的核心资源。
从2004到2010年,盛大文学集团先后收购了起点、晋江、榕树下等网络文学平台,对网络文学资源进行再整合。2014年腾讯收购盛大,推出上市资金5200亿港元的阅文集团,标志着媒体资本巨头对网络文学的垄断,网络文学成为腾讯内容生态的上游环节,在资本的主导下,以网络文学IP为核心的跨媒介产业开始形成。依照腾讯内容生态的布局,阅文集团采取了网文、动画、网络电视剧、网络游戏、网络电影等多重、多次开发的路径。以《择天记》的版权运作为例,2014年“猫腻”在创世中文网上开始连载《择天记》,腾讯为小说制作宣传片、主题曲、同名动画和众多周边产品。2015年《择天记》实体书在媒体发布会上高调面世,2017年由流量明星鹿晗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播出,而《择天记》的手游也同步开启全平台预约。到2017年11月,阅文集团和上海大学合作,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网络文学创意写作硕士点。这种文化资本对网络文学的深度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文学的走向。网络文学原有的具有理想色彩的自由、自主的创作属性让位于商业增殖的无穷欲望,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成为跨媒介文化工业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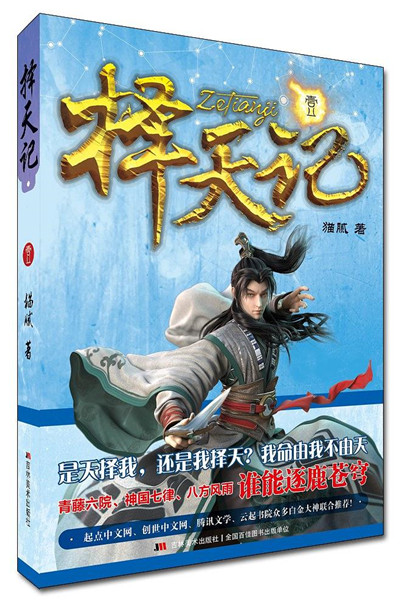
当下网络文学的困境并不在于这种商业模式是否能产生“好”的文学作品,而在于这种商业化的、资本化的网络生产与文化传播,是否会消解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结构原本赋予文学的多元选择。这正是数字时代文学生存的悖论:当网络赋予更多人写作的权力,文学却最终被文化资本所垄断,并越来越类型化、同质化;当网络使文学的商业价值不断增殖,文学自身独立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其优秀传统却在流失。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同构的。“网络技术霸权”下市场化的文化生产机制,恐怕正是美国传播学家丹·席勒所言的“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下的产物,互联网并没有改变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则,反而使这种规则更加深入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只有把握互联网这一媒介的技术属性和政治经济属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在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文学公共性的重建
理论家米勒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中讨论了“文学终结论”,反复提及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对“文学的时代”终结的表述:“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和米勒都清晰地强调了新媒介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媒介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延伸”,其最深远的影响是创造出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即“被剥夺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情书的电脑人”。米勒的论述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媒介技术正是通过改变人的主体意识,将人类漫长的历史传统中所形成的关于文学或“文学性”的认知颠覆,从而将文学置入巨大的危机。
当我们观察今天互联网对读者和作者的改变,会发现米勒绝非危言耸听。移动互联网重构了时间、距离、空间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同在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实现自我认同与满足的虚拟空间和“第二人生”,也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欲望、焦虑和孤独无限放大。因此,对于一般的文学、文化消费者而言,在现实生活的碎片化、跳跃性的阅读场景中,人们寻求的是通过文学创造出的虚拟时空和对自身的欲望进行即时满足,网络文学成为一种现实替代性的补偿。大量以虚构的“架空世界”为背景的“爽文”构成了网文的主体,构造出一个个给予人们安慰和满足的乌托邦,而这样的乌托邦,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所言,只是现实世界消极面的镜像。“爽文”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消极面时,放弃了文学对生活本质的多样性和细微性、人性的痛楚和更隐秘深处的正面刻画,而是用同质化、简单化的“套路”,创造出斑斓的镜像,刺激那些业已麻木的现代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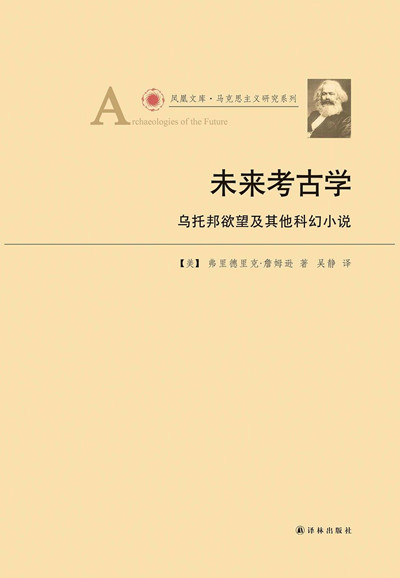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市场和媒介技术的作用下,作者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介创作机制的匿名性、开放性和无门槛,成为创作主体逃避作为写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意义追寻的绝佳平台,从本质上取消了创作主体的担当意识,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宝贵的传统,也是使文学立于历史舞台中心的社会价值所在。在巨大的商业利益下,网络作家是极为勤奋尽职的“职业作家”,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于商业生产链条中。正如唐家三少接受采访时所说,“我就是个普通作者,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以此为职业,没想过要流传千古……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觉得舒服,第二天还想看,再体会这种舒服感,这就可以了。”在网络文学商业化之前便开始创作的“远古级大神”作家荆柯守,也在移动阅读市场的影响下更加商业化和“小白化”,开始了低层次的自我重复。这种在创作上自我矮化的心理,与“大神”作家们惊人的收入形成了强烈对比,更体现出网络文学的作家与文学的社会责任的分离。
如果说是文学的市场化生产机制导致了作者自我矮化的主体心理,那么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则真正将大量作者“去技能化”,降格为“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据艾瑞网统计,在2016年的10个月里,中国累计出现了140万名网络写手,想从这140万人中崭露头角,必须保持一天至少一次、每次至少3000字的更新。这种文学“量产化”的需求,催生了“小说生成器”等基于数据抓取的网络文本自动生成软件。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东浩纪认为这种“数据库”写作彻底解构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光韵”。将文学置入危机的正是在资本的作用下互联网对人的“异化”,即用媒介的逻辑、技术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取消了“人”在文学创作和阅读中的能动作用,如个性、激情、想象力和反思,以及创作与阅读都需要的闲暇。这最终将导向的是“媒体化”的文学,即被媒体技术和体制改变其自有逻辑的文学。这也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电影、音乐、美术等人类艺术共同面临的困境。
要从这一困境突围,显然不仅仅是媒介技术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要解决数字时代留给文学的这道难题,仍然需要回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的本质特征“去中心化”,让技术重新为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创作主体赋权,形成多样、丰富、自由的网络文学生态。实际上,目前的网络文学也并不只有类型化、商业化的网络小说,只是在市场的力量和政策的监管下,其他的声音太过于微弱。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上,工人群体等边缘群体的诗歌、戏剧都有了创作与传播的通道,热衷古典文学、“纯文学”的文艺青年也形成了自己的兴趣圈层。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自媒体和媒体人则开辟了“非虚构写作”这一打通新闻与文学的创作空间,让写作重新进入公共领域,重新具有探寻社会深层问题的力量。即使是在高度商业化的“网文”世界内部,也有大量具有文学专业背景和高知识素养的“学者型”粉丝,并形成了具有艺术水准的“经典网文”的评价与遴选机制。
由此可见,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公共性的重建,仍有可能使网络文学发展出更丰富的题材,更具探索性的新形式和风格,以及形成真正深入时代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的良性生态圈。这一网络文学生态圈的建立,需要文学、艺术教育的支撑,需要学院视角的主动发掘和引导,需要更合理的网络治理政策,需要更有效而非一味追求高效的市场规则。惟其如此,文学才能有其继续生长的空间,现代人的精神才有长久的栖息之地。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