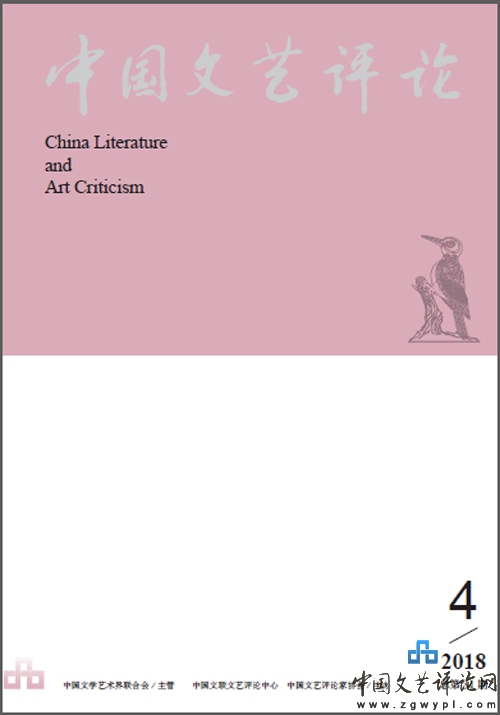
内容摘要:黔剧《湄水长歌》取材于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最终在贵州湄潭县坚守七年、砥砺前行的办学历史。这是一种既表现浙大师生在中国人民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坚持“求是”校训,为保存中华文脉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精神,也是讴歌湄潭百姓为支持浙大办学节衣缩食、无私奉献的双主题变奏。双方同舟共济,奏响的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黄钟大吕之声。作品不仅为地方戏如何以时代精神为引领超越地方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也在阐释历史的视角与主题的开掘,以及如何发挥黔剧的优势等方面,呈现了突出的亮点。
关 键 词:黔剧 浙大西迁 双主题变奏
贵州省黔剧院2017年推出的原创黔剧《湄水长歌》[1],从台词、念白到唱腔,从音乐、服饰到舞美,可谓黔味十足,演员的唱念做打也非常专业,是一部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绝非偶然。
《湄水长歌》是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宏大背景下,围绕浙江大学的西迁以及贵州湄潭人民为浙大所作的无私奉献来展开戏剧冲突的,类似于一种双主题变奏的结构形式。浙大竺可桢校长和湄潭县严县长这两个主角,分别代表浙大师生和湄潭百姓。一面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求是”的校训,为保存中华文脉奋发进取,一面是从开明县长到普通百姓,为支持浙大办学,“我愿邻曲谨盖藏,缩衣节食勤耕桑”。[2]故事虽然只关涉浙大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及湄潭人的让地、让房、让粮,但点点滴滴均感人至深。
《湄水长歌》的双主题变奏主要有三个亮点:第一,有问题意识,为地方戏如何以重大题材、时代精神为引领来超越地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二,在阐释历史文化方面有创新和突破,其视角在过去的作品中极少出现;第三,传统戏剧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住自身的特点、魅力,并发挥其优势,一直为很多人所关注,《湄水长歌》在这方面亦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一、双主题变奏的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地域环境及其历史文化,既关系到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关系到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感知方式,也关系到风气、风俗和氛围对人的影响与熏陶,因此,艺术、文化与地域的关系几乎是前生注定、与生俱来的。任何艺术,都会被打上“地方”的深深烙印,地方戏尤其如此。全国有三百余种地方戏,地方性的差异可谓千姿百态、五彩纷呈,所有差异均与不同地方的自然环境及风土、风俗、民情有关,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地方戏的方言、声腔、念白方面,也体现在服饰、音乐、舞蹈、化妆,甚至特有的特技、绝活方面。
然而,地方戏最终所追求的毕竟不仅仅是地方特色。传统地方戏通常都要载道,都要以道德或因果来教诲人。向现代转型之后,则强调先进的思想力量,要求有超越地方的价值内涵。对地方戏的改编或原创来说,真正的难题就在如何既立足地方又超越地方。那需要有时代情怀,需要有责任感与担当意识。观众看戏,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地方特色,无论它有多么独特。地方戏的剧情、剧本、剧目,如果不能与历史、与时代以及艺术的未来形成对话,格局一定不大,前景一定十分黯淡。无数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精神的引领,一直是地方戏旧剧改造、新剧创作的重要途径,地方戏要超越地方,要有更大的格局,必须有对时代精神和主流文化的呼应。而这一点,正是《湄水长歌》双主题结构的突出亮点。
《湄水长歌》是一部有问题意识的戏剧,它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超越地方,二是如何超越历史。浙大西迁是重大历史,而黔剧是西南边省的地方戏,对浙大西迁历史,通常的着眼点主要是浙大师生的自强不息与薪火传承,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报国梦。《湄水长歌》编创者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既与黔剧如何出山有关,更要在一校、一县生死与共的关系中,找到进入宏大叙事的路径,其中“地方”与时代精神如何融合,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腹地,接纳了从北方、中原以及沿海地区迁入的大批机关、学校、报社、商号、企业。仅高校就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程学院、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大学等九所。西南联大从长沙西迁昆明时,数千名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师生亦曾徒步穿越贵州。在落户贵州的高校中,办学成绩以浙江大学最为突出。蜗居贵州黔北大山七年,浙江大学秉持“求是”校训,不但办学实力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萎缩,反而是越挫越强,不仅建置更加完备,办学规模也从入黔时的三个学院16个学系,增加到返回杭州时的六个学院,25个学系,一个研究院,四个研究所,五个学部,一所分校,一个研究室,一所附中,两个先修班,11所工场;其中仅农场用地就达三百余亩。学生总数也从1937年的633人,增加到了离黔时的2243人。[3]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浙大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只有浙大师生的努力?“地方”有没有发挥作用?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湄潭的贡献在过去会被忽略?所有这些,正是《湄水长歌》问题意识的主要内容,需要它的编创者们深入思考,并用艺术形象作出回答,其中包括如何从“地方”进入民族大情怀与时代大主题,以及如何表现这一主题等。
应当说,《湄水长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案。浙江大学之所以取得骄人的办学成果,首先是有时代旋律的激荡及民族精神的感召,在这一宏大叙事的引领之下,它的双主题变奏分别向精英与民间、知识分子与大众、发达地区与边远地区两个领域作拓展。这部戏成功地告诉观众:正因为有浙大师生和湄潭百姓在艰苦岁月中的相濡以沫,相互砥砺,才会有浙大的办学奇迹。浙大师生的自强不息与湄潭百姓的无私奉献,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顽强奋进的精神,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特殊年代的时代主旋律。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战争年月,文弱书生的忍辱负重与湄潭贫苦百姓的节衣缩食,同样都让人动容、让人振奋。
回顾“黔剧出山”的历史,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地方戏无论取材于历史还是取材于现实,都需要有对题材的深入开掘,都需要呼应激荡的时代旋律,都需要用自己的艺术,参与时代社会的宏大叙事。地方戏仅关注地方,仅以满足部分观众的需要为目的,那是没有希望的。艺术的生命力,既需要有来自地方、来自民间的营养,有各种艺术间的相互砥砺、取长补短,更需要有时代精神的引领。当年昆曲《十五贯》之所以能够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主要就是因为苏州太守况钟那种“为民请命”、实事求是办案的精神,在新中国政权创立初期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黔剧代表剧目《秦娘美》《奢香夫人》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的成功,也是因为分别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可见地方戏走出狭小“地方”的规律,都是因为呼应、阐释了时代精神的缘故。而问题意识,正是这种呼应和诠释的引导。问题意识并不只是学术研究才需要有,文艺创作同样需要有问题意识。问题不仅能促动、推动创作,而且还能激发出思想的力量。
应当承认,在全国三百多种地方戏中,黔剧知名度不高。地方戏虽然都是极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但影响力的大小,常常跟各地人文历史的是否厚重以及经济社会的是否发达有关。说中国的地方戏存在“地以戏名”或“戏以地响”现象,绝不是危言耸听。安徽因为有黄梅戏而提升了知名度,这是“地以戏名”;豫剧、秦腔因为根在河南、陕西,因而“戏”也就因“地”而格外响亮。与之相比,黔剧的历史较短,至今不过百余年,再加上贵州地处边远,经济社会发展也比较滞后,剧种因此也就不怎么知名。但越是这样,影响较小的、比较边缘化的地方戏,恰恰越需要有问题意识,这才能导引出新的思考、新的创新和突破,而《湄水长歌》就是这样的一部戏。

二、双主题变奏有阐释历史的新视角
《湄水长歌》双主题结构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它不仅有宏大叙事,而且有阐释历史的独特视角。过去,文艺作品在涉及精英阶层与边远山区、贫困乡村的交结时,通常会有一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视角。那是精英文化,是高一级文明形态对封闭、落后甚至愚昧的俯瞰,里面当然有悲悯、启蒙的思想内涵,但也容易造成对边远山区和贫困乡村的某些遮蔽。一说起来就都是保守、狭隘、落后、麻木。比如一讲到浙大西迁,贵州从来都是容易被忽略的,贵州形象多为被开化、被驱动,或是被描述、被表现。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就只强调浙大西迁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带动。
《湄水长歌》不是这样,贵州人的形象在剧中比较坚挺。它的双主角、双主题结构设计是平行、对等的,没有主次、高低之分,尤其没有潜在的优劣尊卑观念。无论竺可桢的严谨还是严县长的热情;无论浙大师生的悲壮西迁、艰苦办学,还是湄潭百姓的克恭克顺、无私奉献;都堪称彼此尊重,戏份相等,没有倾斜,没有仰视或俯视,不是文明和愚昧的矛盾预设。
一方面,《湄水长歌》不回避湄潭的狭隘、保守,当严县长动员,要给浙大师生让房、让地、让粮时,湄潭百姓开始也有过犹豫,有过矛盾。但另一方面,在抗战精神的召唤下,湄潭百姓最终所选择的,又是接纳和支持,他们的胸怀是无私和博大的。这样的艺术处理,就把湄潭为浙大所作的贡献,放在了与浙大西迁、自强不息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双方同舟共济,奏响的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黄钟大吕之声。双主角、双主题变奏的效果,最终便形成了双峰并峙、“湄水长歌”的寓意。这种平等、对称的艺术结构,体现的固然也是贵州的文化自信,但更是一种阐释历史的见识与能力。无论是过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民族书写,贵州人的胸怀、品格与精神气质,都是需要去发现、去阐释、去表现的。在贵州实施大文化、大旅游、大生态、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有这样的作品。
当然,这里面仍有一个如何去发现、去阐释、去表现的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的贵州确实很落后,最大的困扰是交通闭塞和烟(鸦片烟)、盐(贵州缺盐,市价极高)经济。另外,贵州地域文化中,的确也存在不少负面因素。抗战时期大批文人涌入贵州,都对这里恶劣的交通状况、贫穷落后的现实,以及“干人”的精神困守,留下了极深印象。茅盾、巴金、张恨水、丰子恺笔下,都有类似的回忆。[4]
但即使是在那样的岁月,当年闻一多、林同济等人,也曾在贵州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来自山野的、坚韧的生命力蕴藏。闻一多认为那是能够给抗战带去鼓舞的。闻一多的感受,是受到了贵州少数民族歌谣的启发。那歌谣是:“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一多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5]这一段话,听起来有点另类,但那是闻一多式的抗战宣言。当文化的强大,科技的进步,不被用来造福人类,反被用作凌辱弱小民族的资本时,你能说闻一多是异端吗?一面是原始、蛮荒、野性的生命魅力,一面是现代科技演化成了战争机器,文明与野蛮的逻辑,已经被侵略者颠覆过来了,所以闻一多从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谣里,听出了血性,听出了蛮性,他认为抗战就需要这种精神。林同济的性格和闻一多的豪放、狷介不一样,他要温和一点,但他也反复强调:平原文明应当放下架子,虚心向山地文明学习,不要动不动就是野蛮、落后、改造。[6]
《湄水长歌》对抗战历史与贵州地域文化的阐释,与闻一多、林同济异曲同工,但又有新时代的语境与新思想的内涵。它的双主题变奏既是历史发现,也是艺术创新,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
如前所述,剧作不回避贵州山地文化某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狭隘、保守、落后、封闭。当数以千百计的浙大师生涌入黔北山区一个贫穷的小小县城时,引起老百姓震荡在所难免。《竺可桢日记》对此有着琐碎但真切的记录。[7]《湄水长歌》并不回避这一历史。当湄潭百姓在需要勒紧裤带给师生们让粮让地时,有过矛盾、犹豫,对这些“外来者”充满抵触和排斥。湄潭的官员很狭隘,当他们听说浙大教授谈盛国的夫人是日本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间谍”。精英与民间、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戏剧冲突由此而展开。但一切终当有澄清的时候,当湄潭百姓看到让这些文弱书生奋发自强的动力,竟然是与自己同样的民族屈辱时,他们的胸腔就不平静了,难免会响起和外来者一样的共鸣。来自精英和民间的两种不同的声音,终于在这里汇成了一股激越的旋律。越是有之前的矛盾、误解,湄潭百姓后来对浙大师生的接纳与支持,也就越有艺术张力,那是可以用民族大义、民族大节去解读的。到湄潭之前,浙大从浙江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再到遵义、贵阳,漫漫西迁路已经走了两千六百多公里。在贵阳,浙大面临着到四川还是到云南的艰难选择,是两位湄潭人(陈世贤、宋麟生)向竺可桢推荐了自己的家乡,从而从贵阳把浙大请到湄潭来的。而到湄潭后,立刻得到了以严县长为首的一些开明士绅的鼎力相助,这才有浙大和湄潭从1939年一直延续到今天近80年的因缘。《湄水长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采用双主题变奏形式,浓墨重彩地把这段历史搬上舞台,彰显湄潭百姓的觉悟,这就叫发现,是过去没有人注意,也少有人去尊重的历史。有这样的由头,不仅黔北地域文化,仡佬族民族风情可以更好地渗透到剧情中去,而且有关贵州的地域历史、民族文化,也才会有更大的阐释空间。舞台上的黔北风情与少数民族文化,也才会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艺术真实。
所谓双主题变奏,当然不是说一部作品有两个不同的主题,而是指同一主题的交替变化,或者是同一主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维度的展开。类似的文艺作品有很多,除了音乐的变奏曲比较典型外,其他艺术也不乏类似的创作。凯瑟琳•毕格罗的电影《猎杀本拉登》就是比较典型的双主题叙事:一面是复仇,一面是从女性视角去反思对人的尊重。米兰•昆德拉则直接说,他的《笑忘录》“就是变奏曲形式的一部小说。相互接续的各个部分就像是一次旅行的各个阶段,这旅行贯穿着一个内在主题,一个内在思想,一种独一无二的内在情境,其中的真义已迷失在广袤无际之中,不复为我所辨”。[8]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说,双主题变奏需要有碰撞、有对话、有交流,最后才能汇合到一起,导向一个主题、一种思想。“戏”也才能由此而生,《湄水长歌》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三、双主题变奏有助于黔剧艺术风格的拓展
熟悉黔剧历史的人都知道,黔剧的前身是一种由多人分饰角色,围桌坐唱的贵州扬琴(亦称贵州弹词),清代中后期才从江浙及四川、云南、湖南等地传入。黔剧曲调唱腔清丽优美,当时的爱好者多为士大夫阶层中的官吏、秀才、举子,多是士大夫文人的雅玩、家玩。流布的范围最初也只是文人雅集的场合,如士大夫家庭、堂会,后来才逐渐商业化,由文人雅聚转到茶楼酒肆,成为市井细民的喜好。与贵州的另一种主要的地方戏花灯戏相比,黔剧从声腔到对白都比较适合唱文戏,比较适合庄严、肃穆的正剧、悲剧。花灯戏因为来自民间,它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可以有更多的喜剧性和传奇性,而这在黔剧传统里是少有的。
《湄水长歌》的戏剧冲突,既发生在竺可桢与严县长,浙大师生与湄潭官员、湄潭民众之间,也发生在双方各自的内部。由于从浙江到贵州,从精英到民间,有着很大的地域落差与文化落差,在民族危亡最艰苦的岁月,各方的冲突与磨合必然是一个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的过程,而且事关民族大节大义,无疑,这样的戏用黔剧来表现是非常适合的,这就是蕴含着崇高、峻急、悲壮内容的文戏。2017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湄水长歌》剧本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用黔剧的戏曲艺术形式来表现浙大西迁这一段历史都极为称赞,其中就包括了对戏剧形式与题材内容相对应的某种认同。
《湄水长歌》最感人的一些段落,来自浙大师生与湄潭百姓的碰撞、交流和磨合,一些戏剧冲突,则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当湄潭一些狭隘的官员执意要对浙大教授谈盛国的日本妻子采取措施,引发了谈盛国要“走”与竺可桢要“留”他的尖锐矛盾。严县长作为一个有着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他对浙江大学的支持,比其他官员境界更高,竺可桢与他的相知和相交,除了校方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更有知识分子之间对传承中华文脉的共同理解。这几个地方的唱段,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这样的双主题变奏,尤其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地方,黔剧的方言台词及声腔念白都很好地派上了用场。如果以贵州花灯戏来表现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可能就没有黔剧的效果。黔剧自身的特点、魅力和优势,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某种意义上,这些特点、魅力和优势是附着在题材、人物及表现方法上的,很多唱段都有典型的文人色彩。
另外,从方言与戏曲的关系看,尽管地方戏在如何运用方言上存在着分歧,但我们知道,戏剧的多样性,某种意义上就是方言的多样性。包括地方戏在内,任何地域文化的构成,都会有方言的独特作用。地方戏的台词、念白和声腔,反映着特定地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面貌,是一张张特殊的地域文化名片。作为地方话、家乡话,方言在地方戏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在特定语境中表达某些思想,传达某种情感,只有方言念白和台词、声腔才更准确生动,一旦转换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立刻就失去了特殊的神气和韵味,变得十分苍白。惟其如此,方言和地方戏才是一种与生俱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黔剧的台词、念白全部都是贵州话,唱腔也带有贵州话的发音特点。然而,对贵州人来说,汉语官话方言的长期阙如却是基本的事实。准确地说,贵州汉语官话方言是比西南官话更次一级的地方话。全国任何一个省都有这样的方言,一开口就知道他是哪里人,比如四川、湖南、广东、河南、江苏等等,很好识别。但贵州话不行。贵州人说话,人家可能把他当成四川人、湖南人、云南人,总之不是贵州人,这说明贵州汉语官话方言不能以言识人、以言识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历史上,贵州的建省是为着经略云南边疆的需要,从云南、四川、湖南、广西各切一块拼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析地建省”。如此一来,贵州也就成了介滇、介蜀、介楚、介粤之区[9],其文化是输入的,方言难免就带有邻省的特点。
贵州汉语官话方言的阙如,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与历史上缺少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有关,与移民史有关等。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也比较重要:那就是贵州方言缺少包括黔剧在内的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其他省的方言都有这个传统,并且这个传统都跟地方戏有关。比如豫剧、越剧、秦腔之类。相比而言,贵州直到明清时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传统才逐渐明晰起来。黔剧的出现(包括花灯戏),是这个传统极重要的一环。虽然时间晚了一点,但如果好作品层出不穷,对形成这个传统一定会有极好的推动作用。问题的关键,还是需要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黔剧和贵州花灯戏对此可谓重任在肩。
《湄水长歌》是在《秦娘美》《奢香夫人》之后又一部大型原创黔剧,它的语言是以贵阳话为标准音的贵州汉语官话方言,台词、念白的吐字发音与戏曲演唱的声、腔调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地方味十分浓郁。可以想象,如果多有一些成功的黔剧作品,借助艺术形象的魅力,贵州官话方言声、腔、调的特点一定会为更多的人所熟悉,那样的话,贵州官话方言的阙如,或许就会逐渐成为历史了,而贵州文化的影响力,也就一定会获得相应的提升。
《湄水长歌》的不足,主要是双主角、双主题的尺度还应做更好地把握,比如戏份多少及主次详略。现在的感觉,是严县长的戏有点抢。过于强调湄潭在浙大西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会矫枉过正,不利于主题变奏的对等和匀称。另外,剧情也还可以再紧凑一些。目前的戏剧冲突还有些枝蔓,不够集中,谈教授的日本夫人刚刚有点戏就结束了,与敌特的戏一样,对双主题结构来说,有点游离。二是有的台词和念白太现代,且过于直白浅露,文化底蕴不够深厚。尤其是竺可桢、谈教授等浙大师生的台词和念白,应当有更多的文采。这方面应从当年浙大“湄江吟社”的作品中吸收些素材。[10]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