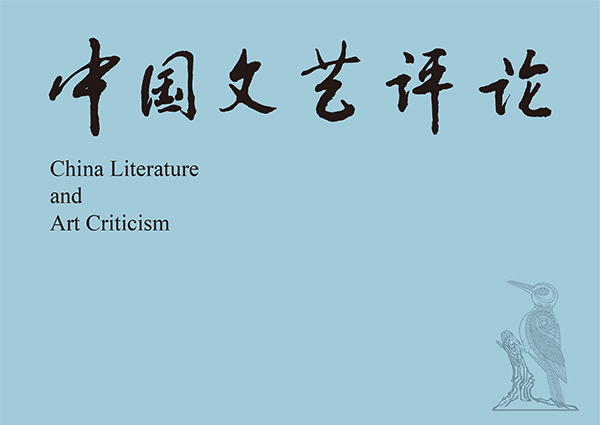
内容摘要: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精神问题,并不都是艺术所要表现的,艺术表现的是那些关系到活着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价值、生死的焦虑等根本性的精神问题。叙事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生命能否有大格局、大气象,取决于人物遇到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取决于人物在面对精神问题时内在挣扎的经历和程度。
关 键 词:叙事艺术 经典作品 精神问题 生命自由
一
作品中的味道,是我阅读和观赏叙事作品时特别注意的。有的作品有味道,有的作品就没有味道。有味道的作品有内在张力,而没有味道的作品虽然用力,却没有那种深入、透彻的生命感觉。作品的味道与作品中的精神问题有关,与人物纠结什么、挣扎什么有关。
人活着会遇到很多精神问题,伦理的、情感的、物质的、欲望的,形形色色。我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精神问题,并不都是艺术所要表现的。艺术要表现的,是那些根本性的精神问题。根本性的精神问题给人带来的内在纠缠、迷茫、挣扎、选择、决绝等,才是艺术内在精神张力生成的源头。或者说,艺术的精神力量,源自艺术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
每一生命个体,不管什么出身,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处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遇到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大致相同,因为他们有一样的生命本质。那么,哪些精神问题才是根本性的?我们反观自身,审视一下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对这个问题都有答案。那些关系到活着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生死的焦虑的,就是人在现实中常常遇到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它们看似玄虚,不着边际,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如生命的尊严,你失去一次,就会屈辱一生。在群体中,你被强制和野蛮无端羞辱,或违心地献媚他者,你的内心会打下一个死结,永远无法解开,除非你不在意生命尊严或者是一个无耻的人。
叙事艺术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是融化在作品人物的生命之中。生命化的东西,就不能像哲学那样去辨识,也无法阐述清楚。我就曾对叙事艺术所触及的精神问题,特别是根本性的精神问题,试图梳理、表述,想让别人对我说的一目了然,从而在学理上证成我说的,可是我做出的任何一种概括都不完整、准确。对叙事艺术中的根本性精神问题进行任何概括、界定、抽象,必然徒劳无功。但我并不失去信心,因为面对具体作品时我的感觉在:人物纠结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前段时间,我被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态度所感动。他强调“对自己的责任”,强调理论的原创性。原创性理论,只能来自自己内部的觅得,是自己的的领悟、发现、认知。维特根斯坦给予我的启示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者,要想说明问题,还得结合作品,尤其是要以经典作品为案例,细细体会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纠结,接近人性的真相,感受人性深处的复杂和混沌,发现哪些精神问题影响着作品的品质。我细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尔比的《在家在动物园》、毕希纳的《丹东之死》、塞林格的《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契诃夫的《吻》等,体会苔丝、葛利高里、安娜和彼得、丹东、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生命困境,揣摩他们的内在状态,发现他们的精神痛点都与独立、自由、孤独、存在这些生命的大问题有关。其实每一个有生命感的人,不管处境好坏,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独立和自由驱力,都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存在感。这独立和自由的内在驱力、孤独和存在的感觉,来自于人的现实与内心的断裂。独立和自由的向往一经冒出,便遭遇有形和无形力量的钳制,从而造成个体生命挣扎的孤独和存在的失落,这是有生命感觉的人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是生命的大问题,这大问题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决定了人物的生命格局,决定了作品有无我说的那种味道。
二
书写根本性精神问题的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只是“触及”,而不提供答案,也没有答案。这是因为,叙事艺术中的根本性精神问题隐于生命内部和人性深处,所以它是模糊的、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去感受、体悟。或者说,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困惑、纠结、挣扎、驱力搅在一起的复杂和混沌。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却有生命的确切感,创作者和接受者谁都能感觉到,谁又无法表达清楚。
对于接受者来说,他阅读和观赏作品时,被叙事带入对人物精神处境的体验,在体验中经受生命,触摸精神痛点,领悟精神症结,从而获得关于生命本质的启蒙。这种深度启蒙是从体验中获得,启蒙的发酵效果是在人的身体内部产生的,这就是作品的味道和精神力量。

《德伯家的苔丝》
最近重读《德伯家的苔丝》,发现苔丝虽然活在19世纪,可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痛点却引发我对当代人精神问题的联想。她几经起伏,经历了由单纯到复杂、自然到异化的精神演变过程。她的悲剧在于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是由别人决定的,从来没有独立过。渴望拥有她的亚雷,把她作为纯洁象征的安玑,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形成合力改造她的天性。被重新塑造的她,不觉醒,才背负沉重罪感。时代道德完全融入苔丝的血液和灵魂中,让她自愿地承受罪感的折磨和惩罚。“失身不洁”就像石头一样,死沉沉地压着她。安玑向她示爱之后,她一直为自己不配安玑而痛苦,唯一的渴望,是安玑的原谅和接纳。她的痛苦和诉求非常清晰,却不内省,存在意识相当模糊。她永不消逝的美丽,对安玑的执著,对独立生命消失的迷蒙,把读者带入不可言说中。她的天赋丽质,她的健壮丰韵,尤其是她劳动时的从容,让任何一个读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为之心动,可是,当看到她无止无休地折磨自己时,觉得她又被一团雾气罩住,变得模糊,让读者意兴阑珊。哈代在创作《德伯家的苔丝》时有着高度自觉,大段大段地写苔丝的内心世界,好像钻进了苔丝的内部,全知全能,把苔丝写成实心人物,但最能表现苔丝人性深处状况的生活,如她与亚雷、安玑的真正私生活和切身感受,操持全视角的作者又不在现场,留下空白。可以想象,两个男人能置她于绝境,也能激活她的觉醒,给她以存在感,小说的叙事却在关键处终止或越过。哈代是不是通过叙事缺席,有意把精神问题留在读者体验的延伸之中?不管怎么说,只要细读这部小说,苔丝就会成为生命存在的启蒙资源。
还有一个人物和苔丝一样,让读者感到既清晰又模糊,他就是海明威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麦康伯。以前我看重这部小说中的两点,一是它完成了麦康伯从软弱到勇敢的变化过程。弱者到强者的蜕变,有丧失尊严的耻辱,也有维护尊严的悲壮;二是人物间作用的张力,麦康伯的变化就是妻子玛戈和威尔逊蔑视、偷情的反作用的结果。当我思索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时再读它,发现还有另外的读法。麦康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一瞬间,退缩自保,是合乎人天性的选择,软弱也是一种自由,而且是人性本原的自由,应和勇敢享有相同的尊严。而作为外界存在的玛戈和威尔逊,歧视、压制这种自由,扭曲这种天性。麦康伯按照他者规制的男人标准重新造就另一个自己,像打了鸡血似的挑战野牛,成为“勇敢的男人”,最后死于玛戈枪下。我设想,如果他活着,后来的他,肯定怀疑自己的“勇敢”,为自己的舍弃和妥协陷于迷惘,成为一个寝食难安的人。他消失了,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当一个生命违背自己的天性,按他者的要求去改变自己时,他的本真就不复存在。海明威崇尚冰山理论,把自己的叙事意图隐匿于海水里边,正如玛戈是失手误杀还是谋杀丈夫,真相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海明威让我深刻体会到詹姆斯•伍德说过的一句话的分量,那句话是“空隙和实体具有同样的深度”。
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都是人性的问题,而且是人性深处的复杂问题。木心说:我憎恶人类,但我迷恋人性的深度。人性的深度是什么样的?估计没有人能够表述清楚,你得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命去体会和领悟。苔丝、麦康伯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让读者在经历生命过程中,感受人性深处,领悟生命的存在和尊严。
三
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只具有生命感的人才会遇到,与他是英雄还是平民百姓无关。现实中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有生命感,“生命感”对于现实中的人,是一种缘,有了“生命之缘”,才有那根敏感神经,对精神问题才有感觉,有反应,才纠缠不清。这和佛不度无缘之人一样,一个与佛无缘的人,他的金刚种子还没有发芽或者没有种下,他就悟不到佛法的精髓,感受不到佛光。艺术也是如此,也有缘分一说。一个人没有“艺术之缘”,他就感受不到艺术与生命的血肉关系,感受不到艺术的神圣,自然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好的艺术。
优质的叙事作品只能出自有强烈生命感、并有足够内心自由的创作者之手。创作者的生命感和内心自由,最终决定作品的品质。在作品中,不管轻若微尘的小人物,还是左右历史进程的大人物,只有在他对生命的存在,对生命的苍凉和荒谬有感觉,并经受生命根本性问题的折磨时,他才活着,才有生命张力。
《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彼得和安娜,都是现代的普通人,一个温文尔雅,一个安静端庄,丈夫没有外遇,妻子没有第三者,日子过得平淡而美满。戏从这安逸、平和、舒适的家庭生活开始。安娜突然想作妖,要疯狂一次,这让彼得惊醒,意识到自己也处在压抑和绝望之中,也渴望突降一股龙卷风,摧毁他们现有的安宁。在家受到刺激的彼得来到动物园,又遇到孤独的杰瑞。杰瑞几近疯狂的坦露,激发了彼得反思与妻子的“扭曲、断裂和隔绝”的关系,从而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种疏离本性的孤独。再看《丹东之死》中的丹东。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功臣,国民公会代表,掌握生杀大权,曾把许多人送上断头台。就是这个风云一时的大人物,在享受革命果实时却质疑自己曾经投入热情和心血的革命,而迷茫于个体生命的消逝,认同妓女玛丽昂及时行乐的正当性。安娜、彼得和丹东,生活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和处境也无法比拟,但他们遭遇的生存危机和精神问题却相当的一致,这与他们的身份标识、地位高低无关,只与他们的生命感和生命悟性有关。

《小说机杼》
作品中的人物不一定非得遭遇重大变故和挫折,亲临危机和绝望,才能触及根本性精神问题,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动荡小波折,就可能让他体验到现实与内心的断裂,质疑自己的存在,感悟生命的荒谬和悲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称这个小说对人物心灵质询的生动程度超过了别的作家,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又说只有像契诃夫那样的严肃观察者,才能写出《吻》中的那些细节。除了詹姆斯•伍德说的这些之外,这篇小说还是小人物在小事情中触动大问题的范例。
小说中的上尉亚包维奇,其貌不扬,站在军官堆里毫无光彩。有天他和同伴到驻地一个地主家参加舞会,别人在舞场上尽情狂欢,他却独自溜边,因为他从来没有跳过一次舞,胳膊也没有搂过一个上流女人的腰。他闲逛到一间幽暗的屋子,有个女人匆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到底来了!”然后抱着他的脖子热吻起来。随后,那女人发出微微惊叫,吻错人了。这种偶然如天际的一道彩虹,不期而至,转眼消逝,从此了无踪影。然而,它在亚包维奇身体里持续发酵,“一种生平从没经历过的新感觉”抓住了他,让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特想畅畅快快地放开自己,“由着自己的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后来他忍不住和战友讲了那晚的事,想让他们分享快乐。他极想把那让他浑身燃烧的艳遇讲得绘声绘色,可是一分钟就讲完了,而且干干巴巴的。别人听了,不是认为他无聊,就是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他诅咒再也不和别人说这事。小说的最后两页意味深长。部队又来到那晚的驻地,他心神不安,想像着跟她重逢的情景。可是很晚了,地主家也没人来邀请他们。他坐卧不安,一个人来到河边。河水流得很急,发出咕咕声。奔流的水让他醒悟:那个亲吻的事,还有他的焦躁,他的希望和失望,和整个世界、整个生活一样,都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目的的玩笑”。他回到营房,屋子空了,战友们被地主请走。一刹那间,他心里腾起一股冲动,可是他立刻扑灭了它,上床睡了。上尉亚包维奇遇到的错吻是件多么小的事,小到一分钟就讲完了,可它在他灵魂中生成的荒谬和悲凉却是大事情。荒谬和悲凉饶不过任何人。
亚包维奇临水而悟。水是神圣之物,流逝的河水总给人以神示,让人彻悟。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中的悉达多,也受惠于河水。悉达多成为富有者之后将所有财富抛弃,去寻找那个内心的自我。他来到河边,向船夫讲述自己的经历,船夫安静地倾听,悉达多为他的专注而感动。船夫告诉他:河水教会我如何倾听。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河当作去路的障碍,只有几个才在过河时用心去谛听水声。悉达多留在了河边,成为一个摆渡者。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生也是一条河,自己要做的,是静下心倾听这条河的声音。
四
一部叙事作品能否触及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还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生命格局。生命格局是指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气象,或者说,是指人物生命的格调和气势。在作品中,决定人物的生命能否拥有大格局、大气象、大气势,和他在什么情境下遇到什么样的精神问题有关,和他面对精神问题时的内在反应有关。
叙事作品的创作者,想让人物的生命有格局、有气象,那他首先必须让人物触及到生命中最敏感的问题,即生命的自由、尊严和苍凉。敏感的生命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个体的存在上。一个人活在人群中,最可怕的是合群,一切都和别人一样,自我迷失在人群中。所以,一个人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用自己的思想和创造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就成了最根本的生命问题。说这问题敏感,是因为在独立的过程中,个体要遭遇他者的压制。一旦受到压制,个体对自由就有了强烈的感觉和诉求,生命的尊严和苍凉感也随之在人的内心深处生成、涌动。压制个体的他者,是强大的社会存在,历史的当代的,政治的伦理的,有形的无形的,这些构成生命个体追求自由、维护尊严的背景,这个背景同时给予个体生命以压制和反制的动力。这里,我自然想到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作品中的葛利高里,生命格局很大。他是一个强悍的哥萨克人,驰骋顿河岸边,守护属于自己的安宁。作为顿河的儿子,他要为顿河左岸哥萨克人的平安生活尽一份力量;作为情人,他要和阿克西妮亚在一起,像一个男人那样呵护她,不管她是不是有夫之妇,爱她就是理由。葛利高里的追求遭遇了大革命和道德的制约,他陷入痛苦。痛苦中的葛利高里阴郁而高贵,因为他痛苦,有心绪,有意志,和别的哥萨克人相比,他强悍而又有精神光芒。他痛苦中的质疑、挣扎、无奈,都直接触及生命的自由和尊严。决定葛利高里生命格局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让他内心痛苦的都与个体的存在、自由有关;二是他遇到生命问题的现实背景。他内心挣扎与重大政治事件纠缠在一起,使他的精神痛点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性。他的内心诉求与他所处的现实断裂,是现实让他的精神之痛更重、更深入内心。

波兰电影《审问》剧照
有人会说,人物生命有大格局的作品,一定是大部头的,因为大部头的作品才有足够的叙事空间,才能充分展开人物的生命过程。人物的生命格局的确与他遇到根本性精神问题后挣扎的过程有关,但决定生命格局最关键的是人物为问题挣扎的程度。比如叙述人生劫难的波兰电影《审问》,影片把人的困惑、挣扎、崩溃表现得酣畅淋漓。女歌手托尼娅因为与一个被怀疑有叛国行为的官员交往而被捕入狱。她的身体遭受极其残酷的折磨,审讯者要她说谎,出卖别人,而经过恐惧、绝望之后,她有了一个想法:不说谎,不出卖别人,守住这个底线就维护住了自己的生命尊严。这是心理支撑,更是一个信念,信念使她变得有力量。我要说的还不只这个托尼娅,还有那个审问她的少尉警察,他被她的忍耐、信念击垮,最后开枪自杀。我们看他的眼神和情态,看他对托尼娅的压抑又释放的复杂感情,在托尼娅的肉身被无情摧残的同时,他自己的灵魂也遭遇拷问。拷问什么,影片没有表现,但那一定是直见性命的精神问题,不然他不会垮掉。他的内心挣扎与托尼娅的忍耐都有冲击力,如果从感染力的持久性上讲,他更有精神张力,他的生命格局更大。
五
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艺术中的人,不是“类”,不是“群”,而是个体。优秀叙事作品的创作者,不管他自觉与否,内心深处都笃信个体生命的自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在现实中,他笃信的生命意义被无情地扭曲、蹂躏、改造,这就是现实与内心的断裂。这种断裂谁也逃脱不掉,让人无奈和绝望,但它却孕育着文学和艺术。作家和艺术家在断裂中挣扎、纠结、体验、领悟,经过一番折腾,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好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用灵魂来创作的。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最终还是创作者自己的问题。
我必须说塞林格,必须说他的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塞林格是用灵魂来写作的作家,《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是他用灵魂写作的范本。这是一篇短篇小说,虽然很短,但塞林格在《纽约客》两名编辑的帮助下改了一年,可以说是磨出来的。它讲述了二战退役青年西摩在与妻子度假时自杀的故事。西摩的自杀,是他痛苦中的理性选择。在战争中,从森林战场到集中营,亲历的残忍毁坏了他信奉的真理。在小说中,西摩在海滩、在浅海里陪那个小女孩儿做逮香蕉鱼的游戏时,脑子里转悠着香蕉鱼和西比尔两个寓言,这两个寓言隐喻着人的欲望和困境。他表面轻松、超然,内心却经历着痛苦挣扎,自杀只是他内心挣扎的一种结果。塞林格把西摩的灵魂样态隐藏在叙事的空白处,读者只能在空白处感受人物的灵魂。塞林格曾经建议一个写作的朋友:写“火”,不是把火写进字里,而是放在两个字“之间”。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挣扎、波动,全在人物的行为、状态之下,由读者感悟出来,不是作者出来告诉读者“在这儿”。 小说的空白处才是塞林格小说的门道所在。塞林格写西摩,实际是在写自己。他在《西摩——序言》里明确说,西摩“并非西摩其人,而是,见鬼了,哎呀,一个与我自己很像的人”。塞林格也是一个退役老兵,他一直不敢直面战争留下的创伤,通过炼狱般的挣扎,最后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痛苦,也恰在这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毕希纳写《丹东之死》,其实也是在写自己的问题。在人权协会遭到破坏,会员一个个被捕,自己也被监视的情况下,他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让他陷入道德公意和个体欲望的纠结中,于是,他以质疑的笔触,贴着个体生命,写出《丹东之死》这部穿透历史和生命的戏剧。塞林格和毕希纳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个案,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布加斯基拍《审问》,都把自己的精神问题融入作品人物的生命中。一部优秀的叙事作品,是创作者的精神演练,其精神内核都与创作者的精神诉求有关,是创作者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创作者有足够的内心自由,他才能触及人性深处的复杂,才能用自己内在的生命运动,去生成作品人物的精神肌理。
这是叙事艺术的叙事伦理。创作者在叙事中遵循自己的内心需要,表达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这本来是作家和艺术家在叙事时的天然诉求,但今天却成为一种理想的叙事境界,这是叙事艺术的悲哀。遵循内心需要的叙事不是惟一的,但今天却是最有价值的。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