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这样在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
陕西“三大家”,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商洛的贾平凹,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文学世界。路遥、陈忠实的文学导师是柳青,柳青的小说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最近阅读柳青佚作《在旷野里》,他精炼的文字、对关中风景的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很深的功力,对话很能呈现人物性格。路遥、陈忠实的小说,无论风景描写,还是人物刻画,甚至小说结构,都受到柳青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来自商洛的贾平凹不在这个影响范围中。他的文字柔媚、暧昧,更像是南方水系文化的表征。要说影响,他可能受沈从文的影响比较多。但其实更多还是他的天赋,他对世界的体悟可以说是商洛这片土地给予的。从文化传统来说,大概属于庄禅一路。尤其《废都》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写作基本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的特殊道路。
商洛,因为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坐落于陕西东南部,秦岭南麓,可谓楚头秦尾之地。《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1)。商洛道,也称商於古道,是秦驰道的主干道之一,可谓秦楚咽喉,历来是交通要塞。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的就是商州。贾平凹曾自豪地说:“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2)
商洛地貌复杂,层峦叠嶂,有洛河、丹江等五大河流经过。北部属于黄河流域,暖温带气候,贾平凹的家乡丹凤县则属于长江流域,亚热带气候。贾平凹曾说:“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3)贾平凹在商洛市丹凤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19岁才远赴西安求学。某种意义上,商洛这块土地造就了他,也养成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贾平凹多次撰文写故乡,他在《秦腔》后记中说:“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作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4)
贾平凹初中没毕业就回乡做了农民,这段生活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颇大,不仅造就了他敏感、固执的性格,也让他熟悉了农村,深度认识了乡民。贾平凹的父亲是其老家南寺小学的教师,1949年前毕业于陕西师范学校。这种家庭文化熏陶是不可低估的,家里有这样的人,等于给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子。贾平凹在散文《我是农民》,以及《纺车声声》《头发》等自传性小说中,多次写到父亲,可见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对自己在故乡的这段生活有深入反思,他承认“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5)。在《我是农民》中,他更痛彻地写道:“人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6)
贾平凹深知,和城市孩子相比,自己有哪些不足,这也激起了他的反抗,他发誓要出人头地。用文字不断书写故乡的过程,也是精神返乡和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他不写,就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贾平凹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7)是的,故乡是作家的血地,是很多优秀作家一生魂牵梦萦之地,不管你爱不爱它,它就在你的心里、你的肉体里,影响甚至决定着你的一生。贾平凹对故乡的情感,在作家里也是很特殊的,它是如此深厚,以致几百万字都写不完。我两次去棣花,走在不大的村镇,很难看到贾平凹笔下的故乡和这里的相似性。大概他写的是他心里的棣花,这个棣花已经独属于贾平凹了。这片土地深刻影响了贾平凹,绘就了他的文学地图,故乡的人物、历史、地理从精神上塑造了他。不管是写故乡,还是写西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入口。某种意义上,商洛的19年,奠定了贾平凹的思维模式和小说书写方式。贾平凹后来走向庄禅,包括《废都》之后那种汤汤水水、鸡零狗碎的新写法,其实都与故乡有关。

二、 直觉与呈现式写作
我一直认为,作家的直觉是创作成败的关键,而这大多来自天赋,学问的积淀虽有帮助,但不起决定作用。从《浮躁》到《废都》,再到《河山传》,贾平凹靠的就是以直觉呈现当下时代,这是他的优异之处。贾平凹说:“《河山传》依然是现时的故事,我写不了过去和未来。”(8)写过去,可以是总结,也可以查阅史料;写未来,是一种想象,像科幻小说。写当下,其实是最难的,因为还没有沉淀,没有时间的隔离,即古人说的当局者迷。贾平凹喜欢写当下,比如《废都》就对当时的时代特征把握得很有深度。对当下时代的整体把握,靠的是他过人的直觉能力,甚至是一叶落而知秋的预见性直觉。
在西方,直觉起初是一个神学概念,人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或修辞论证认识和感知上帝,只能通过冥想,“人们对上帝‘洞见而不理解’,洞见是一种直接的直觉,可以在沉醉状态中达到”(9)。柏格森认为:“直觉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能使我们隐约看到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10)。总之,直觉是无法用逻辑推理论证的,是通过直接感知对象,是一种“当下即悟”的内在活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部体现意识流与审美直觉的代表作。贾平凹在商洛大山里居住了19年后才进入城市,可以说,他的直觉除了天赋之外,大多来自商洛,来自他的家乡棣花镇。在小说创作上,作家对时代的直觉把握,往往比用概念判断的人更加精准和及时。在对时代的表达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使用呈现式写法,《河山传》也具有这个特点。
在《河山传》的篇名中,“山”来自老板罗山,“河”就是罗山的跟班洗河,这部小说等于是两个人物的合传。《河山传》是编年体的写法,从1978年写起,主要内容分四章:洗河(一九七八年—一九九六年)、罗山(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董事长和助理(一九九八年—二〇〇一年)、花房子(二〇〇一年—二〇二〇年),还有一个前言、一个后话,最后是后记。
河山,也可以说是渭河、秦岭,再延伸一下,就是山川、社会。贾平凹不太擅长人物塑造,但刻画时代氛围却拿手。如《废都》对1990年代初时代转型期的呈现,那种况味一般作家真写不出来。《河山传》多的是叙事,几乎就是靠对话在推进,景色描写、肖像描写也是寥寥数笔。作家文丑良的几次跳出来议论更是突兀,与全书的氛围不是很谐和。贾平凹本来就不是以思想见长的作家,他的特长在呈现,呈现他对时代的直觉。
《河山传》的时间跨度(1978—2020),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有学者认为它“是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在立传”(11)。《河山传》更像是一部“问题小说”,它通过一座叫花房子的别墅,将农村和城市,将不同生活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联系在一起,不仅写出了人生百态,更呈现出一个鱼龙混杂、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当下社会。
小说采用编年体的方式,通过对特定时代具体事件的呈现,素描了中国社会40多年的大变化。贾平凹的作品惯以时间开头,初看像是记账簿,但大量日记体式的细节刻画,颇有可读性。贾平凹喜欢用时间词来定位或者推动情节,如“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转过年的四月”“六月二十一日”“又过去了一年”“在七月”“秋后”“这事过去了二十天”等,每个时间表述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时间表,而且很具体,呈现出历史书写中“本纪”的笔法。
贾平凹对洗河初进西安的描写真实、生动,如作者亲历一般。贾平凹喜欢用繁密的对话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这种白描式的呈现方式很考验作者的功力。贾平凹曾谈到《尤利西斯》等现代小说对他的影响:“《尤利西斯》这本难懂的书你可以什么都没有看懂,但你要看得懂它是怎样把潜意识的东西用语言传达出来……现代小说的语言更具有独立性,能直接达到目的。学习现代小说的语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旧的文学思维,要确立新的文学观。有了新的文学观才能真正地学到真髓。”(12)他还举例说:“比如我们写张三和李四说话,张三问:你吃早饭吃的什么?李四说吃的稀饭。张三又问:下饭的菜呢?李四说:是咸菜。以传统的写法,我们就一问一答地写了。而乔伊斯不这么写,张三在问李四:你早饭吃什么?张三是看着李四的,李四或许坐在窗前椅子上,但现实生活中张三问李四这句话时眼看着李四,眼里的余光一定就同时看到了李四身后的窗台上还放着一束花,窗子的帘布是红色的或白色的,这些他全看到了,但看到这些一定会反射在他的心里,觉得那束花好看不好看,花是谁送的,帘布合适不合适,是谁买的,又用过多久。这些都是潜意识,不会说出口,更不会影响到他在问李四你早饭吃的什么,乔伊斯却在一问一答中同时把这一切都写了出来。”(13)对小说如何写,贾平凹是有自觉认识的,也做了很多尝试。
《河山传》不是传奇写作,基本是通过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呈现一个时代。如一座花房子别墅改变了村里原有的秩序,去花房子工作的帮工有钱又有闲,让村民感受到贫富的差距,并对帮工的高收入产生了妒忌心理。这部分的叙述,在鸡零狗碎中透露出一个时代的变化。贾平凹比较擅长描写混乱的场面,对环境的描写虽不多,也呈现出时代的众生相。小说开头写洗河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此处对劳务市场的描写颇见功力,细小的场景描写,映射出时代的巨变。作家这样描写等活的人:“他们似乎好几天没有洗脸了,头发蓬乱,面色憔悴,在等待着那种眼巴巴的样子,像饲养场前爪子搭在圈墙头上待食的猪。雇主一来,又像鸭塘里扔了石头,所有的鸭子涌动,呷呷声乱。永远有幸运的和不幸运的,能被招领的跟着雇主走了,嬉皮笑脸,没被招领的又很快安静了,委顿着,疲惫着,蹲在地上咳嗽,擤鼻,啃吃着干馍,低声咒骂。”(14)
小说对呈红的书写也比较有意思,呈红在小说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是个投机者,靠色相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凭借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而不断上位,做人毫无底线,眼里只有金钱。她通过罗山结识了郑秘书长,很快成了郑秘书长的情人,后来郑升迁为副书记,之后被抓,她乘机霸占了郑的别墅,又和别的男人同居。贾平凹说:“中国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民思想为主的国家,虽然好多人已经进城了,但意识还是农民思维,聪明狡猾,又诚实又狡猾,又可怜又可憎。非常复杂,所以改革开放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15)贾平凹通过书写洗河、罗山、呈红这样一群人,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样貌,用小说表达了他对时代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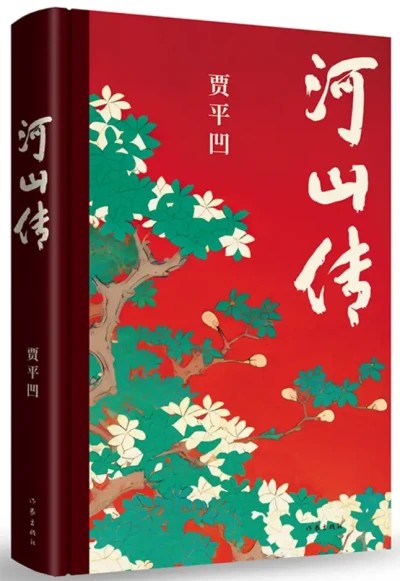
三、 庄禅思想与现代主义技法
有学者认为,贾平凹受了《金瓶梅》《红楼梦》等的影响,但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刻画人物见长,文字精炼,结构明晰。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写作却越来越汤汤水水、鸡零狗碎,结构很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不重视人物刻画,也不强调故事情节,就是混沌而来,混沌而去。雷达认为,《秦腔》“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元素”(16)。其实,贾平凹《废都》之后的长篇小说大都有这个特点,《浮躁》的写作就已经开始使用现代小说技法。
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里特别喜欢跳出来说话,只是用的是小说人物的口吻,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他的替身或影子。这种写法很像现代主义小说追求整体的象征或隐喻。1996年,在《土门》座谈会上,贾平凹提到了他在形式上的探索:“后来我感觉一有情节就消灭真实。碎片,或碎片连缀起来,它能增强象征和意念性,我想把形而下与形而上结合起来。要是故事性太强就升腾不起来,不能创造一个自我的意象世界”,“张爱玲一生都在写《红楼梦》的片段,张爱玲为什么不旧?因为她加入了现代的东西。”(17)
贾平凹的小说一开始就不太重视客观描写,其主观性很强,比如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他的小说由于太喜欢主观书写,呈现内心的黑暗、痛苦和烦恼,还多次受到批评。1980年,他28岁时写了散文《静虚村记》,可以看出他对庄禅思想的倾心。从短篇小说《好了歌》《晚唱》,都可以看出他的探索。1982年,他的《“卧虎”说》发表。同时,他也阅读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日本古典传统结合的创作之路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费秉勋在《论贾平凹》中指出:“他既用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用过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小说很少做事件全过程纤毫毕见的再现,那些细腻的、娓娓不断的描述,都是通过微末的细节在品味着醇美的诗情。”(18)不过,费秉勋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贾平凹的诗人才情。其实,这种现代主义的写法,是贾平凹自觉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结果。他1984年就强调“破除框式,搞中西杂交”,倡导把民族传统的东西和外来的、现代的东西,“融汇化合,走出一条极民族化的又极具现代意识的路子”(19)。川端康成之外,拉美文学对他的启发也很大。他还阅读了大量现代派哲学、文学、美学书籍。
贾平凹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有较深体悟的,这在他的绘画上可以看出。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之余雅喜书画,已出版《贾平凹书画》(花城出版社,2007)、《当代名画家精品集——贾平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贾平凹语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等。他的书法有点碑的意趣,适合写大字,字一多章法就略显紊乱;他的画,题材多庄禅,颇有超现实主义色彩。他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可能从西方美术史中吸收得比文学史更多一些,这一点与鲁迅颇为相似。
从贾平凹的画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画作有一种禅机,没有严格的技法,却有一种自由随意的洒脱。他画了很多有关佛的画,画作大都充满禅意,或荒诞,或夸张怪异且神秘,笨拙中自有一种童稚的憨态。如画作《漂泊的草》,一个人裸体漂在河里,身上长出草木,草木伸出水面。又如《服装与花》,一件右衽长袍,从衣领中间长出一朵荷花。从他的画作可以看出,在佛和道之外,他还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写道:“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得益最大的是美术理论,在二十年前,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各流派的美术理论让我大开眼界。”“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观念,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结合了,如面能揉得倒,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比如,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澈。”(20)这些文字说明,他小说上的新写法是一种有意识的尝试,虽然不一定很成功,但这种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写道:“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21)
中国的水墨画,其核心就是庄禅。用徐复观的话说,中国艺术的精神就是庄子。这与西方的现代美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贾平凹对两者的迷恋,对他的小说写作影响很大,这在《废都》之后的小说写作里是可以看到的。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还说:“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22)
庄禅在某种意义上就很后现代,所以贾平凹的小说就有了格外的艺术形式。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都呈现了时代的氛围、时代的变迁。贾平凹的小说,某种程度上也呈现了当代社会的变迁、文化思潮的演变,甚至时代精神的变化,这也是他长篇小说最大的贡献。贾平凹的小说技法有接续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面,但内里也多有西方小说技法,比如打散、解构的写法。一部长篇小说在设计一个严谨的结构时,是需要功力的,但打散、解构的写法更需要胆量。如果解构了而没有成为一地碎片,那自然需要更强大的功力。
现实主义是写真实,但是过于讲究起承转合,重视前后照应,往往会显得不真实。真实的生活,确实是汤汤水水、鸡零狗碎的。很多人见一面后,可能一生都不会再遇上。人生有逻辑吗?真实的生活,可能真的就是碎片化的,而且越是现代的日子,越是全球化的日子。从前,一个人的人际交往就只有那些人,现在的人全中国、全世界地跑来跑去,日子越来越没有逻辑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写法,在描写这种新的人生常态和心理变化方面是有优势的。
贾平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秦腔》后记中说:“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23)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小说注重结构,强调情节,重视刻画人物形象,追求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喜欢营造悬念,而现代主义小说正好相反,比如《河山传》的开头,就将小说要讲述的故事和盘托出,不留悬念,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写花房子里的鸡毛蒜皮,泼烦无聊。《河山传》不太注重结构的完整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整体呈现出一种情节淡化,结构松散的碎片化特点,正是这种非情节、非故事、非人物的特点,凸显了时代巨变中的人生百态和复杂的心理变化。小说的结构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但也多有闪回、插叙,这些更多是一种心理时间。比如在绑架熊启盘的描写中,又插入了于长峰、于长岭兄弟的后代因30年前“土改”时房屋历史遗留问题发生冲突的小片段。
《河山传》的很多人物都是意外死去的,还有些人偶然地出现,偶然地死去。如洗河的爹外出打工,因爬上脚手架看稀罕,掉下来摔死了。从崖底村外出打工的人,“有架线时被电打死的,有过马路被汽车撞死的,有掮着一捆钢管小跑着突然倒地死的。还有李建社给立交桥的桥墩浇灌水泥浆,自己头晕跌下去,浇灌的水泥浆还在继续,他永远凝固在了桥墩里,连尸首都没拉回村”(24)。楼生茂做爆米花是为了寻找被骗子拐卖的女儿楼小英。楼家父女的命运牵系着读者的心,可在读者期待楼小英的结局时,小说却不再叙述。只是后来洗河偶遇楼生茂,才知道“女儿后来是找着了,但已经给人家生了孩子,这事就算了,各人有各人的命,他也让她过自己的日子吧”(25)。短短一句话就对楼家父女的结局进行了交代。后来,楼生茂死了,楼生茂的死也很偶然,他在偷盗工地钢筋时,被倒塌中的墙砸中。这些情节全是打碎了穿插其中,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占的篇幅很少。
《河山传》的故事不强调逻辑性,显得碎片化、偶然性,凸显了人生无常和底层人的卑微。比如写花房子的建造,中间总穿插一些碎片化的事故。花房子的工人施某在施工过程中打了一个喷嚏,无意间扣动了手里射钉枪的扳机,钉子击中了另一个工人马某,马某从脚手架上跌落致死。罗山的煤窑出了事故,砸死了人,罗山赔偿了9万元,最后发现是一场骗赔偿金的谋杀案,而被预谋杀害的是个流浪汉。
现实生活本就是一地鸡毛,没什么悬念、情节、高潮可言,都是琐碎小事。《河山传》以洗河和罗山为中心,用类似于散点透视的方法,铺陈人事,试图呈现40多年来的社会面貌。贾平凹说:“现代性的小说多写的是人性生命。现代小说有时可能并没有典型的人物,神奇的情节,或者有人物而没有姓名,按习惯看法不像小说,却更是小说独立为小说,与散文界限分明。”(26)
《河山传》的主人公罗山、洗河,具有非理性、传奇性的特征,不是那种严格的现实主义写法。罗山的死,呈现出命运的不确定性。如正在事业上升期的罗山,被一个跳楼的人砸死,脑袋裂为三瓣。贾平凹写道:“这个不想活了的骆晓婷从高楼的二十八层掉下来死了,却也砸死了活得正好的罗山。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27)洗河更是具有传奇色彩。一方面,洗河的成功是必然的,如他的商业头脑和不安于农村生活的叛逆性格;另一方面,他的成功又具有偶然性,如他来到西安,从众多名片中就留了罗山的,觉得他肯定是大老板,跟流浪汉说“我就要结识罗山”,还写了“到了西安,就找罗山”的标语,没想到还真让罗山给看见了,洗河从此改变了命运。洗河跟着罗山闯荡,他处事精明,手段和方法令人佩服。但在事业正顺之时,读者本以为他要闯出一片天地,成为像罗山那样的企业家时,他却被留在了花房子,从助理变成了一个管家、保安。当读者觉得他事业上没什么前途之时,他又在花房子找到了真爱梅青,有了家庭,生了女儿。更出乎意料的是,罗山死后,罗山的儿子罗洋留学归来,继承家业,罗洋娶了洗河的女儿鸽子,最终保安和保姆成了别墅的主人。
《河山传》的故事推进,也是无法按常情、逻辑理解的,有些情节颇有笔记体传奇的特色。贾平凹一直比较喜欢魏晋志怪、唐宋传奇,以及《聊斋志异》。长篇小说《秦岭记》,有种独特的离奇、魔幻色彩,深受笔记体小说影响,但篇幅却长得多,而传统的笔记体小说都是短章。其实,这种笔记体小说是暗通现代主义小说的,其间有很多相似或相通之处。这也是贾平凹“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28)的一种创造。贾平凹不仅热衷意象,甚至将情节处理成了意象,这种探索在《河山传》《怀念狼》里很明显。现代主义解构的写法,需要作家有很强的哲学思维能力,像卡夫卡、加缪基本都是思想家,当然包括鲁迅,尤其是他的《故事新编》。因为它已经不是再现,而是表现。美术里的素描是一种客观的再现,而杜尚的《小便池》就是观念艺术了,是一种打开,一种解构。这些其实更需要天赋和超越的思想能力。在这一点上,贾平凹是有欠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有思想能力的也确实不多。
《河山传》有点回到了《废都》,包括文字、写法,包括那种对时代的把握,都有点像,只是没了《废都》的大力量和那种泥沙俱下的感觉。毕竟写《废都》时,贾平凹还年轻。小说《太白山记》中,贾平凹是以实写虚,用实景的方式写出各种意象化的东西,他之后的小说似乎更加热衷于意象,如《秦岭记》《河山传》更具后现代性的特征。
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写道:“苦恼的是越是这样的思索,越是去试验,越是感到了自己的功力不济,四年里,原本可以很快写下去,常常就写不下去,泄气,发火,对着镜子恨自己,说:不写了……当我写完全书最后一个字时,我说天呀,我终于写完了,写得怎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总算写完了。”(29)可见,贾平凹深知这种探索的艰难和成功的不易。不管成败如何,贾平凹一直在写作,而且是手写,这种勤奋值得肯定。有时失败也是一种对写作的贡献。时代在前进,写作技法也必然跟着时代变化,新的思想内容用新的形式呈现也是一种必然。在这方面,贾平凹的不断探索也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司马迁:《史记》第1卷,第1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2)(3)(4)(5)(7)贾平凹:《后记》,《秦腔》,第539、539、539-540、540-541、5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贾平凹:《我是农民》,第22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
(8)贾平凹:《后记》,《河山传》,第2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9)朱俐俐:《论直觉——认识活动、审美知觉与情感本能》,《外国美学》2023年第38辑。
(10)〔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149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15)贾平凹、韩鲁华:《我就是想写这几十年如何混混沌沌走过来的——<河山传>访谈》,《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
(12)(13)(26)贾平凹:《五十大话》,第242-243、242-243、24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14)(24)(25)(27)贾平凹:《河山传》,第22、6、74、27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16)张胜友、雷达等:《<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17)贾平凹等:《<土门>与<土门>之外——关于贾平凹<土门>的对话》,《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
(18)费秉勋:《论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9)贾平凹:《对当前散文的看法》,《贾平凹散文大系》第2卷,第105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
(20)(29)贾平凹:《后记》,《古炉》,第607、6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1)(22)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
(23)贾平凹:《后记》,《秦腔》,第51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8)贾平凹:《后记》,《怀念狼》,第2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本文原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6期。
(作者:杨光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艳,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学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