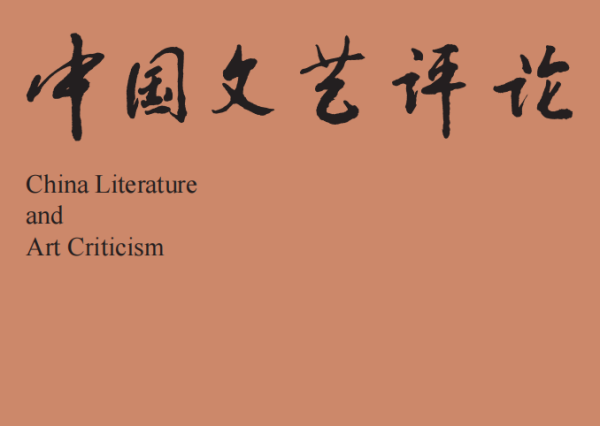

蒋祖慧简介:1934年10月生,湖南常德人,著名作家丁玲的女儿,新中国第一代芭蕾编导家,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国家一级编导、艺术指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49年在朝鲜平壤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学习。1950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任演员。1951年入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学习。1954年调入北京舞蹈学校五年级进修。1956年被选送到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学习。1961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中央歌舞剧院,现为中央芭蕾舞团)任编导,1984年至1994年兼任副团长。编导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巴黎圣母院》《祝福》;合作编导舞剧《红色娘子军》《纺织女工》《巴黎的曙光》《杨贵妃》《雁南飞》等。《祝福》第二幕在1980年文化部直属院团观摩评比演出中获创作一等奖;《流浪者之歌》获创作二等奖。1994年在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举办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展演中,《红色娘子军》获“经典作品”金像奖、《祝福》第二幕获“经典作品提名”奖。致力于新中国中外舞蹈交流:1966年和张策为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国家歌舞剧院排演《红色娘子军》,1987年为菲律宾芭蕾舞团排演《祝福》第二幕,多次赴欧洲、美洲、亚洲等国家进行访问演出。2014年荣获第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
一、“中国人就要搞中国的舞蹈”
张延杰:您早年在中央歌舞团、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和苏联的求学经历,为您后来的芭蕾编导和创作打下基础。您在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和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求学期间,有哪些事情给您的触动很大并留下深刻印象?您觉得对您后来的芭蕾编导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蒋祖慧:1949年春天,我去平壤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学舞,当时我还小,只会扭秧歌,不知道还有什么舞蹈。学的舞蹈有朝鲜舞、芭蕾舞、德国现代舞、俄罗斯舞。说实话,我当时年纪小,只是盲目地学了一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就回来了,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一边学习一边演出。
1950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院长接来了崔承喜及她的几个演员,并准备开办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办班前,崔承喜想先收集整理中国戏曲中的舞蹈动作,作为教材的主要部分。学校为她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其中有我、李正一、王世琦等六七个人,她叫我们向戏曲界的演员学习动作。她请了韩世昌、马祥麟、侯永奎等人。这些人来了她就问,青衣有什么动作?水袖什么姿态?步伐是什么?还有什么技巧?我们就跟着学,青衣的步伐、花旦的步伐,还有小生和武生,她把它们编成由浅入深的动作组合。
1951年崔承喜舞蹈研究班成立,我成为那里的学生。崔承喜跟我们讲,她是跟日本人学的舞蹈,有现代舞、芭蕾舞、日本舞。但她是朝鲜人,所以她就想搞朝鲜舞。她到农村去学习收集朝鲜舞,当时穷得把订婚戒指都卖了。后来她找了六七个学生编了舞蹈,之后就到德国、英国等国家去演出,一下就打响了。有人说,日本人征服了朝鲜,但没有征服朝鲜的舞蹈,没有征服崔承喜。所以她要求我们好好学习中国戏曲中的舞蹈和中国民间舞。整个舞研班的戏曲舞蹈课程,除了她整理的之外,还要学戏剧片段、戏曲的独舞。所谓的独舞就是起霸、挡马、剑舞,如《霸王别姬》里的剑舞。她请武术界的老师来教我们飞凤剑,请王瑶卿的侄子和王荣增教我们片段。当时她有一句口头禅“羊毛出在羊身上”,意思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创作中国的舞蹈,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1年蒋祖慧在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
崔承喜本人是演员,但她把朝鲜舞推出去是因为她的编导,所以影响到我们也要会编一点。有一堂课叫节奏课,就是跟着不同的节奏走一个大圈,走的时候必须要带动作,可以用戏曲里的动作。这样我们就对创作有了兴趣,但我当时没想过要当编导,想的还是当演员,只是不自觉地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
另外,除了中国舞之外,崔承喜还要我们学现代舞和芭蕾舞。她到印度和印尼去了一趟,创作了一套南方舞。实际上就是主要学习借鉴当地舞蹈中的手部动作,但还是以自己本土的舞蹈动作为主。还有一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在学到中国双剑舞中的动作时,朝鲜没有这种剑舞,朝鲜的剑是短的,没有长剑。崔承喜就拿它配朝鲜的音乐,加上朝鲜舞蹈的韵律,编了一个朝鲜的剑舞,叫她女儿来跳。她女儿在1951年因为这个剑舞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得了一等奖。所以我们觉得只有京剧的东西还不够,还要借鉴其他的。同时她要求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学习民间舞:会蒙古舞的教蒙古舞,会扭秧歌的教秧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2年蒋祖慧在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学习朝鲜的剑舞
当时有点小成果就是我回中央歌舞团,从民间舞蹈汇演中学了采茶舞。在我们学采茶舞的时候,我就想不能总是一个动作,总是用一只手采茶。崔承喜南方舞中手的动作很漂亮,能不能运用进去?所以我后来就想,用两只手采可不可以?我就加了崔承喜的手的动作,结果老师们很认可。当时没想过当编导,就觉得这么好的动作,不用进去就太单调了。这就是当时在崔承喜的舞研班学到的。还有一点,崔承喜很重视音乐。为什么有节奏课?这个节奏用什么动作?那个节奏用什么动作?她让我们学戏曲舞蹈的时候,就请来两个戏曲的乐师,一个叫刘吉典,是后来《红灯记》的作曲,他拉二胡,还请了一个吹箫的,让他们给舞蹈伴奏、写音乐。所以舞蹈创作必须要有音乐,她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后来到了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当时主要目的是学习编导,那时每天都有芭蕾课,还有性格舞课。二年级以后有双人舞课、宫廷舞课。因为编舞必须要有素材,不会动作怎么编?所以他们很重视掌握大量舞蹈素材。但是在苏联那些年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编导艺术之外,就是编舞要强调音乐的个性。当时在课堂上编导课老师拿唱片给我们听,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音乐想表现的是什么。我当时听不懂,因为我以前没学过交响乐,后来老师就单独辅导我。他拿了很多明信片摆在那儿,一边放音乐,一边问我这个音乐是不是像这张画?当时他先讲色调,是夏天的,还是冬天的?是晚上的,还是热烈的?是有火焰的,还是很安静的?我就这样慢慢爱上音乐了。当时我住的宿舍有一个特点,就是收音机从来不关,全天都在播放音乐,我整天就是在听音乐当中度过的。
除此之外,芭蕾课老师塔拉索夫要求我们用芭蕾的素材来编古典芭蕾舞剧中的独舞。比如,他让我用舞剧《睡美人》中的公主阿芙洛拉变奏的音乐编一段独舞。我就把自己会的芭蕾动作和技巧往里边放。我回课时,老师说:“你这是疯丫头,哪是公主?公主怎么会是这么张牙舞爪的?另外,公主和公主还不一样呢,《睡美人》的公主是躺着,她是被人呵护着的,醒来以后是一个天真乖巧的公主。《胡桃夹子》的公主是活泼的,是喜欢到处游玩的那种公主,但也不是农村的丫头,所以你要掌握人物形象,就要多听音乐,音乐里给了你形象。”因为我当时没看过《睡美人》,舞剧也没怎么看过,后来就去大剧院看别人编的舞剧,仔细观摩。
当然创作课讲编导艺术的主课老师启发我们编情节舞,这种实践非常多,每个学期都得编。还有一堂表导演课,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导演体系,总体给人很深的印象,因为表导演体系有指导思想,而且要从表导演体系出发最后用于分析剧本。怎么改成舞剧剧本,重点是案头工作怎么做。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苏联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很重视主题思想和最高任务。主题思想是什么?最后表演是为了什么?当时老师问我:“你的最高任务是什么?”我说:“我的最高任务就是学好编导。”老师说:“错了,你的最高任务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远大目标,所以你的作品要给人一种远大目标的感觉,给人一种启迪,给人一种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每个作品的最高任务。现在我们的编导可能不太强调这个,但苏联当时非常强调在分析作品时,为了达到远大目标,要思考怎样突出主要人物的贯穿行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整个斯坦尼体系的案头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搞作品和选题材的时候,我们创作组都从这个角度考虑,讨论主题怎么样,演出效果会怎么样。当然,也要考虑它的戏剧性和舞蹈性是怎样的,不能只有戏剧,没有舞蹈。文学作品都可以搞,但要思考从什么视角怎么取材。取得好,即使像《巴黎圣母院》这么复杂的剧,也可以搞成舞剧。
在我回国前,苏联老师帮我分析我当时想带回来的剧目:“古典的好的也不多。你想带的《泪泉》《罗密欧与朱丽叶》《西班牙女儿》等都还可以。但如果想要更有出息,可以搞中国的现实题材。”这几句话令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回国以后就先熟悉苏联的创作方法,排了《巴黎圣母院》之后,周总理说可以搞革命题材、搞中国的东西的时候,我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位老师塔拉索夫也跟我说:“你回去要搞中国的东西,我建议你要表现中国的,不要把中国舞动作当作装饰。舞蹈不是物理的结合,而是化学的结合。中国的元素要跟芭蕾融合在一起,不是拿两个动作点缀一下就完了。”

1956年蒋祖慧在留苏期间与同学一起演出合影
二、“生活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张延杰:您认为当时在创作《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包括您参与创作的这几幕,从您的角度看,哪些地方像您老师说的,是化学的结合,而不是物理的结合?您可否具体讲讲《红色娘子军》里面有哪些东西最能体现中国的芭蕾?
蒋祖慧:我认为我们正式公演的《红色娘子军》中所有的舞蹈,无论是哪一场的独舞、双人舞,还是几人舞、群舞等,都是芭蕾舞和中国民族舞化学地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找出哪段舞是纯古典芭蕾,哪段是纯民族舞。所以人人都说,《红色娘子军》是中国民族化的芭蕾舞剧。从《红》剧的创作过程看,没有赵沨院长的领导,《红》剧不可能这么成功。周总理当时看了两次《巴黎圣母院》,看第二遍的时候,他说:“你里头好像用了点中国的东西吧?”他说搞外国的还是要“洋到家”。当时我太天真了,我说外国好的舞剧也不太多,如果都排完了怎么办?他说:“我们可以搞我们自己革命题材的东西。”后来文化部很重视总理的意见。这里就涉及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当时林默涵副部长召集文艺界的一些人开会,包括吴晓邦、赵沨院长。当时我正带着《巴黎圣母院》在外演出,由李承祥、王希贤参加的讨论会,就是关于怎么落实总理的讲话精神,创作革命题材的剧目。林默涵副部长提出可以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舞蹈专家吴晓邦提出改编《红岩》。李承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可以排《红色娘子军》。赵沨院长非常好,他不迎合上级,而是尊重编导的意见,他认为《红色娘子军》好,故事家喻户晓,音乐主题歌好,以女性为主,符合芭蕾舞特点。赵沨院长是我们芭蕾舞团的奠基者,没有他,《红色娘子军》也不可能这么成功。
我们三个人一开始就分头做案头分析。赵院长说你们现在先别忙着搞剧本,先到海南岛下生活去。到了海南岛,部队一辆卡车带着我们从东线到中线转了一大圈,访问了娘子军的战士和连长。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一边了解生活、一边构思剧本,海南岛的风景和当地的生活都使我们有了切身体会。比如,我们进入一大片椰林,就想象到琼花逃跑,老四抓她,她从椰林中逃出来,比电影中在街上逃跑被抓要好一些。又如,我们当时还到了琼海,那里是娘子军诞生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广场叫列宁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土台子。当时有一个队员给我们讲解,说当年他们就是在广场上开会,大家喊口号,还有赤卫队员和儿童团员。广场旁边还有几棵树,叫木棉树,也叫英雄树,开红颜色的花,很有革命气氛,这样根据地的氛围就出来了。我们把红军娘子军成立、琼花参军这些段落都放在列宁广场。原来在电影里没有赤卫队员,我们加入了赤卫队员和儿童团员,还有群众、男红军。我们还去了五指山,学了黎族舞蹈,这也帮助我们丰富了舞蹈素材。他们那里有钱铃双刀舞,我们在表现赤卫队员的时候就借鉴了当地的钱铃双刀舞,改编成了五寸刀舞。
我们深入生活时,舞美设计马运洪、作曲吴祖强也跟我们一块去了。我们一起收集素材、一起体验生活,很多音乐的创作也受到了当地生活的启发,使我们的思想很统一。当时赵沨院长强调集体合作,五个作曲不分你我,都写主题,哪个好就用哪个。他对我们三个编导说:“你们先编出来,我来看一看,不能搞成公主、王子,要搞成粗丫头、战士。一人编一段看看。”我们当时分工:我负责序篇、第一幕、第二幕,王希贤负责第三幕和第五幕,李承祥负责第四幕和第六幕,每人编一段。我编琼花逃跑,粗丫头的形象,不能像公主;李承祥编快乐女战士,战士的形象;王希贤就编黎族少女舞,属于性格舞。赵沨院长看完说:“很好,可以继续排下去。”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对琼花的刻骨仇恨有了切身体会。因为在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姓黄的战士讲她当时为什么参军,就是实在受不了地主的打骂,就偷偷逃跑。她被抓回来以后,地主用烧开的粥泼在她身上,她被烫坏了,然后让她顶着一个盆子跪在太阳底下。我当时听她说的这些,就觉得没法忍受。海南岛的蚊子特别多,她顶着烈日,被咬得浑身难受。所以她就恨死了,就是咬牙切齿的仇恨。粗丫头是干活的,不像喜儿是乖乖女,海南岛都是女的干重活,男的干轻活;在部队里女的扛机枪,男的背步枪;女的下地,男的抱孩子。粗丫头应该是很强悍的,我就想到用芭蕾当中比较强烈的动作如大跳的大舞姿等来表现。我过去学过的戏曲中的东西也都用上了,把它们结合起来。
当时跟吴祖强合作,他写音乐,当时的主题他用了琼剧的音乐元素。我说琼花跑出来是带着仇恨的,要在舞蹈当中把仇恨发泄出来。剧的一开始琼花跑的过程中有一段音乐是特别强烈的,把琼花的个性全部体现出来。当时赵沨院长一看,“通过!没问题,挺好!”我们三段舞蹈他都通过了。当时编完全剧之后钢琴联排,我们都很高兴,但赵沨院长很冷静。他说:“咱们自己高兴不行,要请人来给我们提意见。”他请了话剧界的吴雪,请了音乐界的、舞蹈界的,还请了军队的干部和战士。他提出:“让你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鼻子是竖着长的,你挑成横的了,我们都高兴,不怕你们说错,就怕你们不敢提意见。”这次提意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提出:“像娘子不像军。”战士们认为,很好看,但不像军……
话剧导演吴雪说:“你的序像话剧的哑剧,我们的话剧哑剧也可以这样表演,你的舞蹈特点没出来。”当时是我编的序幕,我太同情那些在水牢里受苦难的人,琼花在柱子上绑着,有一个人在水牢里面死了,两个人把他抬下去,大家哭哭啼啼,但那个场面不是舞蹈。这个意见一下子启发了我,于是后来就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琼花是从水牢里逃出来的,既有舞蹈,又交代清楚了情节。
第二场娘子军那段舞蹈也是我编的一段群舞。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像娘子不像军”,团里决定休整20天让演员去部队。演员们在部队深入生活,临回来的时候跟战士联欢,还编了点小舞蹈,回来向我们汇报,我们很受启发。李承祥也很感兴趣,对我说:“这段舞我有想法了,我帮助修改吧。”我同意了,果然他改得非常成功,要表现部队的生活,演员的脚尖立起来要看齐,还有刺杀训练,等等。这段舞从生活当中来,体现了部队生活,舞蹈也很好看,成为这场的一个亮点。如果没有赵沨院长横挑鼻子竖挑眼,就不会出现第二场这么好的舞段。所以我想说,领导的胸怀很重要。他站得比较高,但同时也很民主,尊重艺术,尊重编导的意见。

1964年蒋祖慧排练《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从左至右为薛菁华、白淑湘、蒋祖慧、刘庆棠、赵汝蘅
三、“创作就是从人物出发,揭示人物的典型环境”
张延杰:舞蹈理论界把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祝福》称为“心理芭蕾”,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祝福》这个作品已将近40年了,在整个中国芭蕾的发展阶段,除了《红色娘子军》之外,您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位?对现在产生了哪些影响?
蒋祖慧:从《祝福》的创作角度来讲,我延续的还是原来的创作方法,先讲它的主题、最高任务,再找到它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它的环境背景是旧社会妇女受到礼教的压迫,不能改嫁,祥林嫂就是这个命运的典型人物。鲁迅先生说过:没有哪个年轻的妇女,丈夫死了不愿意再嫁的。但是祥林嫂不能再嫁,大家还说她是丧夫星,给她心里很多压力。这种旧社会的东西,怎样把它搬上舞台,让观众看到原来旧社会的封建礼教是杀人的,是我首先思考的。
另外我还想到最高任务是反封建,一定要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在分析祥林嫂的时候,我从人物形象考虑《祝福》的主角当然跟《红色娘子军》是不一样的。琼花是一个粗丫头,性格是外露的,而祥林嫂是压抑自己的。她告诉自己“我不能再嫁,我不能再嫁”,但生活中她又需要温暖、需要爱情、需要孩子。他们说这是一部心理剧,但我不是按照心理剧写的。在理论界看来,好像心理剧要比现实主义的剧高一截,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祥林嫂受封建礼教压迫,存在很多心理矛盾。她到底应不应该嫁给贺老六?这就有矛盾了,这个矛盾就是自我斗争。她的心理活动不是说“我要报仇”,而是说“我不能嫁”。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表现的是怎样让祥林嫂转变心意嫁给他,而且后来生活得很好,这是一种解放。贺老六在山区,受的封建礼教束缚比较少,他是一个憨厚的人。我想表现出贺老六的憨厚:“我那么穷,用钱把你买来了,而且对你还很好。你撞桌子都不愿意嫁给我,我也能够理解,实在不行就算了,你走吧。”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善良的一个人,祥林嫂能不感动吗?贺老六允许她走,她到了门口,想走出去,但往哪去?她根本没地方去。回头看贺老六也非常痛苦,人财两空。这就感染了祥林嫂,让她下决心:“算了,我跟你一块吧。”我觉得这是两颗善良的心、两个善良的人在一起了。
当时有评论家说:“你把鲁迅作品暗写的东西给写出来了。”我主要想体现他的思想,就是表现怎样使祥林嫂改变观念。我到绍兴去,看到贞节牌坊,让我的心情很压抑,我想一定要把她们的苦难表现出来。当时分析鲁迅先生作品的人说,祥林嫂后来不是饿死的,是精神压力太大了,丈夫死了以后,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富人家的礼教思想比穷人家严格得多,在那里又重新受到礼教的压迫。这让我太同情她们了,所以我就想把它创作出来。
张延杰:所以您还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出发去进行创作的。
蒋祖慧:是的,还是从人物出发,要揭示当时这个人物所在的典型环境,在旧社会鲁四老爷家、富人家,他们怎样用这种惯术欺负老百姓、欺负妇女,让妇女甘心当奴隶。妇女想要解放,又受到精神上的压迫,就这样一个主题。我还是按照苏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来表现的,但是创作也蛮困难的。我还去采访了演祥林嫂的越剧演员袁雪芬,我问她祥林嫂为什么后来嫁给贺老六?她说:“贺老六太善良了,他给了祥林嫂一杯水。”我后来也借用了这个细节:祥林嫂撞桌子之后晕过去,贺老六看她的手耷拉着,就轻轻把她的手盖好。她醒了以后,想要喝贺老六给她熬的药,但又觉得不能嫁给他,就把药打翻了。这个时候要表现贺老六的善良,他不是粗暴的态度,而是把药碗捡起来,很伤心:“我的一片好心被你打碎了。”祥林嫂看到贺老六表现出的那种痛苦,自己也很难受,想安慰他又觉得不行,这种穷人的困境,就体现出来了。
张延杰:您认为《祝福》从文学作品到舞台呈现,对后来的中国芭蕾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价值?
蒋祖慧:不同的题材也可以用芭蕾来创作。《祝福》我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比如第二幕婚礼那一场有一段群舞,我就有意识地把原来学过的民间舞素材花鼓灯搁进去。芭蕾舞剧一般都是古典芭蕾的素材,但也要有性格舞,把作品的环境和气氛呈现出来。这段群舞我把中国民间舞的素材搁进去以后,加上双人舞,《祝福》第二幕就比较成功。去国外演出最多的就是第二幕,当时去美国演出了两次,还去过苏联、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当时有个中国人在美国白宫工作,她说她看了祥林嫂,感到心里在哭,“旧社会的妇女原来这么苦”。
张延杰:刚才您提到《祝福》第二幕把花鼓灯等民间舞元素放进去,也延续了之前我们说的,从您创作《红色娘子军》开始,就受到从苏联和崔承喜舞研班的学习经历的启发,要有民族意识。您一直都是这样保持着,并且融入到您的作品创作当中。
蒋祖慧:我感觉自己年轻时中国舞的底子打得比较好,对民族化起到一些作用。现在的编导创作芭蕾舞,最好还是要多学点中国民间舞。

1980年蒋祖慧指导演员排练《祝福》,演员为王才军、王萍萍
四、“只有自己的东西创作得好,国际上才能承认”
张延杰:您认为国际视野和本土道路这两者之间如何联系起来?中国芭蕾的发展如何做到既具有国际视野,又走本土道路?
蒋祖慧:每个人对国际视野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把音乐剧的东西拿过来搁在舞台上,就有国际视野,他们这么跳,我们也这么跳。错!这不是国际视野。我认为国际视野,一方面是要借鉴国外新的创作手法,当然新的语汇也要多一点,芭蕾的语汇永远都是不够的,还要继续丰富。尤其现代人,可以从生活中提炼和借鉴,从崔承喜那时开始就提倡要借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立足本土,要创作自己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东西创作得好,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承认。
张延杰:现在业内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芭蕾学派”。您怎么看“中国芭蕾学派”?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中国芭蕾学派”?芭蕾以前有丹麦学派、俄罗斯学派、意大利学派。当然这些学派更强调的是训练方法和教学体系,但还是要有代表作品,形成统一的风格。近年来中国题材的作品如《沂蒙》《敦煌》是不是也可以被看作“中国芭蕾学派”的代表作品?
蒋祖慧: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创作一个西班牙舞剧,用了西班牙的舞蹈动作跟芭蕾结合,可不可以叫“西班牙学派”?还有俄罗斯也创作过《一千零一夜》,动作和音乐用到了阿拉伯元素,是不是就叫“阿拉伯学派”?苏联创作过《巴黎火焰》,是法国题材,运用了法国的民间舞,你不能说这是“法国学派”吧?我认为自己创作了《西班牙女儿》以后,再做中国题材的就更知道应该怎样吸取中国的东西,因为我做《西班牙女儿》时,就吸收了西班牙的东西。苏维埃时期对民间舞更加重视,特别是莫伊塞耶夫民间歌舞团,挖掘了很多民间的东西。要丰富芭蕾舞的语汇,做什么国家的东西就把什么国家的民间舞用进来。在基训方法上,其实国外也在互相借鉴,比如苏联原来没有压腿,他们的身体都挺硬的,现在有压腿了,就是跟中国学的。在训练方法上要互相借鉴,丹麦主要是腿部打击动作特别多,因为民间舞就是打击动作,也是属于跟民间舞结合,丹麦的民间舞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的训练当中这个特点比较明显。
张延杰:我们在芭蕾舞剧里融进了中国民间舞或者传统戏曲的元素,比如《红色娘子军》和《祝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取材,自己就在这个土壤里面。但从您的角度来说,不能因此说这就是中国学派了。
蒋祖慧:我们现在的创作方法实际上还是苏联学派,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要体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有一点我刚刚忘了说,就是音乐。在苏联有一句话,舞剧就是用音乐写出来、用舞蹈体现的戏剧。舞剧首先是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要写成音乐,怎么写成音乐?编导把这个剧本的大纲弄好以后,就是那种细致的剧本,要弄一个表,叫音乐长度表。比如第一部分我写的故事情节,一开始是琼花逃跑,然后老四来抓她,每一段情节要有表现形式,是用舞蹈还是用场面,是否有独舞,需要写上我对音乐的要求。这个剧本包含的一个是剧情的第一、二、三部分的情节;另一个是表现形式,我想用场面还是独舞、双人舞、群舞,最后是我对音乐的要求。
比如“琼花逃跑”这个音乐要有琼花的主题,是粗丫头的主题,是带着很强烈的仇恨和决心的逃跑。我要求分三段,比如前头是逃跑,要急切,观察环境;已经逃出来了,要表现自己将来一定要回来报仇,这里要有一段抒情;最后发现有人来了再继续逃跑。要通过音乐表达出每一段的情绪是怎样的。如果你音乐修养高,还可以说我想参考什么。比如《红色娘子军》那段舞蹈,我希望用电影的音乐主题曲进行发展,怎么发展?我要求一开始是音乐主题,后来怎么变化,又怎么发展,提的要求越仔细,作曲就能根据你的要求写得越明确。但有时候作曲比你还要高明,在音乐上比你还了解,所以他写出来的效果可能比你构思的还要好。比如我给吴祖强写的第一段是跑,第二段是双人舞,老四来抓她,要有一个小过场是安静的,她以为没人了,刚出来,碰到了老四,有一段双人舞,我当时提了这些要求。后来他写出来,跟我的要求稍微不一样,他把琼花的主题也搁进来,我一听比我想得还好,很连贯,跟前面的变成一个总体了,而且戏剧性很强。他让我先听钢琴曲,我说太好了,比我想象得还好。这段音乐去阿尔巴尼亚排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的钢琴伴奏都说,音乐表现的戏剧性真好。这些也是我们在苏联学习时打下的烙印。
张延杰:您觉得中国当下的芭蕾创作,如果我们就在这个舞团里面,像您当年这样一个合作机制,那芭蕾编导应具备怎样的能力或者素养?
蒋祖慧:我们原来团里有一个创作组,也可以叫艺委会,包括编导、作曲、舞美设计,后来又增加了编剧。实际上,我认为编导应该自己编剧比较好,他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有舞蹈。有些纯搞文学的不知道什么地方该有舞蹈,什么地方该有戏剧场面。这个艺委会的组织非常重要,正好当时我们三个编导都在苏联学习过,王希贤是我的同班同学,李承祥是在中国跟古雪夫学的,舞美设计马运洪也是从苏联回来的,我们很多观点非常接近。当时排任何一个剧的时候,大家要一起讨论这个剧的主题思想怎么样,最高任务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舞蹈要怎样体现,讨论之后确定下来,大家再开始创作。每排一个舞剧都需要动员很多力量,所以决定排什么戏要大家讨论通过。
现在编导系培养编导,不仅要懂技法,尤其是双人舞技法,还要有创作思想。我认为,还是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掌握戏剧。戏剧是一切之本,你要懂戏、要会分析剧,找出剧的主要矛盾、戏的贯穿行动、戏的主题思想、戏的风格、戏的最高任务。你不仅要懂戏,还要懂音乐,同时要懂得芭蕾编导的规律。另外,还要做各种练习。刚才谈到音乐,现在很多编舞是舞蹈编完了再找一个音乐来配,这就错了!音乐表现哭你就哭,音乐表现笑你就笑。你拿来一个音乐,动作还不合音乐,音乐是舒缓的,但你的动作是一惊一乍的,或者音乐是快乐的,你却在那里慢慢走,这是不行的。我觉得编导搞创作,首先要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好,我们得了解生活,从生活当中找题材,创作的时候要想到剧本结构、想到音乐,要掌握大量的素材。如果到国际上,就要跟国际接轨,人家国外的编导都是懂音乐的,你不懂音乐,人家会说,这舞蹈怎么不合音乐呢?
另外,题材出新,舞蹈才能出新。我要表现工人,舞蹈动作肯定不能是秧歌,要选择机器的声音、工厂的声音。让我表现车间,但是没有机器怎么办?我就要想到工人劳动的场面是怎么样的。我认为现在要创新,得根据人物需要来。创新得有基础,什么基础给我什么启发,有根才有新,站在人家的肩膀上才能创新,而不是空中楼阁的创新。我认为不能刻意求新,你要想求新,就得找一个新的题材。
访后跋语
2023年3月16日,经由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刘晓勉老师的引介,我终于见到新中国第一代芭蕾编导家蒋祖慧老师。此前我对蒋老师的艺术成就虽有了解,但依然停留在文献资料上遥远而单薄的印象。当历经时代风云激荡的蒋祖慧老师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我不禁感叹,眼前的蒋老师如此亲切温暖、淡然从容。她虽然身形瘦小,嗓音有些沙哑,但步履轻快、目光如炬、思维敏捷。从延安保育院到朝鲜崔承喜舞蹈研究所、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再到中央芭蕾舞团,作为新中国芭蕾艺术的奠基人之一,蒋老师的思考和观照视野从未局限在舞蹈艺术领域。她的成长经历和艺术生涯彰显着那一代艺术家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国家命运、社会变迁和生动的现实生活始终是蒋老师的关注重点和艺术创作的重要起点。蒋老师充满先锋性的当代价值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谈及女性题材作品创作时,蒋老师坚定地说:“女性一定要有独立思考。”蒋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不已。无论是访谈问题,还是文字稿中涉及的人名、作品名称以及专业术语,蒋老师都反复认真修改和确认。访谈结束时,我瞥见蒋老师在客厅里安装的芭蕾把杆,不由得在心底对这位终身追求芭蕾艺术的老人升起更深的感佩和敬意。祝福蒋祖慧老师艺术常青,期待蒋老师为中国舞蹈艺术发展提出更多宝贵建议。
采访人:张延杰 单位:《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编辑部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7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王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