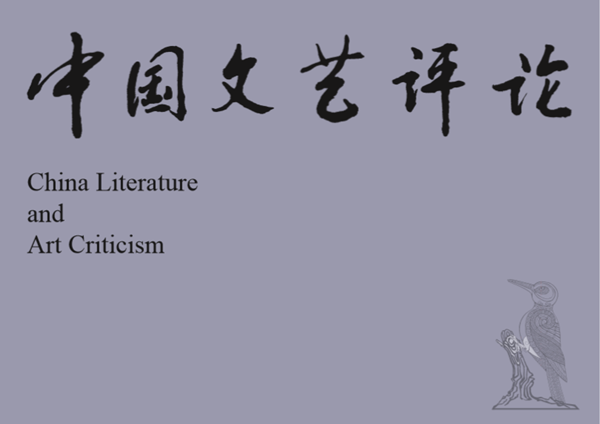
内容摘要:针对我国电影市场的新现象、新要素、新症候,电影理论界、批评界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但存在诸多认知误区。首先,“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三分法”并未过时,它们只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入和深化。其次,影片、院线产能的中长周期性触顶和回调,档期、观众的增长乏力和不稳定性,已是中国当代电影下一个历史周期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电影工业美学”在应用上的尴尬局面,反映出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不匹配。在这个意义上,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大浪淘沙之后,中国当代电影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亟待再出发。
关 键 词:新主流 主旋律 电影批评 电影理论 电影工业美学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我国内地电影票房突破百亿门槛,并在不到十年间就站在了600亿的上方——不仅我国内地的影片产能、院线产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放量式增长,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新的电影观众,以及视频网站、直播网站等新的观影渠道、新的宣发渠道等也在快速增长,对于内地电影市场而言,全新的行业现象、要素、症候,正在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央。这些具有鲜明时代区隔性的种种症候,在显著改变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精神气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电影理论与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究竟如何阐释中国当代电影在过去十年里所卷积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历史周期性变迁。
对此,我国的电影理论界、批评界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例如“新主流电影”“小镇青年”“新主流大片”“电影工业美学”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过去十年来我国电影市场此起彼伏的新现象、新要素、新症候的基本回应。但由于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生产体制未与社会现实很好地同步,与相关领域的生产实践的结合程度不够紧密,知识体系、分析框架相对陈旧且更新缓慢等,我国电影理论界、批评界在阐释中国当代电影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其中,“新主流电影”“小镇青年”“新主流大片”“电影工业美学”等概念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尽管这一系列话语近年来在理论界和批评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仍存在论点、论据、论证等诸多学理层面的基本问题,在阐释中国当代电影的相关问题时,甚至处于理论、批评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无效状态。
因此,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梳理、反思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等话语中所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对于厘清、辨识当下中国电影所携带的复杂文化经验、文化症候,更好地总结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进而有效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方向,都具有着普遍性的行业示范价值和长期性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科学评估“三分法”的理论解释力
“新主流电影”概念的提出,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1999年马宁在其《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随后2000年,尹鸿在其《1999中国电影备忘》、马宁在其《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中都明确提及这一概念,并予以进一步的拓展。
尽管马宁等学者宣称“新主流电影理论并不是那种体系严密的理论,它实际只是一群年轻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的而发出的良好愿望。它的提出不是为了发动中国电影的一种风格革命或者是某种意义的国际化运动”。但他还是给出了其明确的边界——“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的电影、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主旋律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以电影节为转移的影片、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种合适的演变途径。”[1]马宁在相关文章的论述中指出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也就是尹鸿等学者所论述的“长期以来,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片的‘三分法’,是对中国电影创作路线的常态分析框架”[2]。“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3]
从马宁到尹鸿,从1999年到2019年,相关学者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逻辑预设前提:不管是“新主流电影”,还是“新主流大片”“新主流”,都是超脱出“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三分法”之外的电影理论新概念。如果说在马宁等学者所处的世纪之交,这还只是一个不具有严谨学术性的“良好愿望”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实践,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更充足的论据来支撑起这样的判断——“尤其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无问西东》等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作品,使得主旋律、商业、艺术这三者人为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了。”[4]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
因此,若要从理论上彻底剖析相关概念,我们就必须要直面马宁、尹鸿等学者共同指出的,包含“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三分法”是否过时这一基本问题,这也是直击相关话语痼疾的一个核心着力点。
非常遗憾的是,在触及影响“新主流电影”的“规范和定型”的“主旋律”概念时,“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首先就存在考据等学理性的基本问题。尹鸿等学者在论述“主旋律”概念时,明确将“主旋律”的起源定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旋律’概念是上世纪 90 年代被正式作为一种创作口号提出来的。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在电影领域得到贯彻。……‘题材+主题’的先行要求,构成了‘主旋律’电影鲜明的政治教育功能,从而使‘主旋律电影’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宣传烙印。……这些影片在二十多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呈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和思想特征。”[5]
然而历史的实际状况是,“主旋律”并不是直到1996年才被提出,在初始阶段也并不是“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产物,而是作为正面应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和改革开放以来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现实挑战的,一系列文化政策的主要构成而登上历史舞台的。[6]早在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腾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一“主旋律”的基本理念。其后国家又完善了一系列制度性配套,如同年7月成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1988年1月设立了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等等。[7]由此可见,“主旋律”正式登上我国电影、电视领域的历史舞台已然超过了30年。
不难发现,“主旋律”概念的出现,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前苏联解体前后,内置于“后冷战”年代的全球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精神文明建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乐章。[8]所以,对于“主旋律”的这种考据性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远不止局限在技术层面,其最大问题是直接影响了对“主旋律”问题背后的“三分法”的整体性基本判断——“主旋律”绝不是想象中僵化的、本质化的概念,在其既有的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的“主旋律”影视剧也呈现出了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并且迄今仍在不断向前发展推进。
在经历“主旋律”影视剧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在1987年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1989年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1991年的《大决战》系列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影片之后,到了1996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阶段;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等外部挑战的解决,“主旋律”影视剧保守的历史讲述方式——官方参与拍摄、制作、发行、传播等,就已经开始逐渐淡化和消退[9]。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精神文明建设”阶段,实则已经是“主旋律”影视剧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主旋律”影视剧在拍摄、制作、发行、传播等诸多领域,都在初步尝试、摸索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路径,涌现出了一系列“长征”题材的影视剧及《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些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影片[10]。倡导“新主流电影”的相关学者也将这些影片作为例证,其错觉和错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对“主旋律”的错误认知。

也就是说,尹鸿等学者认定的“主旋律”影视剧所具有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和思想特征”,并不是僵化的、本质化的概念,然而在几乎所有既往的当代电影理论、批评中,都相当程度地忽视了对“主旋律”影视剧的内在演化逻辑的分析和梳理。因为在包括《集结号》《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主旋律”影视剧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主旋律”不仅已经找到了远比前两个阶段更加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好莱坞大片的商业类型元素,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好莱坞大片的中国本土化的类型嫁接。最终,从《湄公河大案》《湄公河行动》开始,以《建军大业》《战狼Ⅱ》为代表,包括《人民的名义》《非凡任务》《空天猎》《红海行动》等在内的“主旋律”影视剧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主旋律”基本完成了市场化、产业化的有效转型。[11]
显然,“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三分法”及其背后的电影理论、批评的基础概念、范式远未过时,它们只是在其各自路径的中国实践当中不断深入和深化。无论是早先的“新主流电影”,还是近来的“新主流大片”,都没能超脱出以“三分法”为代表的既有电影理论、批评的基础概念、范式的原因,除了对“主旋律”影视剧缺乏有效认知和辨析之外,更在于没能正面、有效地回应诸如商业类型电影所包含的“小镇青年”、院线和档期,以及艺术电影所指涉的中国电影人才培养机制等,中国电影实践在这一发展周期所独有的鲜明结构性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二、“收缩型城市”带来票房增量触顶
无论是尹鸿等学者认定的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还是陈旭光等学者认定的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中国当代电影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等话语演变的关键节点,正是来自于票房。关于“新主流”的相关讨论,也从马宁等学者定义的“新主流电影”,翻转为今天似乎默认为常识的“新主流大片”。同样,无论是尹鸿等学者所认为的“一系列被认为体现了‘新主流电影’特征的‘标杆’影片。这些影片票房都在 5 亿以上,……证明了它们都是真正的市场上的主流电影”[12];还是陈旭光所分析的“人口‘红利’和影院银幕等刚性增长”[13],他们都在共享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预设前提,那就是已经取得的票房佳绩和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票房空间预期,是支撑他们各自理论、批评等话语的合法性来源。

从2010年到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持续攀升的高增长周期中看,这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依据,只不过一旦票房增速放缓,就会迅速暴露、放大其背后的结构性痼疾。因为即便是马宁等学者在1999年提出的“良好愿望”,也依然承认“商业电影的总的票房取决于它们对影院空间和档期的控制能力。……它们的模式和类型相对比较固定,生产方式也较为严密”。[14]——其中所论及的“对影院空间和档期的控制能力”,也成为了我们梳理“新主流电影”的两个重要抓手。
上世纪末,我国电影在进口大片的持续冲击下,开始初步找到自身节奏的标志,就是以《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冯氏喜剧为代表的贺岁片模式。广义上由当年11月持续到次年2月的贺岁档,也是我国电影领域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后的第一个稳定档期。这也是“新主流电影”在1999年浮出历史地表的基本背景。
随着我国的商业地产从2008年开始爆炸性增长,每年商业地产的新开工面积迅速拉升到了以数亿平方米作为计量单位的周期,我国的电影票房也随之突破了百亿门槛,不同规模的电影院线也开始遍布全国,并不断在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落地、渗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过往春节期间周而复始的“大鱼大肉”式的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开始逐渐向轻松的休闲文化娱乐消费转移。于是从2013年开始,过年看电影开始成为全国范围的“新民俗”。当年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总票房斩获了12.45亿,正式拉开了春节档的序幕。春节档的全年票房占比,也从2012年的2.4%[15]增长到2018年的9.7%[16]。春节档在全年档期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史上最强春节档”这一表述从那时起不断高亢,并一直延续到当下,取代了其所脱胎的贺岁档。

但是,在2019年春节档,八部影片在七天时间里看似产生了58.3亿的大额票房,实则只是勉强持平于上年同期的57.7亿票房,相较于2018年春节档67%的涨幅,2019年春节档的涨幅只有1%左右。[17]在票补大幅减少、票价大幅提高的背景下,2019年的春节档非常尴尬地维持住了2012年以来春节档年年都是“史上最强”的票房纪录,远未达到70亿的票房预期。
无疑,作为全年的风向标,春节档的“横盘”也为我们剖析中国电影的档期结构,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所无法触及的深层次问题等,提供了有效的切口。2019年春节档的“横盘”并不是偶然,而是我国档期结构危机的必然结果,因为春节档的火爆首先直接造成了极强的档期“虹吸效应”。在集聚了全年优质影片资源和全年半数以上票补的同时,不仅其原本所依托的贺岁档受到了严重的挤压,而且由于一轮又一轮“史上最强春节档”的提前透支,从2012年开始,每年的春节档之后、暑期档之前,也就是当年的3月到6月,包括清明档、五一档、端午档在内的票房表现都呈现出了规律性的低迷。2016年清明档《叶问3》“买票房”的金融欺诈丑闻,正是这一结构性痼疾的具体体现,一旦缺乏票房支撑,我国电影就立即被“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游戏所裹挟。这也是《战狼Ⅱ》《我不是药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被认定重新“抓取”了“小镇青年”的2017年暑期档的《战狼Ⅱ》、2018年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出现之前,连暑期档也没有太多票房上的存在感。可见,重新反思直接关联着档期和院线的“小镇青年”问题,也就是重新科学地正视中国电影的增量问题,在当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2010年到2016年,在国内电影票房高潮迭起的那七年里,由于增长速度过于迅猛,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行业预期,于是寻找推动国内电影票房不断攀升的幕后增量,就成为了全行业关注的焦点。很快,2013年、2014年前后,“小镇青年”这个概念,被一步步推到时代的聚光灯下,被认定是内地电影票房的真正增量。只不过随着2016年《叶问3》金融欺诈丑闻的曝光,行业阴暗面被持续披露,加之近年来国产电影品质的不稳定起伏,票房高潮的消退也使得社会各界对“小镇青年”的关注迅速降温,近两三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都几乎没有再真正有效触及中国电影的增量问题。
2019年前四个月的观影人次为5.9亿次,同比2018年减少了超过8000万人次,降幅超过了11%。[18]无独有偶,2018年全国观影人次为17.17亿,同比增长5.86%,较2017年18.22%的同比增速明显下滑。2018年全国总计拥有银幕60079块,新增银幕数总计为9303块,新增数量较2017年则同比下降3%。而且,单块银幕产出继续下滑,2018年单块银幕产出为94.14万(扣除服务费),同比下降8.72%[19]——与观影人次和院线的增量持续疲软相较而言,2019年前四个月我国内地票房共计233亿,同比去年同期的241亿出现的3.3%的降幅[20],甚至显得有些无关痛痒。[21]

诚然作为基础设施的影院建设,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使电影的供给渠道已经基本“下沉”到主要县级城市。但在这背后的真正问题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增速已经进入到阶段性的平台周期,再加上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加码,县级市商业地产的高速发展时代已经结束。2019年3月31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2]中,更是第一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无论是放置在改革开放40年,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视野下审视,“收缩型城市”概念的提出,都具有足够的长周期转折意义。电影也不会例外,“小镇青年”,也就是中国电影的有效增量,恐再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由于2010年到2016年的过快增长的提前透支,近年来资本市场对于我国电影市场的估值已整体性大幅下调,影院建设所必需的资本投放额度也在被逐步收紧——即使我们在未来可以不计成本地继续投资建造新的影院,无论新建影院是否能盈利,在城镇化所带来的观众增量不再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来自院线的增量已不会再对票房总量起到上一轮增长周期曾有过的放量式拉动作用。[23]票房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影院银幕等刚性增长”在突破60000块[24]的天量之后也已是强弩之末——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萎靡等大时代背景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很难再有从2010年到2016年那样的强劲外部动力。更何况,国家层面提出的“收缩型城市”概念所指涉的未来中国城市格局的基本面,已经为那些从2010年到2016年在票房高潮阶段曾有过的天真畅想画上了实质性的句号。直接关联着档期和院线的增量空间,正在触及到中长周期的天花板,并呈现出了清晰的下行趋势。
不难发现,从“新主流电影”到“新主流大片”,其实际表现,距离马宁等学者在1999年所论及的“对影院空间和档期的控制能力”,既有着漫长的摸索之路,也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
三、尴尬的“电影工业美学”
“新主流大片”丝毫不“新”——近年来被引以为傲的“新主流大片”,并未开拓出独立的档期,也并未有可持续的票房表现,这是中国当代电影实践的一个基本事实。例如继《战狼Ⅱ》之后,被“电影工业美学”予以反复褒奖的《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其所依托的依然是年年“史上最强”的春节档——《捉妖记》和“西游”题材的相关IP,这些已经被饱受诟病的国产特效大片在春节档同样可以表现不俗。而在2018年夏天大放异彩的《我不是药神》,尽管也被所谓的“新主流大片”概念所征用,实际上却并不符合“新主流大片”的投资规模门槛,在“电影工业美学”上也没有过多的阐释空间。同样的例证还有2019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陈旭光在分析《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提出了“从工业美学的角度看,‘电影工业美学’形态可以按投资规模、制作宣发成本、受众定位等的不同区分为‘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轻度工业美学’”的“电影工业美学”分析框架。[25]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作为‘重工业美学’的《流浪地球》有巨大的投资、超强的匹配、完整的工业流程,打造了宏大的场面,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其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代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国家文化现象建构的努力。它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界呼唤和期待已久的体现电影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高峰,也为‘电影工业美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案例。”[26]在分析《疯狂的外星人》,他认为“宁浩清醒自觉的‘中度工业美学原则’意识,使他自觉地不是在画面造型、场面规模、视听效果等方面求胜,而是尽量接上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地气’,并在故事叙述、剧作打磨、现实思考与人性考量等方面下功夫,这也使得《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号称科幻、改编自刘慈欣的电影显得颇为‘土气’,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装扮、造型、场面设计等。”[27]
然而,中国当代电影实践的真相却是:“虽然(《疯狂的外星人》)故事上是反好莱坞的,但在特效制作上……整部电影制作投资达到四亿多,其中特效成本占比达到50-60%。宁浩说,影片实现的特效是难度最高的A类特效——生物表演类特效,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顶尖的,只能请国外的团队进行制作,包括《少年派》的团队、《侏罗纪公园》的团队都参与了。”[28]《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在一则采访中也明确提及:“向维塔数码的人透露了《流浪地球》预算,对方脸色突变,一头雾水,‘……他们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有底气过来聊,这明显和他们平常接活的数字差太远了,这个数不止外界传的5000万美金那么少,但也确实不高。’……就在这个时候,一旁宁浩赶紧挺直了腰板说‘我们预算够’,留住了维塔数码的人继续聊。这里插一嘴,宁浩之所以这么坚持,必须敲下与维塔数码的合作,是因为他挑战了外星人数字生物角色这块‘硬骨头’,这是视效中最高级别的难度。而《流浪地球》则是在编剧本的阶段,就考虑到预算的关系,把涉及最难最贵的特效部分完全去掉了。”[29]
显然,对于“电影工业美学”而言最为关键的视觉特效场景,《流浪地球》不仅在文化工业的技术含量上远远不能和《疯狂的外星人》相比拟,如若没有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团队挑战生物表演类特效的巨额投入背书,《流浪地球》甚至没有机会得到来自好莱坞文化工业体系中最为上游的新西兰维塔数码的技术介入——如若连构成支撑所谓“重工业美学”论证的最重要论据,和与生物表演类特效相比成本较低廉的太空场景都没有了的话,“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相关讨论则直接无从谈起。何况,《流浪地球》除了在投资规模上明显低于《疯狂的外星人》,在IP授权、拍摄制作等方方面面的具体环节上,都受惠于宁浩《疯狂的外星人》团队。由此可见,“电影工业美学”稍加应用就暴露出如此尴尬的局面,这深刻地折射出中国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现实的脱节或不匹配。

至于受众定位,尽管在文本内部,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的差异,陈旭光指出:“从电影形态、类型上说,《流浪地球》是一种美式科幻大片。在我看来,《疯狂的外星人》才是真正的‘中式科幻’。《疯狂的外星人》也许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它是非常中国也非常当下非常现实的电影,也是宁浩以自己的‘作者电影’风格,以对中国现实的体认为准绳,以好莱坞科幻片的剧情模式和宏大场面为反讽对象的黑色幽默喜剧。《疯狂的外星人》具有美式科幻电影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意义,也许预示了科幻与当下现实,与喜剧结合的可能性,为一种新的喜剧亚类型或科幻亚类型昭示了一个方向。”[30]显然,就受众定位而言,两部影片都挤进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对中国电影而言全年唯一有票房保证的春节档,这就使得在受众层面的任何分析都显得太过徒劳。更何况,能够欣赏作为“美式科幻大片”的《流浪地球》的中产阶级观众,和能够欣赏“颇为‘土气’”的《疯狂的外星人》的“小镇青年”,哪一类观众基本盘更大,在春节档期间对票房的贡献更大,已经无需再作更多辩驳。
不仅如此,在春节档和“小镇青年”的背后,还有以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所无法阐释的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作为中国当代电影最高文化工业水平代表的《疯狂的外星人》,又被安置在了全年唯一有相对票房保证的春节档,同时又看似更为符合“小镇青年”的审美趣味——却在保底发行28亿[31],刷新迄今为止最高保底发行记录的情况下,仅仅收获了不到23亿票房[32],这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实践而言,无疑是不能再辛辣的讽刺。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不仅无法有效识别具体影片的文化工业水平,也并未对影片的内容逻辑与档期的关系及规律进行基本探讨——对于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断走进影院的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中国电影的新观众的分众特征,更是几乎未触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从最初的“新主流电影”到后来的“小镇青年”“新主流大片”“电影工业美学”,使相关理论、批评话语不断加速的最主要的“权力”因素,就是从2010年到2016年,票房持续攀升的高增长所带来的强烈“眩晕感”“致幻感”。“面临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我们更应该考虑制作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国产电影。应该发挥国产电影的‘主场’优势,利用中国本土或者传统的文化‘俚语环境’,有效地解放电影的创造力。应该在以较低成本赢得较高回报的状态下,恢复电影投资者、制作者和发行者的信心。”[33]“新主流电影”概念的提出,自然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语境,其本身正是当时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所面临的种种焦虑的一个缩影。
然而,“‘主场’优势”“俚语环境”“较低成本”等这些“新主流电影”的最初“良好愿望”,在后来的“小镇青年”“新主流大片”“电影工业美学”话语当中逐渐淡化,甚至被翻转,这也使其最终几近丧失了对中国当代电影实践的阐释力,而前者恰恰是中国当代电影在当下最具活力的有机部分。这是因为中国当代电影在历经了20年左右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之后,终于通过一系列电影节、电影展的摸索、淬炼,为在其市场化、产业化的初期,曾有着浓墨重彩一笔的艺术电影创作实践,找到了一个相对符合自身国情和特点的,为整体性的产业结构所接受和吸纳的,有中国特色的“好莱坞——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式的内部循环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并不断推出了《钢的琴》《万箭穿心》《白日焰火》《推拿》《一个勺子》《烈日灼心》《黑处有什么》《追凶者也》《暴雪将至》《北方一片苍茫》《大三儿》等一批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实现了稳定的中小成本的现实题材影片供给。

四、新周期的总体格局及系统性风险
从1999年到2019年,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中国当代电影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大浪淘沙之后,今天我们再回溯其内在线索的根本目的,就是旨在通过对其话语累积过程中的种种“权力”因素的梳理,寻找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批评资源。
“三分法”并未过时,这一基本判断的背后,是当下的中国电影实践并未超脱出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世界电影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商业类型电影为中心:既可以将艺术电影吸纳为自身的预备队和后备军;也可以兼容国家意志也就是相对平顺地表达“主旋律”——中国当代电影实践并无任何“意外”发生,不过是沿着世界电影发展的基本规律,完成了各项“规定”动作。作为描述性概念,描述某一阶段的特点和特征,从“新主流电影”到“电影工业美学”尚具备一定的阐释力,但作为严谨的电影理论、批评概念,则既经不住学术层面的推敲,也无法跟上中国当代电影实践的迅猛步伐。
影片、院线产能的中长周期性触顶和回调,档期、观众的增长乏力和不稳定性,已是中国电影在2017年就开始面对的总体格局,票房产能还将进一步落后于影片和院线产能,也将是中国当代电影在下一历史周期所无法逃避的系统性风险。在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区间的现实语境下,中国当代电影很可能会面临内部影片、院线、档期、观众增量的全线匮乏,外部关注、投资、估值、认可度的全面回调,这种一方面票房体量过大、一方面几近全产业链亏损的最为被动、难堪的“滞胀”局面。
在这样的系统性风险的基本格局下,更为重要的是,“小镇青年”所表征的我国新一代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收入整体偏低的广大青年群体,几乎完全不具备传统迷影文化意义的影迷特征,也不具有好莱坞电影观众所标识出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审美趣味、经济收入、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但“小镇青年”已在悄然间改变了过去电影观众概念的外延,并开始一步步渗透,改变着过去我们所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电影生产及传播逻辑,其对“主旋律”、传统文化等领域已经表现出的令人咋舌的巨大热情和冲击力,早已实质性地溢出了电影的范畴、框架,甚至直接改写了曾被奉为“圣经”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知识。
在未来,以影片、院线、档期、观众为切口,对于“主旋律”、传统文化等“小镇青年”的文化公约数的再整合和再建构,其所蕴藏的历史势能的蝴蝶效应,对于我国的文化治理、国家治理,都将是前所未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式的历史挑战。而这其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对于世界电影史而言,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价值和贡献。

[1] 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第16页。
[2] 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82页。
[3] 尹鸿:《1999中国电影备忘》,《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第10页。
[4] 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82页。
[5] 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82页。
[6] 孙佳山:《三十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电影艺术》2017年第6期,第75页。
[7] 同上,第74页。
[8] 同上,第75页。
[9] 孙佳山:《三十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电影艺术》2017年第6期,第75页。
[10] 同上。
[11] 孙佳山:《三十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电影艺术》2017年第6期,第75-76页。
[12] 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84页。
[13] 陈旭光:《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第38页。
[14] 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第4页。
[15] 《电影的十年春节档:从8000万到近20亿》,腾讯娱乐网,https://ent.qq.com/a/20160207/010667.htm,2016年2月7日,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影报”。
[16] 《2018年中国电影行业重要档期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902/
717188.html,2019年2月28日。
[17] 《2019春节档58.3亿 火爆中有危机》,Mtime时光网,http://news.mtime.com/2019/02/10/1588937-all.html,2019年2月11日。
[18] 毒眸:《如何找回消失的8000万观影人次?》,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6618707265_18a81754101900h1ap.html,2019年5月14日。
[19] 康雅雯、朱骎楠:《2018年电影市场总结:票房、观影人次增速放缓,票价、口碑回暖》,新浪财经网,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q/go.php/vReport_Show/kind/lastest/rptid/4467363/index.phtml,2019年1月3日。
[20] 毒眸:《如何找回消失的8000万观影人次?》,新浪网,
http://k.sina.com.cn/article_6618707265_18a81754101900h1ap.html,2019年5月14日。
[21] yvonne:《人次落差近8000万,四五线城市缩水严重》,
艺恩网,www.entgroup.cn/news/Exclusive/1063656.shtml,
2019年3月10日。
[2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4/t20190408_932843.html,2019年3月31日。
[23] 画外:《中国电影市场专题研究•2017——受众、供需与票房》,2018年,第58-66页,此为网络付费报告。
[24]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全国电影银幕总数突破6万块 稳居世界第一(附图表)》,中商情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3908174637825354&wfr=spider&for=pc,2019年1月28日。
[25] 陈旭光:《中国科幻电影与“想象力消费”时代登临》,《北京青年报》2019年4月19日C4版。
[26] 陈旭光:《中国科幻电影与“想象力消费”时代登临》,《北京青年报》2019年4月19日C4版。
[27] 同上。
[28] 黄柏雪:《〈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拍美国人拍不
了的科幻片》,http://www.sohu.com/a/296706798_247520,2019年2月22日。
[29] 科欧米:《揭秘〈流浪地球〉工作法:改造好莱坞流程
背后的经验》,http://ent.ifeng.com/a/20190208/43175796_0.shtml,2019年2月8日。
[30] 陈旭光:《中国科幻电影与“想象力消费”时代登临》,《北京青年报》2019年4月19日C4版。
[31] 《王宝强会栽在史上最高28亿保底上?》,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0539090_100113360,2018年7月11日。
[32] 数据来源艺恩网,http://www.cbooo.cn/m/638300。
[33] 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第4页。
作者:孙佳山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1期(总第50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征稿和征集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启事(点击查看。学术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