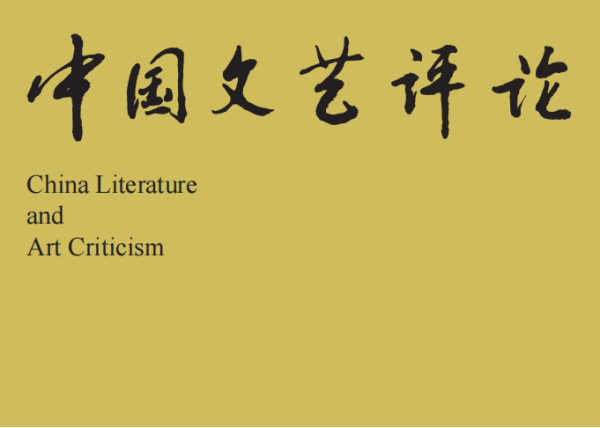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但在当下文艺领域,创作同质化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原创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文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从影视到文学,从戏剧到美术,诸多作品呈现出相似的情节、人物与风格,陷入僵硬的类型化、模式化的窠臼。这种同质化现象不仅消解了文艺作品应有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更从根本上削弱了文艺创作的生命力。本期专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挖掘剖析文艺创作同质化的根源,探讨提升原创力的路径,以期为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戏剧的“原创”与“原型”
【内容摘要】 戏剧研究中原创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否原创不能只看表面,创作离不开各种原型。中文“原型”这一概念是多义的。在技术层面上,改编与原创的剧目大多来自不同的原型——改编的原型是文学作品,原创的原型来自非虚构材料。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高,古今中外很多大剧作家有大量基于原型又超越原型的改编作品,国际戏剧评奖并不强调二者的区分。关键在于有没有原创精神——如魏明伦说的“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在文化层面上,某些特殊人物在被历代艺术家反复塑造成为社会公认的代表性形象后,成为文化原型。文化原型也可用作戏剧创作的原型素材——或重构,或质疑,或与其他人物做对比。具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的最高成就,是其创造的人物经过历史的选择,最终成为文化原型。
【关 键 词】 原创 改编 原创精神 文化原型 生活原型
原创与改编的两种原型
跟欧美剧坛相比,我国的戏剧创作似乎特别讲究“原创”。记得我回国任教还不久时,就注意到很多演出的海报及其他宣传中都喜欢强调一个词——“原创”XX剧,这是国外的戏剧海报和说明书上看不到的。开始以为这个“原创”标签能吸引更多观众来买票,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再后来我当了十多年戏剧评委,更清楚地看到,原创的大戏多半是给评委看的,自发买票来看的观众很少;事实上原创剧目往往演不长,远不如传统戏曲经典有那么持久的号召力。那为什么还要唯恐天下不知地宣传自己是“原创”呢?原来各种各样的评奖都规定必须是原创剧目,以至于千百年来习惯了改编移植、积累了很多保留剧目的戏曲,也只好频频找并非自己剧种的名家来编导“原创”新戏。有些地方年度演出总量很小,奖项又一个都不想放过,最成功的模式竟是年年“原创”,年年得奖,年年封箱;再年年“原创”,年年得奖……
欧美主要的戏剧评奖并没有这个要求。相关的大奖中唯一区分原创与改编的是美国的奥斯卡,但那是电影奖,而且也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区分,欧洲评电影奖的威尼斯、戛纳和柏林电影节就不那样分。美国戏剧界的最高奖是百老汇的托尼奖,外百老汇的非营利性剧院还有个奥比奖,都没有“原创”的要求。剧目的托尼奖只分话剧和音乐剧、首演剧和复演剧——复演老戏也十分重要,不管是原创还是改编。如得奖无数的音乐剧《西区故事》明显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但1957年首演时根本不提那是改编作品,以后每次复演倒是一定会注明是“复演”,因为导演、演员、舞美不一样。单项奖中导演奖和各类舞美奖基本相同,此外话剧评编剧奖,音乐剧则有编剧、作曲、配器、编舞四个奖,所有奖项都不问原创还是改编。
他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个戏是不是“原创”呢?因为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几乎都是改写前人原型故事的大师,而不是从头原创剧情的大师。古希腊悲剧都有原型——来自神话,只有埃斯库罗斯的“现代戏”《波斯人》是个例外,那是他亲身参加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回来以后写的。但剧中却又没写一个他熟悉的希腊人,写的全是失败的波斯人一方的事——材料多半还是听来、读来的。普罗米修斯、狄奥尼索斯、俄狄浦斯、美狄亚等最著名的希腊神话人物主要还是通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这些剧作家笔下的戏剧角色而广为人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成了人类文化的“原型”,被历代作家不断地重写,成为经过全新阐释的原创作品。古罗马文艺理论经典贺拉斯的《诗艺》早就说出了重写原型背后的道理,译者杨周翰用大白话解释道:“题材最好用现成的,才容易为人接受,而在组织安排上可以出奇制胜,这样来体现首创性。”
但中文的“原型”一词有点复杂,因为这两个字有两个很不一样但又有关联的意思:一个指学术意义上标准比较高的文化原型,英文是archetype。现代西方文论中称某些被历代大众熟悉的经典人物为“原型”——比中文语境中常说的“典型人物”有更深广的历史、宗教的维度。原型批评的旗手诺思罗普•弗莱研究的起点是神话:“我们就从神话世界着手并开始我们对原型的研究吧。这是一个既有虚构型又有主题型构思的抽象的或纯文学的世界,这个世界丝毫不受以我们所熟悉的经验为根据,按近似真实的要求进行改编这一规则的制约。”中文“原型”的另一个意思是指通俗意义上启发创作灵感的生活原型或故事原型,英文是original story/person。其实大量的所谓原创作品都有生活原型——近年来写好人好事、真人真事的剧目越来越多,原型还特别明确,只不过那些“原型”不是取自虚构的神话传说或文学作品,而是从非虚构的新闻、历史或采访的故事中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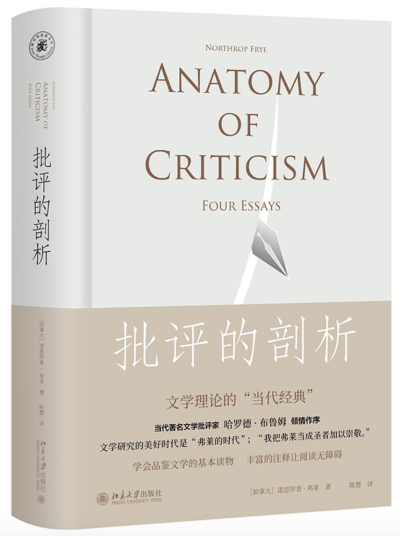
[加拿大] 诺思罗普• 弗莱著《批评的剖析》
莎士比亚最大的本领就是利用别人写过或讲过的故事原型重新创作,他总能写得比前人精彩太多。没什么人会计较他的剧本能不能算“原创”——在他的时代,戏剧完全靠观众“用脚投票”,不需要迎合任何奖项的要求。他的三四十个剧本里只有一个算是例外——关门戏《暴风雨》,其实该剧剧情里也揉进了他以前好几个戏的故事,如兄弟争权(《哈姆雷特》)、流放野外(《皆大欢喜》),等等。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编剧时都有故事原型,并非“原创”;但他借助前人的素材,塑造了如哈姆雷特、麦克白、马伏里奥等许多深入人心的戏剧人物,后来成了积淀在大众心中的文化原型。歌德最伟大的剧作是前后写了60年的《浮士德》,浮士德这个人物的原型有很多人在他之前都写过,包括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学才子”克里斯多夫•马洛,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原型。这些被后来的大剧作家赋予了全新意义的“改编剧本”直到今天还在频繁地演出,而比它们更早的故事原型却往往被人遗忘——很多甚至查不清源头了。
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戏剧史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从“原型”到“原创”的编剧方法的转型。严格地说,那是从基于文化原型的编剧转向基于世俗故事原型的编剧。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发起的市民戏剧起,剧作家逐渐减少借用知名神话传说故事的老办法,而是开始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找素材。易卜生早期的剧作还是用的历史人物或培尔•金特等传说中的人物,形式也是较为传统的诗剧。后来他越来越关心当下的社会问题,就把寻找故事的目光转向了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开始了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原创”编剧。
欧美各国都经历过这样的转型,新鲜的应时题材为戏剧赢得了更多的普通观众——特别是那些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如伦敦东区“开膛手杰克”的故事在20世纪初曾催生了不少惊悚剧作,直到几十年后的电视剧还在写它,连中国最近一部讲在美华人故事的电影《唐探1900》也用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特别能反映那个报纸大流行时代的特点,至于故事发生在美国还是英国,对中国观众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大致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案件“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故事原型也催生出了多部热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剧作品,全国各地的演出无数。
用原创精神改写文化原型
一般认为,《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直面现实社会的剧比以前那些基于传说原型的诗剧更加原创,也更有现实意义。此说很有道理,写实的剧作中还有大量如《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剧,这些老百姓更喜欢的通俗戏剧也很重要,学者也不应该忽视。然而,在导演黄佐临的心目中,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是《浮士德》与《培尔•金特》。他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歌德和易卜生写了伟大的IP,就有了伟大的剧本,而是因为这两位剧作家在世人早就熟知的那两个文化原型中注入了全新的深刻思想。易卜生后来从改写原型的诗剧转向了直面当时社会的散文话剧,但从来不贴自诩“原创”的标签,他很清楚两种剧作的差别只在于素材来源的不同——其实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原型”。与此同时,也有些现代剧作家并没有放弃重写经典故事的做法,如奥尼尔(《悲悼》作者)、萧伯纳(《圣女贞德》作者)、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作者)、萨特(《苍蝇》作者)等人还是常常喜欢用极原创的精神来重写神话传说,他们也从不给自己的剧作贴上“改编”的标签。事实上,他们的这些新版本因为有原型作对比,反而差别更明显,更能凸显出剧作家的原创精神。
但大改经典并不一定就能体现“原创精神”。元代纪君祥写的杂剧《赵氏孤儿》用了《左传》和《史记》里的故事,通过精心编织的剧情突出了原故事里未能清晰表达的思想,很有原创精神。这部经典在现当代有过无数形式的演出版本,有些主要是做了技术性的改动,如剧种、唱腔的移植;有些则大刀阔斧地删改剧情,甚至把全剧核心的报仇情节也去掉了;还有的把原剧中的屠岸贾改编成值得同情的、因报复害他在先的赵盾而变成的坏人。这些大改剧情版本就情节而言可以说相当原创,但其中有没有原创精神呢?未必。其实,“坏人也有道理”“好人不该报仇”之类的新情节反映的只是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新潮”西方理念,体现的未必是剧作家、导演自己独有的原创精神。
编织出原作本来没有的新情节或许是为评选奖项或为契合某种对“原创”的要求进行的技术性操作,但技术上的“原创”并不一定意味着是高质量的作品。“原创”二字本来是个中性词,原创作品中优质及劣质的都很多,还有大量平庸的“原创”。演过许多传统川剧、也写过不少原创剧本的剧作家魏明伦曾经写下这样三个要求: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何为“原创”的技术性问题,但这12个字可以说是关于原创精神的最好回答。具体地说,体现原创精神的作品有两大类型,现在较多的一类是根据生活中的故事原型来编剧,而另一类则是用历史上积淀多年的文化原型来编剧,《赵氏孤儿》就属于后者,其本身也可以成为今天的编剧的故事原型。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芬顿应约给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RSC)改编《赵氏孤儿》,写出了一个与中国各种版本都不一样的剧本,但反而比那些刻意不报仇或改善恶人形象的“现代解构版”更加尊重原著,保留了全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基本剧情。高子文在研究这个改编案例的论文中写道:
RSC对《赵氏孤儿》的改编走的是与我们相反的步子。首先它肯定剧本的复仇主线,直面故事中所含有的传统伦理的主题。从场刊中我们可以看到,RSC对整个故事作了一次充分的研究。他们不仅研究中国古代的不同版本,同时关注当代戏剧与影视改编,还把西方自伏尔泰以来的改编作了梳理。为了深入了解剧作的思想,他们还对比了元明版本的不同以及孤儿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表现。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RSC对挖掘传统剧本中所包含的戏剧能量非常重视。RSC的改编,首先把一种东方式的为忠义牺牲个体的礼教传统复活过来。
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连基本情节都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个古代中国的戏?但芬顿也并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给原剧加了画龙点睛——甚至可以说是点石成金的一笔:在孤儿向屠岸贾报仇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尾声,程婴来到16年前他拿出去调包送死的自己儿子的坟前,这时候婴儿的鬼魂质疑老父,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儿子去为赵氏孤儿替死?程婴无以应对,自杀了。这个英国版剧情的“原创”幅度看似还比不上那些为复仇行为或屠岸贾“翻案”的中国当代改编,却是真正经过独立思考、有独家发现和独特表述的《赵氏孤儿》。编剧并没有给它冠以“原创”之名,演出的宣传中反而特别强调了其原型是一部中国经典。
中国导演徐俊在筹划音乐剧《赵氏孤儿》时,慧眼相中了这个外国人写的剧本,买来版权改写、作曲,做成了一个在全国巡演多轮的“原创音乐剧”,成了中国音乐剧的保留剧目。这里的“原创”二字,主要是指的形式上的大幅度转换——从英文的话剧到中文的音乐剧。但跟大多数中文的《赵氏孤儿》版本相比,这部音乐剧又确实是很有独特的现代原创精神的,只可惜其剧情和主题所体现的原创精神主要还是来自那位“外来和尚”。

音乐剧《赵氏孤儿》演出照(来源:“徐俊戏剧空间”微信公号)
芬顿的秘诀是保留原型故事的基本架构和语境,在剧情中作一点巧妙的改动,四两拨千斤地体现出新的思想。还有一种方法则是将原作的故事放到全新的语境中来重新讲述,这就更容易在显豁的对比中凸显出新的思想。毓钺编剧、陈佩斯导演并主演的话剧《惊梦》就是一部这样的佳作,甚至可以说是“加倍”的佳作——在一个新语境中放进两个极其重要的戏剧文化原型。《惊梦》讲一个解放战争中两军争夺一个小镇的故事,但戏的核心情节却是两个戏剧经典的遭遇——擅演《牡丹亭》的昆曲老戏班合春社在战乱中饿得撑不住了,解放军给的粮食救了他们,现在他们要应解放军的盛情邀约,硬着头皮演出刚刚拿到剧本的新歌剧《白毛女》。怎么演?喜儿穿青衣的珠翠行头念“苦——啊”?大春像将军那样扎靠插旗“得胜回朝”?台上的角儿左右为难、哭笑不得,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演员穿上宣传科长送来的朴素的“时装”演戏,战士们的反应火爆之极,陈佩斯演的戏班主饰演黄世仁,还被台下的战士打了一枪——其实并没打中,但他吓得跑下台,拼命在长袍上找枪眼。解放军首长赶来安慰他,说当年在延安看《白毛女》,演黄世仁的陈强也差点挨了枪子——哎!你是不是长得跟他有点像呀?酷似其父的陈佩斯装傻瞪着眼不懂他在说啥,让大剧院的观众笑岔了气。这个《白毛女》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喜剧效果,更是完全始料未及:国民党军队的司令跟解放军首长当年在黄埔军校是同学,恰巧也是合春社的戏迷,还曾一起当过昆曲票友。他的副官得知后投其所好,逼着戏班也要演个戏“劳军”,却因对昆曲一窍不通,答应他们就演那个很能“提振军心”的《白毛女》。演出中途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却是兴师问罪的军官打的——他立马意识到自己被戏班“耍”了,还发现有两个营的兵被这个“共产党的宣传”感化得溜号,当了逃兵!毓鉞和陈佩斯只字未改《白毛女》的剧本和人物,只是巧妙地将其“再语境化”,就实现了一个喜剧性的重构,不但没对原著有丝毫的贬低,反而加倍有力地证明《白毛女》这部红色经典有着多么神奇的魅力!
1985年首演的川剧《潘金莲》也是一个“戏中戏”,让“戏外”的现代人来直接评说人所共知的古装人物潘金莲;但魏明伦采用这个手法,不是像《惊梦》那样用来强化戏中戏里的文化原型,而是给那个本来十分负面的文化原型潘金莲彻底翻个案。这个全新的潘金莲从人物刻画来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欧阳予倩60年前对《潘金莲》的革命性改写,但因为欧阳予倩版体量较小,又有很长时间没再演出过,而魏明伦版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剧坛的创新热潮,因此,他的《潘金莲》成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原创精神,同时又演出、移植最多,影响最大的剧作之一。
除了像《惊梦》那样强化文化原型与《潘金莲》那样挑战文化原型,还有一种做法是介乎二者之间——善意的调侃。就在《潘金莲》首演的前后,出现了两个调侃忠臣诗人屈原的戏。我写的话剧《挂在墙上的老B》(198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把悲剧英雄屈原和喜剧丑角范进放在两个戏中戏的片段里,但并不是要对比他们的不同,反而是强调两个角色的相似——“老B”在扮演了两个角色后突然悟到,在他崇拜并借以自况的屈原身上,竟也有着范进的味道。盛和煜编剧的湘剧《山鬼》(1988年,湖南省湘剧院)虽然没有采用《挂在墙上的老B》和《潘金莲》那种先锋的戏中戏形式,讲的是一个关于屈原的完整故事,但其内容极具原创精神——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湘剧中的这位屈原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那个悲愤交加的殉道者,而是来到一个原始部落,与山鬼发生了一段近乎荒诞的“浪漫”故事,反映了当时解放思想、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社会思潮。
戏曲的各个剧种都有相对稳定的唱腔,大多数戏曲作品很难用戏中戏的形式来展现创新的思想,只能像《山鬼》那样在传统的线性故事的框架里做文章,即便是整体的跨文化移植,一般也要保持原型故事的完整性。顾锡东1982年写越剧《五女拜寿》,用李尔王这个源自西方的文化原型进行了绝妙的本土化原创性编剧;就接地气而言,《五女拜寿》还超越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原型《李尔王》。莎剧中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很丰满多义,极少非黑即白的图解;《李尔王》却是个例外,三个女儿两坏一好,都是黑白分明的符号化角色。《五女拜寿》在老父和女儿的故事中植入了大奸臣严嵩弄权的历史背景,这就使中国老大臣的宦海沉浮比英国国王李尔莫名其妙分国交权更显真实;剧中还加了两个特别有戏的“女儿”——养女和最后认为女儿的丫鬟,都比亲生女儿好。《李尔王》里坏女儿的拍马屁作秀其实很拙劣,老王竟看不穿她们的虚情假意,只能说是一种粗线条的寓言式表现手法。《五女拜寿》开头是老大臣过生日,小辈们来拜寿,十分自然。女儿、女婿各有各的想法,其差异比李尔一家非坏即好的截然对立微妙得多。中国社会要求子女服从长辈,造成了虚与委蛇的客套话盛行,话里有话的心理活动唱出来往往比话剧说出来更有效、更感人。这部越剧又像改编又极原创,既充分发挥了写意的艺术特长,又以大量的感人细节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历史和人性的真实。
二十多年前我重写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是因为受到与之完全无关的中国反腐电影《生死抉择》的启发。影片中一位高官的妻子收受了巨额贿赂,高官查明真相后毅然把妻子送上法庭。我看电影时想到,“大义灭亲”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母题,灭自己的亲属当然也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俄狄浦斯克服重重障碍查明真相后采取的行动是“大义灭己”,承担自己无意中犯下的全部罪责,那是更难能可贵的行动。人类历史上好像还找不到这样勇敢担当的领导人。西方政客一旦被媒体或对手揭露丑闻,几乎所有的反应都是一边否认一边掩盖,或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俄狄浦斯那样的故事只能是个神话,却是个伟大的神话,蕴藏着极大的正能量——尤其对一向崇尚正面英雄人物的中国人来说。
由浙江省京剧团2008年首演的《王者俄狄》把整个故事移植到朝代不明的中国远古时代,不再是讲一个老人面对可怕命运的故事,而是塑造了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大义灭己的少年天子。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2012年首演的京剧《红楼佚梦》也改写了文化原型,而且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把一个外国戏剧经典和一个更有名的中国文学经典合到了一起。《红楼佚梦》也没有采用戏中戏的手法,而是把法国当代剧作家让•日奈写的《女仆》的剧情尽可能无缝地嫁接到三个红楼人物身上,让王熙凤和尤二姐、尤三姐做了日奈笔下的女主人和她手下两个女仆姐妹。全剧完全保留了中国古装京剧的框架,让京剧老观众一点看不出外国戏的影子,只当是一个情节全新的“红楼戏”,或者说是“红楼梦续集”。

京剧《王者俄狄》演出照(来源:“浙江省京剧团”微信公号)
用原创精神重塑生活原型
我国近年来的“原创”剧作很多是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是好人好事的原型。如果写的是真实的英雄,当然只能忠实塑造大家已然熟悉的生活原型,否则本人或家属、亲友都会有意见;如果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般也只能按相关领域的专家权威所认定的事件原型来写。这就使得编剧的原创程度在选材之时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想避免同质化确实难度比较大。
但在中外戏剧史上,把生活原型编成具有原创精神的剧作并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剧作家有个朋友劳拉,由于当时歧视女性的法律,她不得已用假名字借钱救了生病的丈夫,但丈夫病愈后得知真相,不但不感激妻子,反而怪罪于她。易卜生在劳拉故事的基础上加了不少更具戏剧性的元素,使之更巧更紧凑:娜拉(很像劳拉的名字,只把第一个字母从L改成了N)的债主刚好在她丈夫手下的银行工作,又刚刚被他解雇,于是在圣诞前夕来逼娜拉要丈夫收回解雇他的成命。丈夫会听她的话吗?这个剧情让夫妻俩的冲突大大强化,而且整个故事浓缩到一天之内,因债主的紧急要挟这一导火线而集中爆发出来。易卜生采用的是当时的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萨杜等人百试百灵的编剧法——一种大众艺术形式的原型,但他的原创精神主要还不是体现在一个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佳构剧”,而是体现在揭露了历史上一向是天经地义的大男子主义背后的虚伪,大声为被无视、被欺压的妻子争权利。
一百多年后,美国人卢卡斯•纳斯写了个名为《玩偶之家2》(中译名《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的新戏,为已然在全世界成为文化原型的娜拉这个形象续写了一个出走后又一度回来的故事,无形中回答了当年鲁迅问过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挑战性问题。纳斯并不像很多好莱坞电影的续集创作者那样,借原作的市场号召力编点类似的新故事来延续原作的寿命,而是大胆地反其道而行之,让娜拉那个长大后的女儿质疑母亲当年抛弃家小出走、现在还反对女儿婚恋这种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形式上这个“续集”是一个跟原作十分相似的现实主义话剧,但它与原型的关系却很像魏明伦的戏曲戏中戏《潘金莲》。虽然两个剧的主题几乎刚好相反——魏明伦质疑几百年来中国社会给潘金莲的“荡妇”定位,纳斯则质疑一百多年来进步人士娜拉的“女英雄”定位;但他们都勇敢地挑战早已成为文化原型的原著,体现出大无畏的原创精神。
在中国用现代的真人真事写原创作品,比易卜生在人物原型基础上虚构故事难度大很多,当代剧作的好例子不容易找。但是,如果把真人真事原型的定义扩大一下,也许就会容易很多。鲁迅自己说过,他的小说人物常常是一种杂合的结果,所谓“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如果用后一个方法作为生活原型的定义,还是能找到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陈佩斯编剧、导演并主演的喜剧《阳台》。全剧的开头是农民工包工头老穆爬到刚落成的高楼顶上,威胁要跳楼,向开发商讨要他们欠了工人一年的工钱。这个情节明显是取材于当时屡屡见于报端的农民工讨薪不成只能以跳楼相逼的社会新闻,但这个本来只是哗众取关注的新闻事件“跳楼秀”在这部喜剧中得到了两度的升华。首先,这是个极高明的喜剧开场行动——观众都知道陈佩斯演的老穆不可能一开场就真的跳楼而死,但此举造成的悬念无比强烈。更重要的是,全剧最后那个贪污的坏人走投无路真的跳了楼,既在结构上呼应了全剧的开头,又给这个爆笑喜剧注入了一丝悲情。陈佩斯独到地称美国喜剧《借我一个男高音》为“结构喜剧”——这是他创造的连美国人也并没有用过的概念。他把从中学来的结构手法运用得极具原创精神,升华了支持农民工、揭露剥削者的主题,结果大大超过了那个美国的剧作原型。
原创戏剧的故事原型也可能是偶然听来的,如能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有可能成为具有原创精神的作品。如俄国果戈里那部1836年首演的喜剧《钦差大臣》,其原型就是来自普希金写信告诉他的一个“骗子”的故事。普希金在1835年10月的信中写道,他在旅行时听说当地官员将一个路过的小官员误认为是秘密巡查的钦差大臣,闹出许多笑话;而普希金本人也曾被人误认为“政府派来收集叛乱情报的官员”。此外,19世纪初另一位乌克兰作家也曾写过骗子冒充官员行骗索贿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引发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那个骗子究竟是一开始就故意欺诈骗人,还是本来无意行骗、后来将错就错成为骗子?果戈里明确地把他的主角刻画成后者,更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会把清白的普通人变成骗子的腐败社会。
《钦差大臣》问世近190年来,已然成了讽刺喜剧的典范甚或“原型”。我也曾学果戈里的创作方法,在一个传说的大人物请客故事的基础上,写了一个与原故事仿佛相反的讽刺喜剧《宴席》。我听到这个传说还经过了一个戏剧的中介——当时还是南京大学本科学生的温方伊写的《蒋公的面子》。温方伊做了大量的考据功课,写了一个大致上忠实于原传说的写实的喜剧,剧中三位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纠结辩论,要不要去赴新近兼任该校校长的蒋介石的宴席?戏的结局是开放的。该剧自2012年起几乎每年都在各地演出,影响相当大。我的《宴席》是在2013年听说了《蒋公的面子》及其故事原型以后开始构思的,2016年首演于上海大剧院小剧场。这是个很不“真实”的喜闹剧,剧中好像有三位“教授”勇敢地前去赴了宴,却一个个暴露出都是捡起被受邀教授扔掉的请柬来蹭宴席的假教授:一个扫地的清洁工、一个多年没升到教授的老讲师、一个本来就不能升教授的训导员。冒牌货都有点心虚,在东道主到来之前抓紧排练拜见的礼仪,笑话百出。校长公务繁忙不来了,来的是美国名校毕业、自诩服膺美式民主的夫人,心里打着算盘要教授“劝进”自己当校长。假教授会怎么办呢?这个剧情离那个传说的故事原型可说是十分遥远,但表面的联系——最高统帅兼校长请教授吃饭的前提情境还在。舞台上夸张的情节和表演离生活原型更远,剧的讽刺意义也更强。这正是从《钦差大臣》那个讽刺喜剧的原型那里学来的。
相比之下,根据生活原型写好人好事的“好人戏”比写讽刺喜剧要难太多。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写大科学家伽利略,就浓墨重彩地写他贪吃,还很自私地不许独生女儿出嫁。但我们有很多戏是表彰英雄模范或历史伟人的,主人公不大会有严重的缺点,现在也不必像样板戏那样靠阶级敌人来反衬英雄,于是满台都是好人,没有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戏吸引人呢?
韩国剧作家白承祐写的音乐剧《星际信使》塑造了一个比布莱希特版更可爱的伽利略,这个伽利略有个贯穿始终的搭档——跟他通了很多信的德国人开普勒。开普勒慕名赠书求教,其实是想得到大科学家的背书。伽利略没答应,但很快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用望远镜探索星空,交流心得。“仰望星空”天生适合抒情,他们关于星球的对话自然地变成歌声,把观众也带进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遨游在苍茫浩瀚宇宙之间,扬起了白色风帆开始全新冒险”。他俩的对话较多地展现了科学家发现和分享的快乐——这在话剧里就很难展现。音乐剧并没有因为要“为尊者讳”而回避伽利略曾向教皇讨饶求生这一历史事实,但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科学家迫不得已认“罪”保住了生命,但并未毁坏他用以进行实验的望远镜,还保留下了关键的实验成果,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会绽放光芒。
我也遇到过一个写历史伟人的“好人戏”难题。为上海戏剧学院及其多年合作伙伴米兰皮克洛剧院(意大利最大的剧院)创作要在两国乃至各国巡演的京剧《徐光启与利玛窦》,那不仅是个好人戏,还是两个好人的戏,两个人好像还没吵过架,怎么编织剧情?意大利人利玛窦精通科学,通中文和儒学,移居中国28年后葬在北京,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徐光启是余秋雨心目中的“第一个上海人”,是精通科学的大臣,也是利玛窦最好的中国朋友和合作者。这两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的友谊与合作是中西交流史上最好的正面例子。史料上他俩的主要交往是大量的讨论与合作翻译,但如果让他们在台上讨论科学问题,肯定会曲高和寡,观众不要看,也没法让京剧演员发挥出唱念做打的本领。我的办法是在这两个好人的故事中找到坏人,干扰他们的生活。
人物原型利玛窦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有趣又感人的“暴力与反暴力”的故事,他曾被一坏太监拘捕入狱。我把两件事裁剪拼贴,变成一个引发悬念的贯穿事件:州官得知利玛窦给皇帝带来了珍奇的自鸣钟,但一直未获皇上接见,就指使强盗前来窃取。三个强盗持刀深夜来抢,利玛窦徒手自卫,赶走了强盗也失去了自鸣钟。后来州官抓住了强盗要杀,书生气十足的利玛窦闻讯赶去,呼吁宽恕强盗、不要杀人,被州官以“闹公堂”之罪名投入大牢。京官徐光启救出利玛窦与其成为至交,开展科学文化的交流,但两人也常出现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歧。最后,一个曾被宽恕放走的强盗再次打来,被徐光启制服,利玛窦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有个唱段是徐光启手持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对着一缕阳光唱的:“请看这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何其多彩又多姿。阳光看似全一律,实非一色览无余。大千世界多绚丽,天下万物浴云霓。家父为我名‘光启’——岂不正是七色‘光’彩之‘启’迪!”这是戏曲中较少见到的正面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题材作品,但也遵循京剧艺术唱念做打的形式原型,并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人颂歌,而是舞台上冲突迭起、人物间交锋尖锐的以情节带思想的情节剧。
结语
近年来,中国的戏剧创作很强调“原创”,讲原创不能只看表面,因为戏剧创作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原型。中文的“原型”这一概念是多义的,必须分而析之。在技术层面上,当下中国的戏剧创作中,改编与原创的剧目大多来自不同的原型——改编的原型一定是小说、电影等其他文学作品,原创的原型则往往来自新闻、历史、传记、采访等非虚构材料。很难说后者一定比前者高,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剧作家都创作了大量基于原型又超越原型的改编作品,国际上的戏剧评奖一般并不强调区分两者。关键在于有没有原创精神——如魏明伦所说的“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在文化层面上,某些特殊的人物——无论真实、传说还是纯虚构的,在经过历代艺术家(包括各类说书艺人)反复塑造,溢出演艺圈外成为社会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后,可称之为文化原型(archetype)。文化原型地位很高,但也是大众所熟知的,并非遥不可及,也可以拿来用作戏剧创作的原型素材——或重构、或质疑,或与其他人物做对比。富有原创精神的戏剧艺术家的最高成就,是其创造的人物经过历史的选择,最终成为文化原型。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美戏剧剧场资料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68)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孙惠柱 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9期(总第120期)
责任编辑:王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