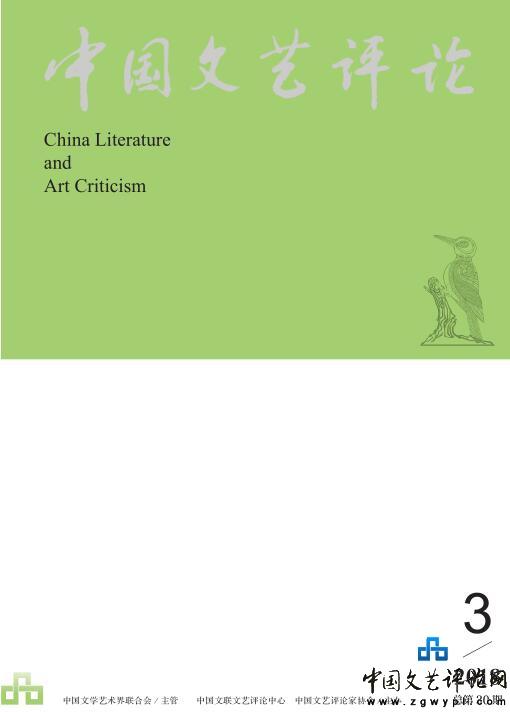
内容摘要:在中国艺术史中,艺术所表现的对象呈现出不断被“灌注”生命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理论体现,就是“传神”“写意”和“韵律化”三个环节。“传神”是艺术表现的总目标,是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直接表达。“写意”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创设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确立以“神”为宗旨,二是在繁与简的关系中确立以“简”为手段,三是在写实与“立意”的关系中确立以“立意”为枢纽。这三条路径也是“写意”之“意”的三个内涵。宋元之后,艺术的“传神”进入“韵律化”阶段。所谓“韵律化”,就是生命从表现的对象进一步渗透、弥漫到形式之中,使生命的表现更为直接、更为充分、更为强烈。
关 键 词:传神 写意 韵律化 生命精神 中国艺术
一
在中国艺术史上,魏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艺术的思考正式启动,艺术的基本理念正式确立。这个理念的最有代表性的表述便是“传神说”,它标志着艺术开始转向对人的精神特征的表现。虽然这个时期的造型艺术作品能够见到的极少,且多是后人的临摹,但在一些墓室壁画、画像石、宗教壁画以及一些雕塑上,也能够窥其一斑。这时的艺术对“神”的表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现存的作品还难以准确估计。但是,对艺术表现中的形神关系的探讨,在此前早已开始。我们知道,形神之分起源于庄子提出的神贵形轻的思想,西汉时《淮南子》对此加以发挥,将其运用到艺术表现,提出“君形者”的概念,阐述了艺术表现应重在其神而不是形。从这时开始,中国艺术的表现理念即显示出与古希腊的明显不同。后者特别重形,而前者明确表示轻形。到魏晋时期,重“神”的思想便在画家顾恺之那里正式提出,那就是以“传神写照”和“以形写神”为基本内容的“传神说”,强调艺术不仅要表现出对象的形,更要表现出对象的精神气质、内在特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
在先秦时期,造型艺术基本上是图案性的、象征性的,重在外形以指物示意,到魏晋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时代往往被称之为文艺自觉的时代。如以曹丕《典论•论文》为标志的文学自觉时代,以嵇康《声无哀乐论》为标志的音乐自觉时代。绘画的自觉时代,其标志就是顾恺之的“传神说”、宗炳的“畅神说”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等绘画理论的问世。所谓“自觉”,就是在艺术上有了独立的意识,有了对自身特殊性的认知和肯定。“独立”就是不再将艺术依附于非艺术的东西,强调艺术本身就自有其价值和意义。“特殊性”则是指艺术对自己所特有的规律、方法和功能的重视和维护。从顾、宗、谢的画论可以看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艺术表现的重心应该是对象的精神、气质、个性等内在生命品格,而非仅仅是形体的似与不似。

二
“神”“气韵”都是指人或者事物自身的灵魂所在,是生命的活力状态。艺术表现人和事物,关键就是要刻画出这种活力状态。“以形写神”是通过形体描绘来传达其精神气质和生命活力;“传神写照”则通过刻画出对象的精神而使其形体获得真切和生动。这两个命题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不矛盾,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传神理论。但是,这里的关键还是在“神”,在生命状态和生命张力的营构。唐代张彦远《画论》云:“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又说:“夫物象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1]所讲即为绘画中形神之关系。他还以顾恺之为例加以说明:“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2]
开始阶段的“传神”论是针对人物画而言的,因为人不仅是一个生命体,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情感、个性和人格的生命体。后来,“传神”就慢慢超出了人物画的范畴,在诸如花鸟虫鱼、山水树石等一切对象上蔓延开来,在以这些事物为对象的作品中,也都讲求传对象之神。王维《山水论》强调,凡画山水,必先是一个好的“观者”:“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这里的“气象”“清浊”“朝揖”“威仪”,就都是人格化的语词,表达的正是人的精神内涵。所以在最后讲到画山与树时说:“山藉树而为衣,树藉山而为骨。树不可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树之精神。”[3]
在中国画家看来,山、树乃至一切的景与物,都是自有其精神气象个性情怀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人有精神,动物也有精神,甚至无生命的山水云石等,也都是有精神的。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普遍存在,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主体间性,即一切事物都是主体,人与万事万物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既然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则对待一切事物现象,也就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的主体。这是中国艺术和美学能够在很早就提出“传神”论的根本原因。从魏晋开始,中国的艺术就不仅仅在表现事物的形,更重要的是透过形来表现事物固有的内在精神气质。例如画一棵松树,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勇敢顽强的生命精神;画一枝梅花,其实也是以梅花来表现一种高洁脱俗的精神气韵。在中国,很多艺术的题材都是具体的物的形态,但由此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生命、一种精神、一种意蕴、一种人格。
三
“传神”概念在魏晋提出后,就成为艺术表现的一个标杆,引导着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和艺术发展的历史走向。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传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传神论”的提出者顾恺之,其传神也不是常常能够实现的。唐代张彦远在其《古画品录》中就有过批评,认为“顾恺之,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4]“迹不逮意”,就是所画之笔墨并不都能够完满地表现对象之精神和意蕴。因此之故,张彦远只把他列于第三品之中。正因为此,才有了后来艺术家在如何让艺术更好地传神方面作出不倦的探索。经过一辈辈艺术家努力,到唐宋之时,便在理论上逐渐形成“写意”的概念,在实践上也逐渐形成写意的艺术。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即:“写意”与“传神”是什么关系?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是并列关系,“传神”侧重艺术表现对象的方面,“写意”侧重艺术家主体意识的方面。但仔细考察人们在使用“写意”时的内涵,就会发现这并不真确。正确地说,这两者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传神”是目的,“写意”只是为了达到此目的而采用的手段。考察我们在使用“写意”一词时的语义,就会发现它无非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形与神关系中,以神为中心;二是在繁与简关系中,以简为手法;三是在象与意关系中,以意为枢纽。其实,这三个内涵都是在通往“传神”的路上逐渐摸索出来的,因而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实现“传神”而展开的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就是与“形”相对的“神”,主要指精神、意态、心灵、情韵等内涵性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写意”与字面上的“传神”重合。不过,顾恺之之强调传神,尤其重视眼睛的作用,认为传神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对眼睛的刻画来表现的。《世说新语•巧艺》所记:“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指示代词“这”的意思,指的就是眼睛。他的这个思想,在其他记载中亦可见出。《巧艺》中还记有一则云:“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5]据《晋书•列传》载,顾恺之特别喜欢嵇康的四言诗,经常以这些诗的内容作画。其中一首叫《赠秀才入军诗》,内容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画完后感叹地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手挥五弦是肢体动态,是可见的,因而也可以入画;目送归鸿则是人的心态、意态,它无迹可寻,所以才难。但恰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展现了人物的神态、神气。此外,在他所作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中,更是强调了眼神的重要:“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6]眼睛之神需要同它所视之物(“所对者”)相呼应,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表达。可见,在顾恺之看来,“目精”(眼睛)是绘画传神的一个重要窗口。后来的传神论则大大超越“目精”的范围,它几乎包括被描绘对象的所有部位以及其动态姿势。由于人的精神可以通过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得到表现,所以这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就都可以是传神的载体。例如苏轼,就既承认“目精”的传神作用,同时也指出颧颊、举止等也有这样的功能:“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盖可以增减取似也。”[7]所以,后来的“写意”,在着眼于“神”的方面,与顾恺之完全一致,但其表现手法却又远远超出于他。再到后来,“传神”又扩展到传一切事物之神,如宋邓椿所说:“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那些“只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的人,是为“非画者”。[8]这样,在人和动物以外的许多“物”是没有眼睛可画的,此时,要表其神,就一定得越出“目精说”的范围。
第二个路径主要指“简略”“概括”,它与细致、精微相对。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形象,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处都具有同等的传神功用的,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效果的细节,而另一些则无关紧要,就好像我们认识客观事物一样,有一些是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有一些则涉及事物的本质属性。正确的认识活动就是抓住本质的方面,而舍弃次要的、非本质的表象。在绘画上亦如此。画一个事物,就要抓住其本质的东西,而舍弃其非本质的东西。当然,在艺术中,我们往往不使用“本质”一词,而代之以“特征”。要想表现一个事物的精神,就要抓住它的特征。这个思想,在顾恺之那里即已出现。《世说新语》记有这样的事迹:“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9]他给裴楷画像,把他颊上三毛也画了出来。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这颊上三毛已构成他的特征(“识具”),抓住特征,其神即会显现出来。自然,在抓住三毛的特征时,同时也就会舍弃其他无关紧要的细节,这就是概括、抽象,以使其简略。使其简略,就是对形象作简化处理。苏轼在谈到“优孟学孙叔敖低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时说:“此岂能举体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10]优孟扮演孙叔敖非常生动逼真,但不可能是所有细节都很逼真,而只是抓住特征,写其大意,即所谓“得其意思”。所以,写意的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比写实性艺术要大幅度地简化。而且,不仅在形上要简化,在色彩上也要简化。唐代王维被认为是写意画的开创者,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用水墨取代五彩。他在《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水墨是对色彩的抽象和简化,因为它代表的大自然的本质所在。所以,在绘画史上,写意画和水墨画往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第三个路径则是艺术家主体方面,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体现出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个性才情等主观的“意”。这个意义上的“意”主要与操作相对,它既指艺术家对其将要创作的作品的布局、经营有一个较充分的“构思”,同时也指将要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内容上的“立意”。王维《山水论》开头即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此“意”即指画作的布局经营,构图立意,所以他紧接着便说:“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又说:“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楼台树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两头,树看顶宁页,水看风脚:此是法也。”“诀”和“法”都是指画山水的要领、法则。当然,具体内容还有很多,但除了这些技术上的规则外,他还特别指出要有“画题”。“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或曰烟笼雾锁,或曰楚岫云归,或曰秋天晓霁,或曰古冢断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类,谓之画题。”[11]“画题”就是绘画的主题,就是对准备完成之作品的“立意”。“立意”是一幅作品的主脑、灵魂,这些都必须在创作之先即已酝酿好,准备好。在他看来,这个“意”也应该是“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最后所说必须画出山水树木之“精神”,此“精神”也是与“意”分不开的。总之,在王维的这段话中,有法,有规,有题,有神,综合起来,就是通向“传神”的另一个路径,是“意”的另一方面内容。这个“意”,也就是绘画之“理”。其中的“题”,就是强调画家主观的动机、目的以及要表现的内容,就是“立意”。这意味着,写意的“意”,已经不仅仅是指对象本身的精神特质了,同时还指画家构思命意上的创造性。就这个意义上看,“写意”是对“传神”在另一方面所作的发展,是画家主体性的进一步高扬。
写意的这三个路径,其实质如何?回答是:赋予对象以鲜活的生机,展示其生动的生命张力。努力表现生命的张力,是中国艺术的真正本质。早在《庄子》那里,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解衣般礴裸”即意味着艺术家在创作之时所必需的无拘无束、高度自由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所形成的一种极富张力的生命体验。只有创作者进入这一状态,才能够使它实现在作品之中。这个思想,张彦远在《论画》中所记事迹很能说明问题:“开元中,将军裴旻善舞剑,道子观旻舞剑,见出没神怪。既毕,挥毫益进。时又有公孙大娘,亦善舞剑器。张旭见之,因为草书。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12]吴道子观裴旻舞剑而成就其画艺,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成就其书艺。这里使他们成就的正是舞剑本身所具有的运动感及其张力样式。他们在观看中真切地感受到剑舞的动态和张力,故而才能够转移落实在自己的书画创造之中。也就是说,他们二人的书画作品从剑舞中获得非凡的生命张力,才是艺术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的意思所在。在这里,“气”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明代唐志契在论及“气韵生动”时说:“盖气者有笔气,有墨气,有色气,俱谓之气;而又有气势,有气力,有气机,此间即谓之运。而生动之处,又非运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穷,深远难尽,动而不板,活泼迎人:要皆可默会而不可名言。”[13]所以,神中一定是有气,气一定有势,势即含运;而生动就在气、势、运的基础上产生。“传神写意”,目的也就是要把对象的生命活力充分地、有力地展示出来。
四
宋元之后,中国艺术进入韵律化时期。所谓“韵律化”,是指艺术对生命张力的表现“渗透”到形式本身,通过形式直接呈现。其典型的样式,在书画中是对笔墨趣味的追求,在音乐中则是对声腔韵味的追求。例如古琴音乐中,就存在着从早期的声多韵少到明清时的韵多声少的转换;在戏曲音乐中,也存在着由元代杂剧的北方以气为主的声腔向明代传奇的以韵为主南方昆腔的转换。最为典型的还是书画艺术,虽然早在唐代,就有王维等人起而倡导水墨写意画,但在实践中影响并不大,成就也不显著。到宋元时,逐渐形成文人画的传统和观念,如苏轼的不求形似,倪瓒的逸笔草草,并以其墨竹、山水显示了文人写意画的成就。而梁楷的泼墨写意人物《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等,亦横空出世,展示出写意画的新气象。但总体上说,宋元时的水墨写意还属于个别现象。自明代起,这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画风勃然兴盛,出现了徐渭、朱耷、石涛以及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其余绪直至近现代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形成一种“大写意”的绘画潮流。此时的“大写意”与以前的三种路径的写意有很大不同。以前的写意主要在对表现对象所作的抽象、概括,以其简化突出其精神气质所在。现在的大写意则将形象推居次位,而将重心移至笔墨形态之上,直接在笔墨形式本身体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元代汤垕说:“今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盖其妙处在于笔法、气韵、神采,形似末也。”[14]此处“古人”就是以顾恺之、谢赫、吴道子开创的传神系统,而到汤垕时已强调要将其实现在笔法、气韵、神采上面,也就是使其笔墨化和形式化。清代唐岱《绘事发微》论气韵时指出:“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而气韵的实现,全在笔墨。“气韵由笔墨而生,或取圆浑而雄壮者,或取顺快而流畅者,用笔不痴不弱,是得笔之气也。用墨要浓淡相宜,干湿得当,不滞不枯,使石上苍润之气欲吐,是得墨之气也。”[15]笔墨化、形式化的精髓便是韵律化,注重运笔用墨之中表现出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有许多方面的对比转换,如:虚实、浓淡、粗细、轻重、干湿等等。韵律本身就植根于人的生命力状态,将对生命的节奏、律动的感觉实现在笔墨形式中,就是韵律。对韵律的追求一定注重笔墨趣味,它是绘画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说,以韵律化为核心的大写意的水墨画,是绘画进入到成熟阶段、并踏上审美高原的一个重要标志。
[1] 张彦远:《画论》,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2] 张彦远:《画论》,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3] 王维:《山水论》,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4] 张彦远:《古画品录》,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22页。
[6] 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7] 苏轼:《论传神》,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9页。
[8] 邓椿:《画继》,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29页。
[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20页。
[10] 苏轼:《论传神》,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9页。
[11] 王维:《山水论》,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12] 张彦远:《论画》,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5页。
[13] 唐志契:《论气韵生动》,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20-221页。
[14] 汤垕:《画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
[15] 唐岱:《绘事发微》,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9页。
作者:刘承华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3期(总第30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吴江涛
延伸阅读(点击可看):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