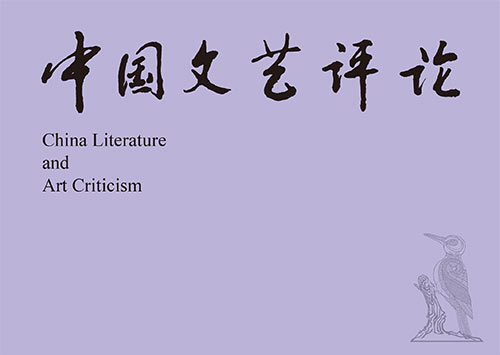
内容摘要:网络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也影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国族性”和“民族性”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以有较高点击率并获纸质出版的网络小说《苗疆蛊事》为例,从叙事策略上分析网络文学在促进民族性大众化过程中的优势,并概括了当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体特征,以及这一新型民族文学样态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少数民族文学 网络文学 民族性 大众化
在当下中国,网络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语境。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国度,网络的影响无远弗届,网络文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最重要的审美化表现形式,文学在网络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看到,网络对人类的影响不止于像通讯、电商、社交等生活的表面,而是深达人的内心,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传统变革最重要的力量。经由网络的增强,文学中直接关联俗世生活和主体肉身的功能被放大,承载这些功能的大众通俗文学进入网络,演变为网络文学,依赖技术之便和资本之利,重兴低迷的大众阅读市场。这一现象也波及到不同民族的写作现场,在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网络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崛起,使文学中的“民族性”迎来了“大众化”的时代。
一、中国文学的“国族性”与“民族性”
文学以文化为根基,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传统文化精神和民俗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天然带有民族性。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既然艺术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那么,这种生活对艺术自必有巨大的影响,它之于艺术有如燃油之于灯中的火,或者,更进一步,有如土壤之于它所培养的植物。”[1]果戈里则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2]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学中的“民族性”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映。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概念,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关系,既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但又不是各民族的简单叠加,而呈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文化向来是确立族群身份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3]这也就是海外华人尽管离开祖国多年,但仍自称“炎黄子孙”或“中华儿女”的原因。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汉族和其他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情感、道德、审美和理想愿望等是有共通性的,我们或可将其称作“国族性”或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比如爱国爱家、团结奋斗、爱好和平、以人为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中国文学的广义的“民族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国族性”特征的体现。为防止混淆,我们将其称作“国族性”。国力的增强带来了民族的振兴,对“国族性”的表达在当代文学中是逐渐增强的。
其次,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具体族属的文化特征。自秦朝“书同文”之后,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于汉语的正统地位和中原王朝的文化影响力,汉民族语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汉语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每个民族均有文学创作活动,有口头文学或书面文学作品传世。诚然,以母语进行的文学创作最能体现该民族的民族性,但一个不能忽略的悖论是,民族语言写作只有转译为汉语之后,才能进入“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指称的范畴和中国文学史的序列,即曾有学者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多数民族文学的叙述其实是各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叙述”。[4]这一现状,又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具有一致性。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与我们奉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5]的民族政策相一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开始就是以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多民族文化文学共同繁荣为目标和价值诉求的。[6]这就是多民族文学“汉语重构”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文学的格局因网络文学的滥觞而被改变时,假如网络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能够从后者的概念中析出,则“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显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在网络时代的新变。但在文化生态嬗变的大背景下观察现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又绝非少数民族文学“网络化”这样简单的对应或线性的发展,而包含着复杂的裂变和融合。网络至少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两个方向上的重要影响:一是会进一步缩小“民族性”与汉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文化特征的差距,文学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趋于同质化;二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民族性”会因为网络文学巨大的受众群体而进入大众视野,被大众了解和接受。
二、民族书写中的时代表征
作为1949年之后才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多元”的重要一极[7],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为现代化的中国保留着原初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关乎形成民族特质的农耕文明或游牧文化传统。随着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城镇化步伐加剧,乡土文明遭遇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改革的红利,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发生明显改变,游牧者的帐篷被定居点的房屋取代,太阳能电站驱动的电视和网络打开了民族地区封闭生活的闸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精神追求迅速被外界同化。
这是时代精神一个可见的表征,频繁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和非少数民族作家有关民族地区生活的书写中。一篇名为《寒婆岭》[8]的短篇小说为上述时代精神创造了一个鲜活的隐喻。小说以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寒婆岭”作为展开故事的地理背景,寒婆岭上的三斗坪村每年都要举办走“高脚马”(类似于中原地区的踩高跷)的比赛,这不仅仅是一项集体参与的娱乐活动,而且是一场带有原始色彩的精神狂欢仪式。比赛具有调和日常伦理的功能,冠军得主将会获得巨大的荣誉,在村子里备受尊崇。作者写道:“这是让三斗坪沸腾的角逐,能把五脏六腑都翻洗干净。激动驱除掉冷漠,三斗坪满是吼声和笑声,邻里隔阂烟消云散。”腿部有残疾的高脚女人曾经凭借毅力接连几年都赢得冠军,但随着三斗坪村生活的改变,她慢慢失去了荣誉带来的荣耀感:“冠军的分量一年不如一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参加比赛的人越来越少。她的独眼男人也打工去了,弄了个假眼,还有了别的女人,到了山下开始修高速公路那年,比赛不得不停,除了她没人报名。”在小说的结尾,这个在高脚马比赛中不服输的高脚女人被大耳朵羊撞下了山崖,“寒婆岭和周围几座大山茫茫苍苍。最后两户人家也搬走了,留下房屋在草丛灌木中圯废、倒塌”。
“高脚马”比赛由盛转衰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商业消费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变:所谓“衰变”之“衰”,是以民族传统文化特质为坐标对变化的衡量,那些显现民族性的特质正在遭遇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分解,尽管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正因为衰变的存在,才引起了诸如《寒婆岭》这样的写作对民族传统的凭吊。在很多写作者那里,“民族性被视为一个牢固的疆界,有效地抵制世界的入侵,从而保障民族文学的纯洁程度”。[9]但“显而易见,这个时候文学的民族性已不是进取型的,而是防守型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将‘民族化’视为一个防御性的口号”。[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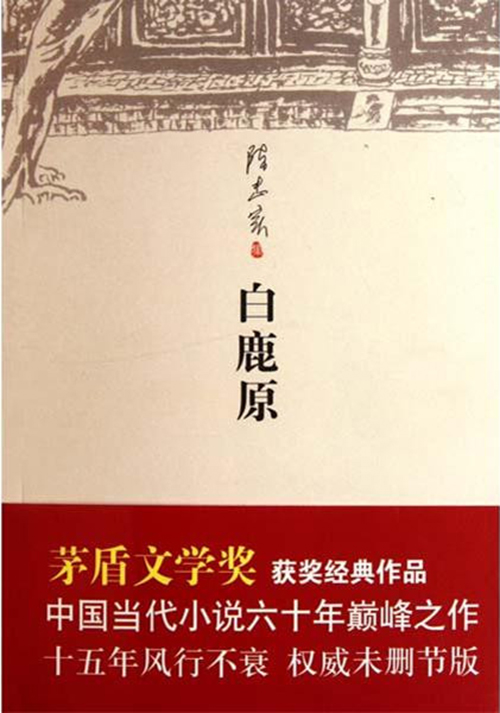
《白鹿原》
面对整个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融合了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存在,使上述对民族性的“防御性”写作已与作家的具体民族身份没有关系,而成为很多写作者自负的责任。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当代文学写作中,从《古船》到《穆斯林的葬礼》,再到《白鹿原》,无不带有这种印记。但是,寒婆岭上“高脚马”比赛现场的狂欢散尽,苍茫大山再也听不见欢呼声,三斗坪的荒废不可阻挡。面对如此变化,文学对民族性的坚守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防御性”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文学可以是一种凄婉的凭吊,或许这种凭吊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但是,在网络时代,面对新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变迁趋势,文本意义上的精神修复似乎比悲怆的坚守更加重要,因为文学毕竟是心灵之物,而非行之有效的实践技能。所以诸如文学的“庸俗化”和“媚俗化”,只不过是从传统的视角观察文学之后的结论。但是,在资本和技术面前,传统生活并未因为文学的挽留而放慢日渐世俗的脚步,文学参与建构起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被娱乐性、消遣性所代替,少数民族文学也没有因对“民族性”的坚守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观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去除当代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遮蔽后,在描写民族风情、反映传统价值观、关注传统生活在时代中的新变化、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等方面,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有更多的可能性。
三、网络文学的叙事策略——以《苗疆蛊事》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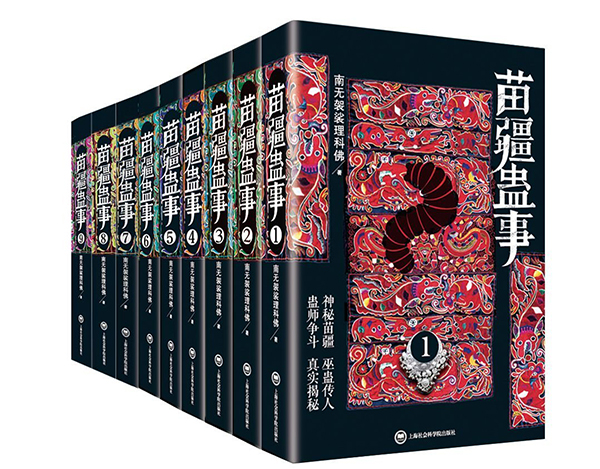
《苗疆蛊事》
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态度上,网络文学的叙事策略与传统文学有着根本的差别。
网名为“南无袈裟理科佛”的网络作家创作的小说《苗疆蛊事》是一部标本式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品。该部作品自2012年11月起在磨铁中文网开始连载,至2014年6月“番外篇”完结,总长四百三十多万字,引起读者热烈关注,点击量超过5000万次,获得读者推荐票近240万张。[11]连载期间,同名实体书即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显而易见,当下绝大部分传统文学作品几无可能达到这一关注度。
《苗疆蛊事》通过明暗两条线索展开叙事,明线讲述一位名叫陆左的青年受到外婆种下的“金蚕蛊”之后,为了完成自救不断奔波,除了增长个人“能力”之外,更多的在于内心的磨练和成熟,并且最终实现了从“自救”到“救世”的蜕变;暗线则深挖夜郎王国骤然覆灭之谜,以小说的方式探寻历史疑云。小说以陆左在朋友帮助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打败邪恶的“邪灵教”组织,在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之时以“金蚕蛊”的生命为代价完成救世之事为结尾,也让人物完成了自我救赎,找到了心灵的所在。
诚然,小说中的悬疑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放在悬疑类型小说序列里,区别于只靠离奇情节形成传奇效果的作品,这部小说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其故事背景、情节安排和人物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的新变,这就使得读者在享受故事本身带来的新奇体验的同时,也了解了苗族的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精神价值。
首先,对苗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小说中的“放蛊”和“养鬼”等情节尽管在现代人看来荒诞不经,但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来历,可以说是苗族传统中神秘的民族信仰。《辞海》中解释“苗族”时说:“与古史传说中的三苗、九黎部落有渊源关系”“信仰鬼神,崇拜祖先”;[12]而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关于贵州、广西、云南等所辖州县苗族聚集地的民俗风情描写中,在“力于稼穑,民少争讼”“并秉礼守义之风,尚气节廉隅之行”等之外,不乏“唯尚巫术信鬼,陋习未除”“好佛信鬼”“信巫鬼、尚诅盟”之类的记载。[13]《苗疆蛊事》的作者本人有苗族的身份背景,熟悉苗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选择第一人称,以此入笔虚构故事,写得贴切自然,很有文学真实性。有网友留言:“之前看过一个关于蛊的小说,一看就是假的,为啥这个情节这么真呢?”[14]这正是来自小说里浓烈的民族文化背景。作者总是从传统文化中为人物离奇的行为寻找根据,类似“我们那里是少数民族,家里面有长辈懂这些,所以我就学了一点”这样的话经常挂在陆左嘴上,无形中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
其次,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与现实中的民族生活产生某种对应。陆左从老家到广东打工,回老家时接受外婆秘传的“金蚕蛊”,之后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里生活,一方面守护传统的秘密,并想方设法提升能力,救赎自我;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用特殊的能力惩恶扬善,实现拯救世界的愿望。小说里的这些情节可看作是古老传统在现实境遇中的深刻隐喻,外婆和罗二妹的故去预示着传统文化的消亡,外婆遗传留下来的术书则被陆左转化成电子文件,成了应急时可以查一查的实用宝典。在过去被尊为“道”的传统精神到了陆左这里则成为安身立命的“术”,这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蜕变。作者借陆左之口,直言传统道德的衰败:“很多人都说乡村淳朴,是人类最后一片乐土,说这话的人大概没几个在农村待过,其实哪儿都一样,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我所待过的、接触过的农村里,经常碰到兄弟分家不合,寡妇门前被欺,或者偷鸡摸狗……”显然,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广义的乡村传统的颓势在民族地区也不可避免。
第三,《苗疆蛊事》中应当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它的叙事视角。主人公陆左“老家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临湘西,是十万大山的门户”,作者是站在民族传统立场上书写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碰撞与交融,所呈现的恰是古老传统与现代世界相遇时的不适与矛盾。外婆的师父是个“养蛊”高手,外婆也曾向行凶作恶的土匪“下蛊”,但是,“一直到七八十年代,行政下乡,寨子与外界联络渐渐多了,外婆才开始淡出了外人的视野,在苗寨里祭祀、拜神、看病、算命,了度残生。”就是这样一位掌握着传统密码的人,积极推动后辈走出寨子。母亲在向陆左讲述时说:“你去打工的时候,我们都拦,结果你外婆帮你看了下香,她说你良如玉石需磨难,说让你去外面的世界受点苦,对以后的人生有帮助。”陆左在外经历的诸多困难,包括从事过艰辛的工作,还曾被骗入传销团伙,以及他身怀“金蚕蛊”再返广东后所遭遇的种种磨难,都表示着传统进入现代时的艰难。但可贵的是,陆左并没有止步,而是不断突破传统和自我的屏障,逐渐融入新生活。尽管他拥有能驱动“金蚕蛊”和“小鬼朵朵”的神秘功能,但他的成功仍然靠的是勤劳和信义这些传统道德,他与饰品店的合伙人阿根以及曾经帮助过他的顾宪雄之间的交往即是例证。作者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作品传递着正能量:“我希望大家在闲暇之余看苗疆(《苗疆蛊事》)的时候,能够从故事的进程中学到一些做人的态度,比如善良,比如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坚持,比如刻苦。当然,如果因为《苗疆蛊事》而对我的家乡锦屏的发展和文化感兴趣,那就再好不过了。”[15]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苗疆蛊事》与《寒婆岭》的立场不同。对待民族文化,如果说《寒婆岭》是批判性视角,则《苗疆蛊事》是一种进取的、发展的和建设性的立场,是站在民族传统的视角上来写的。朱寿桐在谈到鲁迅的创作时说:“于《呐喊》《彷徨》之后,伟大的小说家鲁迅中止了小说创作。人们对鲁迅小说创作中止的原因作过多方面的寻证,可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小说中的审美价值体系尚不完备。一个完备的审美价值体系,必须确立肯定素质的美的形象体系。而鲁迅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从否定意义上显示审美价值倾向的。”[16]新时期之后,传统文学中像《寒婆岭》那样对“民族性”的书写与对农耕文化衰变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否定意义上显示审美价值”,缺乏对体现民族精神的美的形象“肯定”的书写。网络文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弥补了传统文学的不足。在《苗疆蛊事》中,作者用符合大众趣味的审美方法制造“爽点”,让读者在消遣性的阅读享受中,了解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魅力和衰变的遭遇,并经历了在融入外界生活时既保持特性又顺利实现转化的体验。小说还通过读者与人物之间的代入感,藉由人物在外界的命运体味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新变,形成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理想体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苗疆蛊事》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转型和叙事立场的调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其有效性则通过巨大的阅读数据得以体现。
四、民族性的大众化之路
民族地区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文学变化受到文艺评论界关注。马季在《网络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正在步入网络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成为网络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17]。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季探讨了网络写作与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是心灵还乡的新航线,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也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而且网络传播为少数民族作家展现自己民族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民族文化可以扩大传播面和辐射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18]杨玉梅的《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民族文学的坚守》一文将少数民族文学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进行考量,指出市场经济时代文学和作家被经济浪潮推挤到社会边缘以及被现代传媒冲击的现状;同时,也指出了文学写作将走向平常化、通俗化、群众化、非专业化、庸俗化和媚俗化。[19]
在大众文学流行的时代,我们似可从更深的层面估定网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从文化意义上看,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新形态,恰恰为少数民族写作处理“民族性”与“大众化”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在纸媒时代是不具备的。有学者说:“通俗小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各个民族的通俗小说的文化思维和价值判断。”[20]这不免令我们想起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格萨尔王》(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史诗,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诸多汉族传说。其中内涵的“民族性”从外部来看,存在着区别于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的异质性元素;而从内部来看,这些史传传说是符合本民族或本地区的大众审美需求的,正是各个民族通行的“文化思维和价值判断”的体现。
有学者论及,民族性的“从众原则”对本民族内部作家的个性化创作造成了阻碍,因为“真正独创的文学在诞生之际总是超越大众的,作家总是向积淀于大众之中的审美惰性发出挑战,并且试图以个人力量开辟民族文学史上的新纪元”[21]。所以,理解文学中的“民族性”概念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分:置身诸多民族之间,人们将强调个性;囿于本民族之内,人们则遵循从众的原则”[22]。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由封闭走向开放,作为当代文学“内部”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强调个性、在本民族内部追求“大众化”的同时,也必然开始面对“外部”的大众。因此,平衡“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关系,使“民族性”逐渐成为“大众化”的内容,是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应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来,各民族已有的大众文学(包括口头文学)传统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提供着审美的范式,尽管这些范式符合本民族内部的“民族性”审美,但在纸媒时代,流通传播方式范围极其有限,很多作品并未大量接受过“外部”普罗大众的审美检验。网络时代,新的大众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诞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迎来了使“民族性”大众化的机遇,也同时面临着保持“民族性”的压力。因此,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对“内部”“审美惰性”的挑战,主要以适应新的传播方式为方向——作为大众文学在信息时代的网络化,网络文学已经在创作方法和文本形式上形成了自身的规范——在此基础上,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本民族传统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在主题和价值观念的表达上不断探索继承创新的路子。
在小说《寒婆岭》中,“高脚马”比赛作为一项文化娱乐活动,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随着群体生活的改变,绵延日久的狂欢仪式不得不走向停止。而在《苗疆蛊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故事生成的背景被展示给大众,小说满足着不同身份的读者多向度的审美取向,一是共性的需求,一方面,小说用通行语言作为工具,首先使作品有了被广泛阅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学,“反映大众愿望、价值观和情趣”[23],它的创作和接受原理是与整个人类的精神需求相一致的,因此,无论对于有着苗族身份和生活背景的人,还是族外的人,《苗疆蛊事》符合大多数人的阅读期待,能激起大众阅读兴趣。二是差异化的需求,小说营造了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这能使民族“内部”的读者对环境和人物产生情感,并表现出对民族命运变化的关切和憧憬;而对于苗族以外的读者,小说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书写,特别是对神秘文化的展示,等于创造了一个“异域”,使之产生强烈的探秘和猎奇心理,再辅以传奇性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足以让大众在庸凡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阅读快感。
由此可见,《苗疆蛊事》较好地处理了“民族性”和“大众化”这一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一方面坚守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同时让“民族性”在大众化过程中被传播和接受,所以它被读者热捧就理所当然了。
五、民族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在中国当代文学或者中国网络文学的范畴中谈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能将其与网络文学的整体割裂开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当包括几重含义:一是指以少数民族文字为母语的网络写作,它们虽为网络文学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却独立于普遍意义上的网络文学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有学者建议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归入比较文学的范畴。[24]二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的通用语网络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与民族性的关系大多只表现在题材上,隐含的叙事方式或许也受到作家民族身份和民族生活经验的潜在影响。三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在网络上发表的一切文学作品,与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网络文学范围相同,不单指狭义范畴中的网络小说,而是包括了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
当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现状,大致相当于网络文学在中国大陆兴起初期的景观。我们尚不具备条件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仅仅狭义化为普泛意义上的“在网上生成和阅读的长篇小说”[25]。除了传播方式的不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新样态尚不能与“传统文学”严格区分开来,因此,谈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仍需观照“文学”这个整体。综观当下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现场和批评界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关注,大抵可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可循:
1. 相对于数以亿万计的网络文学读者,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学普及程度较低。尽管没有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品和网站全面、权威的数据统计,但由个别作品网上点击情况可窥一斑。据《网络文学五年普查》(2009-2013)载明的情况,以2013年3月6日为统计节点,纵横中文网排名第一的作品《永生》的点击量为2.68亿次,但在以蒙古族为主要用户对象的“草原雄鹰网”上,排名第一的《狼图腾》只有11.3万次,二者相差甚远[26]。这种情况应当主要受到互联网整体应用环境的影响,以政务微博为例,据2018年1月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分省区统计显示,广东省共开通政务微博12395个,而排在第19位、也是排名最靠前的省级民族自治区新疆只有4208个,排名末尾的西藏更只有358个;而一年前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广东省共开通政务微博12707个,而排在第18位、也是排名最靠前的民族省份新疆只有4111个,排名末尾的西藏更只有329个。[27]新疆、西藏政务微博在2017年分别新增97个和29个,而广东政务微博不增反降312个。两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互联网应用水平与增长态势。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作品点击率和公共性网络用户的绝对数量受到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出网民整体对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缺乏关注。
2. 专门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刊布在两类网站上:一类是综合型文学网站,大部分与传统文学作品夹杂在一起;第二类是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刊发在一些政务、门户等网站的文学板块上。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中,部分网站是专门提供文学相关服务为主营的专业文学网站,其余大多数是非专业文学网站,此类网站挂靠在族裔门户网站的文学频道,或是以论坛和博客为平台。”[28]这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广义的对网络文学体裁范围的界定,认为一切网络上的文学形式都是网络文学,而非已被网络文学业界“约定俗成”认定的在网络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这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当下我们所谈论的网络文学在观念上的重大差异。这也反映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网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生产和发展初期相当,尚未走出“网络文学就是把文学作品电子化之后放到网上”的模式。可以说,当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就是广义上的网络文学初期的缩影。
3. 单纯就在网络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而言,与传统作家相比,大部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者的民族身份意识并不强,其作品的“民族性边界”并不清晰。体现在作品中,形式和内容上并不一味固守着与本民族有关的题材,而是将视野投向俗世的现实生活,比如苗族作家血红的玄幻小说,满族作家金子的穿越小说,壮族作家忽然之间的都市小说,侗族作家苍苍子的校园青春小说等。或许在他们的成长中曾经得到过本民族文化的滋养,而且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创作纳入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他们的作品与少数民族身份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对这部分作家的作品做过多的关于民族文化的阐释是无意义的。但也的确有一部分作者以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基础,写出了反映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佳作,《苗疆蛊事》是一例,其他如苗族网络作家西子创作的《蚩尤大帝》,就是作者在跟苗族老人学习苗族古歌,并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创作出的反映苗族上古历史的小说;白族农民网络写手宋炳龙,发表在云南文艺网的原创武侠小说《郁刃浪剑》,也对历史上南诏历史和白族民俗风情有一定呈现,这些作家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民族文学大众化”之路。
4. 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学产业化程度较低。在少数民族地区,刊载网络文学作品的网站大部分是政府部门主办的公益性网站或者民间非商业性网站,主要以宣传、交流为主,与民族生活有关的文学创作仍然主要是传统文学的网络化,商业收益并非主要目的,所以并不能复制商业网站的赢利模式。《网络文学五年普查》(2009-2013)中即说:“少数民族文学网站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说在文学方面得到了民族和社会群体的肯定,但是从商业经营方面来看,却一直没有寻找到合理的经营模式。”
综合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民族性”大众化的内在诉求和受到媒介变化的影响,以及上述发展现状,我们或可有以下展望:一是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将成为坚守民族传统、反映民族生活、书写民族精神、呈现民族新变的重要载体;这种大众文艺样式的流行,将会给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带来有利影响;二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将会更多地融入网络文学整体中,特别是一些拥有民族生活经验、熟悉民族历史,又具有较高创作水平的网络作家创作的作品将会受到读者关注;三是由于受到教育水平、互联网应用水平、文学阅读普及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将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低水平运行状况,商业资本的影响力较难以发挥作用,尤其是以民族母语为文本语言的作品,商业化机会较小;四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网站建设、作家培养、作品评介、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扶持、组织和引导,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