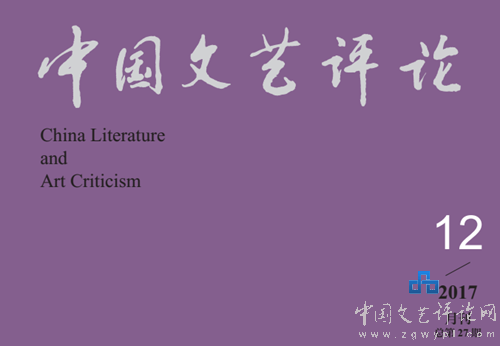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有声艺评(2018年第2期)-《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纵览
内容摘要:哲学与戏剧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内在联系,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憧憬和幻想的。王国维就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但是,中国话剧始终为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所困扰,而在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等方面,又往往陷于哲学的贫困。恩格斯曾说:“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之完美的融合”。这仍然是我们戏剧创作所追求的最高的哲学境界。 关 键 词:实用主义 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意蕴 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了,我想尝试着对中国话剧做一点哲学思考。我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确有些许的哲学冲动。记得1991年,王富仁教授约我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写文章,那时,就写了《文学史的哲学思考》[1]。我总觉得哲学可以让我从单纯的专业视野中解脱出来,有所超越,有所沉思,有所感悟。 我将我对中国话剧的哲学思考概括为三句话:一是中国话剧的哲学困扰,二是哲学和戏剧的姻缘,三是中国话剧的哲学贫困。 一 百多年来推动着、制约着、困扰着中国话剧的一个哲学问题,即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说它是中国话剧的推动者,自有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作证;说它制约中国话剧的发展,它又确实是束缚发展的一个紧箍咒;说它困扰,是说它困扰着中国话剧人和话剧管理者的思维和灵魂。 不可否认它是中国话剧的推动力。中国人最初接受这个洋玩意儿,就带着救国救民的内驱力。文明戏时期,一位叫天缪生的人说得最明白:“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2]因此,文明戏的主潮是以勇猛的姿态,配合着民主民族革命,对腐败的帝制进行冲击,对外国列强发出愤怒的抗议。天知派就是用新剧来鼓动革命的。 五四新文学的领导人物,如胡适倡导新剧,提倡易卜生戏剧,他也是把它作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和工具。欧阳予倩就认为戏剧是“思想之影像”[3]。洪深更认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4]。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田汉、夏衍倡导的左翼戏剧,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显然,就把它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了。抗战时期,话剧要为伟大抗日战争服务,几乎成为中国话剧人的共识,而且的确起到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伟大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人需要话剧绝不是出于人类本能的娱乐冲动。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对西方戏剧产生兴趣,并把它拿来,显然带有匡时济世的目的。当提出话剧为政治服务,就把戏剧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发挥到顶端了。一旦走向极端,那么话剧就被阉割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而“无论如何你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5],也就成为一种奢望。 我们看到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一方面成为中国话剧的推动力量;一方面又带来一种难以摆脱的深刻困扰,似乎至今都没有办法从中解脱出来。好像这种困扰是越来越加深了。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以新的姿态、新的口号、新的手段出现。最近看到一些剧作家谈到话剧困境,谈到自身的精神困扰,一些批评家也直言不讳地谈到中国话剧的种种困扰,但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实用主义的干扰。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它还在推动着制约着当前的中国话剧发展,这一切都让中国话剧人陷入深刻的困惑之中。似乎这样的哲学,就像幽灵纠缠着。 但是,对于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任何绝对化和简单化的论断,以及对它所造成的如此复杂的现象,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事物的复杂性往往需要我们从辩证中进行反思。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如此根深蒂固,它同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哲学有关。但是李泽厚是把实用理性作为“中国的智慧”之一而提出来的,一方面这种实用理性确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缺点。[6]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戏剧,对它在接受、运用和转化上,的确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但也由于为历史积淀的思想模式,阻碍着我们把话剧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重建和发展。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思想模式,几乎是无意识地铭刻在中国话剧人以及中国的文化管理阶层的灵魂之中,甚至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如果看到这一点,就知道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灌注到中国话剧的机体之中,绝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措施就可以达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有这样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 实用主义的简单化,是当前最主要的倾向。有用或者无用,几乎成为判断舍取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功利主义哲学。这在话剧领域中,无论是戏剧创作、戏剧批评和戏剧理论研究上都有所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的哲学研究中,对于“无用”的阐释,迫切地被提到日程上来,带有反潮流的精神。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思潮涌现着。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发表过《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一文,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正是这些蕴含另一种价值的“无用”知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他说: “综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我极力呼吁废除“用途”的概念,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极端重要性。……只要人类灵魂因这些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得到净化、提升并获得满足,它们的存在就有意义。它们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肯定”。[7] 的确,从人类的科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发展史来看,很多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巨著,大都出自那些出于兴趣爱好和某种追求,而不是“实用”目的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贫困潦倒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司马迁写《史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都是如此。 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更长远、更宏观、更宽容、更辩证地看待一些似乎纠缠不清的问题,即使实用主义在话剧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如何复杂的现象,也是可以从哲学的高度给予阐释,直到可以透视中国话剧的现实和发展。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二 哲学与戏剧的关系,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种关系有着它更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对此,我们是有所忽视的。近期出版的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从理论上和音乐的实践上阐明哲学和音乐,也可以说哲学和艺术的内在联系。他说:“哲学和艺术在真理内容的观念上是互相交叠的。一部艺术作品的逐次展开的真理无异于哲学概念的真理性。”“真理内容并不是艺术作品所意指的东西,而是决定艺术作品本身是真是假的标准。就是艺术中真理内容的这种变体,而且只有这种变体,易于接受哲学式的阐释,因为这种变体符合一种哲学真理的适当概念。”他还说:“审美经验必须转入哲学,否则它将不是真正的审美经验。”[8] 话剧《雷雨》剧照 在我写《曹禺剧作论》时,曹禺的《雷雨》和《雷雨•序》给了我对戏剧的哲学思考一次启蒙。他说:“《雷雨》对我是一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9]我也根据当时的认识做了一些肤浅的解读;后来,我更深切地认识到,曹禺的《雷雨•序》和《雷雨》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个艺术的哲学境界。《雷雨》是曹禺生命的一次燃烧,是他的生命哲学的升华。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憧憬和幻想的。王国维就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10]由此,更诱发我对话剧做点哲学思考。刘再复在《〈红楼梦〉悟》中指出:“哲学有理性哲学和悟性哲学之分。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概念、范畴的运作,而是浸透在作品中的哲学意蕴。”[11]他对《红楼梦》的宇宙世界、《红楼梦》的哲学内涵,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的确,伟大作品都有着它的哲学的视角,也就是作家的宇宙观、哲学观;有着它哲学的基石;有着它的哲学问题;从而形成它的哲学的境界。譬如莎士比亚剧作,之所以在世界上广泛流行,它的魅力就在于有着丰富的哲学意蕴。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指出:“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作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12]可以这样说,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蕴蓄着哲学的意涵。哈姆雷特就是一个悟性哲学的化身。 曹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具有艺术的持久性和诱人的魅力,在于他的作品中也有着他的宇宙世界,那就是天地之间的“残忍”。他确有着他独到的哲学视角,那种从污秽中看到金子,从邪恶中看到善良,于是才有了他惊人的艺术发现。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成为典型,正如黑格尔所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3]。“人是可怜的动物”就是他作品中的哲学命题。正是这种看来极为神秘的宇宙感,使之成为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的宇宙的视角,形成一个高远而宏大的宇宙境界。曹禺说,现实主义是不必那么现实。也就是说,以超越现实的视界来观察现实,才能有所升华,有所提炼,有所发现。 如果审视欧美近现代的戏剧思潮,都和哲学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戏剧思潮,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有关,他的《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的诞生有很大的影响。而现代主义无疑又同尼采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关。强大的哲学思潮,往往是文学和戏剧思潮的涌动的渊薮。朱光潜自称是“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14],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悲剧心理学》,就是在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学说的启示下对悲剧心理的研究。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拉斐尔认为《悲剧心理学》“对建立一种全面的悲剧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论据”。[15] 中国的话剧本应汲取西方戏剧发展的哲学视阈,但是却得了自闭症,把话剧封闭在自家小院子里,往往失去了哲学的开阔的胸襟、高远的视野和穿透的洞见。 三 当我们看到哲学与艺术的不可分割的性质,那么,再看看当代剧作以及戏剧的理论和批评,的确处于一个哲学贫困的境遇之中。 在新时期初期,在创作中一度也有一个哲学热,就是在剧作中硬塞进一些哲学理念,当时就受到批评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探索剧热潮中,可以看到中国话剧蓬勃的生机,让人欣喜地看到它带着一种哲学的冲动在冲刺,是对人生的叩问,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人、对人性的紧张的探索,一些戏剧作品出现了具有哲学意蕴的因素。正当酝酿着一个爆发的时刻来临之际,却顿然地消失了,眼看着失去了一个戏剧热能爆发的风云际会的大机遇。 《狗儿爷涅槃》是一部可圈可点的剧作,一个狗儿爷,一个时代的悲剧典型,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形象,就是那个大机遇涌现的风向标;如果说有阿Q哲学,那么就有狗儿爷的哲学,一个印记着深刻的历史悖论的哲学。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环境气氛失去了,精神境界失去了,似乎再也不能回来。在大风波过去,冒出一个过士行,一个《鸟人》就让人刮目相看了,他是一个在创作中有着哲学感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于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有人写过的闲人世界,而且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一个带有普遍悖论的生存状态。《棋人》《渔人》之后,过士行似乎在创作上也遇到了他自己的困境。 话剧《鸟人》剧照 我说,不是我们的剧作家低能,或是过度的抑压,或是精神的迷失,或是堕入食利哲学的陷阱,而导致了精神的贫困,也就是哲学的贫困。这种心灵上的焦虑和利害衡量的病状,是难以获得创作上的悟性哲学灵感的。 我曾经指出被认为是可与《茶馆》媲美的《窝头会馆》,就是一部作家陷于哲学困惑的剧作,远逊于《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作者以经济原因说明旧中国的失败,就缺乏超越现实的思考。而《立秋》的故事,把诚信作为主题,也是缺乏对故事的哲学的审视。尤其全剧的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因为老奶奶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更是一个缺乏历史逻辑说服力的败笔。 目前大家都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怎样算是讲好一个中国故事?有的抗日神剧故事跌宕起伏,也写得颇为诱人,这能算讲好故事吗?其中的关键在于怎样才是一个好故事。如果剧作家缺乏对故事的悟性哲学的思考,也就很难逾越故事的表层,失去对其内涵的开掘、对其中诗意的发现。 目前人们也在大力提倡现实主义,问题在于提倡的是哪种现实主义?是鲁迅先生大胆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还是伪现实主义?真的现实主义,首先是需要胆气的,恩格斯就说:“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16]。哲学告诉我们,生活中是充满矛盾的,直面人生,戏剧就要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而目前规避矛盾、粉饰矛盾几乎成为话剧创作中的通病。在我们的剧场中,毫无人间烟火味、言不及义的作品不少,而焦菊隐先生说的“这里是一片生活”的剧作确实太少了。 又如历史剧的创作,如宁宗一教授所指出的:“相当一部分新编历史剧还缺乏一种历史的胆识、历史的襟抱和历史的气度,逐渐形成了套路、模式,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乃至恶俗化,历史故事的程式化更偏离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这类作品仅仅停留在观照历史表层的阶段,更高层次的民族感和古远的历史追溯意识,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句话,缺乏一种可以称之为史之魂、诗之魄的气度以及二者交融的思想蕴含。”[17]不但是历史剧,所有的戏剧创作,如果缺乏历史的胆识、历史的襟抱和历史的气度,也就是哲学的胆识、襟抱和气度,那必然使自己的创作跌进平庸的境地。 恩格斯曾说:“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之完美的融合”。[18]这仍然是我们戏剧创作所追求的最高的哲学境界。 *田本相: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 注释: [1] 田本相:《文学史的哲学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 [2] 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第2卷第1期,1908年。 [3] 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 [4] 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现代戏剧》第1卷第1期,1929年。 [5] [德]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3页。 [6] 参看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谈中国的智慧》,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322页。 [7] 转引自微信公众号“赛先生”2016年5月7日《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作者为[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39年第179期(issue 179,June/November 1939)。 [8] 转引自[德]泰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译者导言》,《新音乐的哲学》(第五版),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7页。 [9] 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1卷,田本相、刘一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11] 刘再复:《〈红楼梦〉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第210页。 [12] [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99页。 [13]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8页。 [1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15] 转引自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16]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马尔加丽塔•哈克纳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8页。 [17] 宁宗一:《历史剧亟须历史哲学灌注》,《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3日。 [18]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延伸阅读(点击可看):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