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史知识建构的叙事
艺术史研究虽古已有之,但它的成熟和兴盛却是近代的事。温克尔曼和黑格尔被誉为“艺术史之父”,继两位奠基人之后,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史家,以至于艺术史在今天的人文学科中成为一门令人惊叹的“显学”。在林林总总的艺术史研究中,各种范式相互竞争,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不断涌现出新的艺术史论和艺术史观,不断重写着艺术史的版图。

温克尔曼、黑格尔(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艺术史”这个概念在汉语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指艺术过往的历史,其二是指对这里过往历史研究的学科。根据《牛津艺术术语简明词典》,“艺术史”(art history)英文定义是:“如其所指,艺术史是一个涉及贯穿各时期到当下的各种表现形式之艺术的历史研究的学科。”①虽然艺术史所面对的各种视觉对象,从雕塑到绘画到建筑等,但艺术史却又不得不通过语言媒介来表述。因此,叙事乃是艺术史知识构成的基本形态。那么,何为叙事?简单地说,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讲“艺术的故事”,这恰好是贡布里希一本著名的艺术史论著的标题。从史学角度说,历史学家就像是个小说家,他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爬罗剔抉,选取有用的材料,编织“情节”,进而讲述生动活泼的艺术史故事。正像史学家怀特所言,历史研究如同小说家虚构故事一般,“通过对事件中的某些材料的删除或不予重视,进而强调另一些材料,通过人物的个性和动机的再现,叙事基调和叙事观点的变化,以及改变描述策略等,历史事件便构成为一个故事。简而言之,所有这些技巧我们通常会在一部长篇小说或一出戏剧的情节设计中发现。”②
其实,叙事不仅是历史的主要方式,也是一切科学知识建构的主要方式。利奥塔指出,叙事总是与科学知识联系在一起,知识是通过叙事来传递的,所以,“确定一下叙述知识的性质,这种考察至少能通过比较,让人更清楚地辨别当代社会中科学知识具有的某种形式特征。”③据此我们不妨说,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过去的历史叙事。
基于这些观念,本文将采取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讨论艺术史的叙事问题透过艺术史叙事的二元性结构,探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艺术史复杂的叙事张力,进而触及艺术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当我们把艺术史视为一种历史叙事时,就为引入叙事学理论来讨论艺术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说艺术史家很像“说书人”,他或她的艺术史研究乃是讲述艺术的历史故事,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说什么和怎么说。说什么涉及艺术史的讲述内容,而怎么说则关乎艺术史的讲述方式,两者密切相关。这里,我更加关注怎么说,因为怎么说往往决定了说出什么,即是说,当你采用特定的观察角度和特定立场来审视驳杂的艺术史史实时,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会制约着艺术史家对艺术史实和史料的选择。
伟大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解释画家的看与画之间的关系时,曾经深刻地指出:“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④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在观看和表现风景是受制于内心的某种“图式”(schemata),而这个图式来源于他的文化传统。只有与这一图式相匹配的风景,才会跃然而出,成为画家注意力的中心。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一图式在叙事过程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这就引出了艺术史叙事的视角问题。
一、作品与观者的二元叙事
艺术史发展的关键期是19世纪下半叶,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德国艺术理论家费德勒。费德勒的主要贡献是为艺术史研究设定了基本议题,那就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乃是造型艺术特有的视觉形式,他写道:“造型艺术表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只是看待事物的方式。”在艺术世界里,“事物的可见性可以在对纯粹的外在形象的塑造中实现……这些形象是为了可见而被创作出来的,那么规则也只能在其展现视觉意象的特性中才能揭示。”⑤费德勒的这一表述可以说预先埋下了艺术史的两种叙事方式张力的种子。外在形象的可见性形式显然是指艺术品的呈现方式,但这些可见形式从发生学角度说源于艺术家,可以说是艺术家看待事物的方式造就了艺术品;另一方面,这些可见性形式又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各种各样的观者而存在。在费德勒那里,实际上包含了几种不同的怎么说艺术史的叙事方式。其一是以艺术家看待事物方式的变化来叙说艺术的历史变化,其二是从艺术品本身的可见性形式来讲述,其三是以观者及其观看方式的演变来叙述艺术史。尽管费德勒并没有清晰地区分三种不同叙述方式,但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可能性。
此后,深受费德勒影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袖李格尔,在其艺术史研究中,开始显露不同艺术史叙事的差异性及其方法论的自觉。他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风格问题》和《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就隐含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史叙事。前者讨论了装饰纹样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建构了一个典型的聚焦作品可见性形式的视角,从装饰纹样复杂的类型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入手,去探究更为重要的艺术史难题,即艺术风格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李格尔要努力证明的是,在各种看似无关的装饰纹样之间,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内在动因。所以装饰纹样的嬗变既不是艺术的材料变化的结果,也不是艺术所采用的技术变革的影响,甚至也不是人们模仿自然物的冲动所指,而是人借助艺术纹样来装饰自己这一根本性的动因。更重要的是他坚信,有某种“装饰背后的纯粹心理的、艺术的动机”在影响艺术的历史发展,这就是他著名的艺术史概念——“艺术意志”。《风格问题》围绕着装饰纹样的历史演变来叙述,将纹样类型学及其演变的考察作为艺术史的对象,这就确立了一个以艺术品可见性形式来讲述艺术历史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温克尔曼以来的艺术史著述经常见到,也是艺术史叙事最常见和最传统的方法。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继《风格问题》出版8年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著作《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不同于前者讨论具体的纹样变化,后者着力于研究罗马晚期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总体时代风格。李格尔似乎意识到纹样风格类型研究的作品中心叙事的局限,开始尝试新的叙述视角——观者视角。在这一研究中,艺术的可见性形式与观众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结合起来了。以观者视角来审视罗马晚期艺术,并拓展到此前和此后的艺术史变化,李格尔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尤其是过去罗马晚期艺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西方艺术史的衰落期,李格尔通过观者看待事物方式的特定视角来审视,却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那就是罗马晚期的艺术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具有开启现代艺术的进步作用。他从历史角度来解释艺术史上建筑、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的形式变化,提出了著名的三种观看方式理论。这三种观看方式就呈现为古代艺术史中的三种风格的连续演变,第一种称为以触觉为主的近距离观看,其可见性形式是古埃及艺术;第二种叫做触觉—视觉的正常距离观看方式,其可见性形式是希腊古典艺术;第三种名之为远距离的视觉的观看方式,其可见性形式显著体现在罗马晚期的艺术中。⑥在我看来,观者及其观看方式在李格尔那里并没有细致的界定和分析,所以包含了丰富的可进一步阐释的理论内涵。从一个方面来说,观者当然包含了艺术家本身,特别是在他分析的君士坦丁拱门的个案中,深浮雕形式显然包含了艺术家的观看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李格尔的观者概念中,实际上还隐含了一个更大的艺术史观者,正是这个观者的存在,艺术史几千年观看方式的历史演变才得以确立为艺术史叙述的对象。我想,李格尔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史家,他所以自觉地站在20世纪初的时间点上重新审视罗马晚期艺术,并将这一时段的艺术风格置于前后关联的历史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正是这个艺术史的“超级观者”功能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个艺术史观者的确立,才有可能跨越几千年去探究从埃及到希腊再到罗马晚期的艺术形式风格的历史演变规律,以及形式风格的演变与观看方式变迁的内在关系。
为了说明李格尔的两种艺术史叙事,我们可以借用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来阐释。文学研究有所谓作者意图论、文本意义论和读者反应论。围绕着艺术品和艺术家的艺术史叙事就是前两种理论的合体。从瓦萨里到温克尔曼到费德勒,其间有一个从艺术家到艺术品叙事方式的转变。文学批评中也有一个从作者到文本的转变,古典传记批评和浪漫主义批评,都彰显出诗人的立法者地位,到了20世纪,关注作品自身的文本批评成为主流。值得注意的是,从费德勒再到李格尔,从艺术品到观众的转变已经带有一定程度的接受美学观念,艺术的历史既不只是艺术家的历史,也不是只是艺术品的历史,应该包括艺术的观者这一维度,这才是完整的艺术史结构。从比较的意义上说,艺术史观者视角的建构显然早于接受美学半个多世纪。其实,从伽达默尔的观念来看,历史应该是一种“效果史”,所以历史的阐释是在特定的效果史中存在的,接受美学正式接受了这一理念。所以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姚斯指出,“现在必须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放进作品与人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历史连续性放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看。换言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特征的历史。”⑦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李格尔的罗马晚期艺术风格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这样的理念,虽然他并没有像姚斯那样明确地建构一个艺术品接受主体的观者角色。
较之于曾经传统的以艺术家为视角的艺术史叙事(如瓦萨里的叙事),以艺术品为视角的叙事更具有现代性(如费德勒的叙事),同理,相较于艺术品为中心的叙事,观者视角的引入拓展了艺术史叙事的现代性。这就开启了艺术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观念——视觉性。今天,随着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视觉性越来越成为一个艺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从沃尔夫林到帕诺夫斯基,从贡布里希到弗斯特或米歇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观看方式的视觉性是如何嵌入艺术史亦即视觉文化研究的。假如说李格尔的观者观看方式还是一个比较中性或含混的概念的话,那么,弗斯特关于视觉性的解释显然带有更为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如他所言,视觉性被掩盖在视觉现象看似自然的秩序之中,通过对这些秩序的解构,我们就能瞥见支配着观者去看的视觉性,“我们如何看,我们如何能看,如何被允许看,如何去看,即我们如何看见这一看,或是如何看见其中未现之物。”⑧
二、“物学”与“阐学”的二元叙事
上世纪20年代,艺术史家帕诺夫斯基在其著名的《论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史,一种名之为作为“物之学问”(以下简称“物学”,Dingwissenschaft,or science of things)的艺术史,另一种称为“阐释之学”(以下简称“阐学”,discipline of interpretation)的艺术史。在他看来,艺术史所面对的是历史上是不同时期艺术家的各种艺术的样式或设计(design),相当于费德勒所说的可见性形式,这既是每个艺术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艺术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实际形态。因此,这些样式或设计所依循的原则或原理,便成为艺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艺术研究主要有三种形态:艺术理论、物学的艺术史与阐学的艺术史。那么,后两种艺术史的差别何在?
帕诺夫斯基提出,物学的艺术史是一种运用表层概念(暗示性和演示性概念),来描述艺术史上的经验性事实,比如特定艺术品的艺术风格,以及它在艺术史序列中的时空位置等等。不同于物学艺术史,阐学的艺术史旨在揭示个别的经验现象背后的风格的整体特征,是艺术理论与物学艺术史的有机融合。他写道:
作为物的纯粹学问,艺术史研究可以以诸种艺术问题为指引,却不对这些问题本身加以思考;此时,它可以理解风格标准及其汇总,却无力去理解种种样式原则,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合力。后者属于更深层次的知识,研究者须对那些已知的和既定的问题(相对于狭义的艺术史研究)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掌握,借助于艺术理论所构筑的基础和专门问题体系,对那些已知和既定的问题作出更深入的思考。⑨
帕诺夫斯基所说的两种艺术史,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方法:物学是一种是经验研究型的艺术史,它关注的是个别艺术作品的表层风格现象,以描述的方法为主,重在说明它“是什么”(what)以及在艺术历史演变的序列中所处的时空位置。中西传统艺术史论的许多研究大多属于这一类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类艺术史研究更偏重于经验性、描述性和批评性。阐学艺术史则偏重于知识的理论建构,着重对各种纷然杂陈的艺术现象背后深邃的历史或文化乃至形而上的终极原因加以探究。所以,阐学艺术史不只说明“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楬橥“为什么”(why)。帕诺夫斯基特别指出,这种艺术史的研究追求因果律的逻辑一致的阐释,关注各种看似不同的表象之间背后内在的统一性和关系性,建构出一个复杂的问题结构,并为物学艺术史提供基本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像是艺术史的深度解释模式。帕诺夫斯基自己深受德国哲学和美学的影响,极力主张这种深度阐释的艺术史。李格尔“艺术意志”理论对他亦有启发,所以他主张阐学艺术史的最终指向是艺术史风格嬗变的内在动因——艺术意志。如他所言:“阐释性方法还要证明,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贯然一体,无抵触之处……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家面对艺术根本问题时的立场,也唯有如此方能理解种种样式原则背后的根本风格原则。如此,也惟其如此,科学的研究方法能从内部、从‘艺术意志’的意义上把握住风格,不再视其为感性特质的累加,亦非风格标准的集合,而只能是既寓于具体样式原则之中,又超然其上的整体原则。”⑩显而易见,帕诺夫斯基最终是要在不同的艺术样式后面追寻某种统一的艺术原则,而这以原则的真正动因则是李格尔所猜想的“艺术意志”。
帕诺夫斯基所以指出两种艺术史叙事的差异,其要旨在于说明艺术理论对艺术史的知识建构的重要性。以艺术理论为基础的阐学艺术史,对艺术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探究,最终揭示出艺术中纷繁复杂的样式后面的原则,而缺乏理论的物学艺术史则只停留于艺术的现象描述层面。其实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像詹姆逊在讨论理论阐释时所指出的,各种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阐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表层阐释,另一类是深度阐释。他特别列举了四种主要的深度阐释理论模式:辩证法、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符号学。(11)虽然这四种深度解释模式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深度阐释理论,但从艺术史研究来看,这些理论的确影响了艺术史研究,加强了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深度,并为有理论支撑的深度阐释的艺术史叙事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对晚近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艺术史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理论化转向”,艺术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史实认定和现象描述,而是越来越深地探究隐含在这些现象后面的历史动因和可见性形式的原则。换言之,我们有理由说,阐学艺术史已经成为晚近艺术史研究的主流。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帕诺夫斯基的艺术史研究的问题,那就是某种单因论或单一原则的倾向,他虔信李格尔的艺术意志说,并将这个观念置于自己的艺术史阐释之中。今天,更重要的发展是,今天的艺术史研究早已摆脱了单因论或一元论的说明,越来越倾向于复杂系统多因交互关系的解释。
在我看来,艺术史叙事的这一二元结构还隐含了某种递进转换关系。物学艺术史是任何艺术史家进入艺术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关键在于研究不能止步于物学“是什么”的探究,还必须深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对艺术样式原则所以如此的“为什么”的说明。这就需要更多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这样才能深入到复杂的艺术史现象内部,去挖掘隐含其后的深层历史动因。
三、形式论与语境论的二元叙事
艺术史在20世纪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与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型就是从风格史向社会史的转变。大致说来,20世纪的前半叶,发源于德国的风格史占据了艺术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而下半叶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社会史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风格史偏重于形式分析,而社会史强调艺术的社会动因及其影响。
80年代中期,美国艺术史家普罗恩用两个英文概念描述了这一二元概念,他写道:
我发现以如下方式来界定这一变化颇为有用,那就是从the history of art的传统研究向art history研究的转变。在前一种艺术史中,其主题是艺术,研究的乃是构成艺术发展的因果模式,诸如风格的、图像学的或传统的因果模式。其基础性的工作一直是分类学的,对各种我们称之为艺术的物品加以分类,进而得出有关创作者、年代学、民族的或个体的风格以及真伪的结论。在我们这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现在,艺术却越来越被看作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其主题是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和文化史。这里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要达致对个体和社会更深刻的理解,而艺术作品则提供了具体的证据。不同于词语和行为,艺术作品是一些留存下来的历史事件。在其中过去就存在于现在,在重新考察它们的本真证据时,历史也就可以被再次体验。art history的研究焦点不再是the history of art的焦点,但它无需降低作为艺术的艺术之价值,而只是扩大其潜力而已。(12)
如果我们用更为简洁的术语来概括,the history of art和art history的差异,一如风格史与社会史的二元叙事。其实,早在文学理论中就有人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方法论二分,(13)艺术史的这两种叙事的根本差异也就是这一二分之差别。
风格史的基本理路就是上一节所讨论的帕诺夫斯基的思路,就是对样式或设计及其原则的阐释与分析。普罗恩认为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艺术史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历史地看,社会史其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史叙事方法,尤其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考察艺术的历史演变,成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法论。从经典作家的理论,到机械的唯物论,再到批判理论和新左派理论,社会史始终是艺术史叙事的重要范式。卢卡奇、豪塞尔、安塔尔等早期社会史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到上世纪后半叶勃兴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史,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局面。除了德语国家的这些理论学派,在英法等语区也发展出文化社会学、文化研究和相关的社会史研究理论,比如布尔迪厄关于艺术场和趣味的艺术社会史研究,威廉斯关于艺术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等,都是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典范之作。(14)
不同于风格史基于艺术自主性的历史叙事,社会史着重于考量艺术和社会的复杂关系。艺术社会史的奠基人之一豪塞尔早在50年代就提出,艺术社会史研究的任务有三:首先是通过发现创作时间、地点、艺术家的同一性、所属流派或运动、买主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支配艺术品实现的各种条件等,来给艺术品定位;其次是确定艺术家所依靠的传统、流行的技巧标准、题材范围、占优势的趣味;最后是查明艺术品的理解和作用,以及作品与时代精神的关系。(15)到了20世纪末,关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对象有了更为复杂的表述,比如克拉克就明确指出,艺术社会史并不探究艺术品如何反应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也不考虑艺术家属于哪个流派团体,更不能把艺术形式和社会观念简单对应,他要研究的是如下问题:“艺术形式与现存的视觉表征体系、现行的艺术理论与意识形态、社会的不同阶层、阶级与更普遍的历史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16)更为重要的是卡拉克强调,每一个艺术家都会对他的社会背景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必须考虑到艺术家、艺术品与社会背景变化的、差异的和复杂的关联。他通过库尔贝、马奈等艺术家的个案,具体阐明了这一复杂关系的复杂性。
晚近的说法是将社会史研究视为更为广阔的“艺术语境”研究,这种说法其实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语境研究一般区分为几个相关不同的路向,诸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等。(17)这些俨然成为晚近艺术史研究的主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艺术史研究越来越带有文化政治色彩,许多原本只在艺术范畴内讨论的艺术史问题变得极具争议性,从经典的文化战争到表征的政治学,从性别、阶级、族裔的讨论,到流散、身份认同、艺术全球化的争议,艺术史研究成为一个充满了差异性和认同合法性论争的知识战场。
形式论和语境论是这一二元叙事的方法论差异所在,一些关于艺术史的基本概念的差异,导致了两种艺术史叙事的不同取向。风格史的核心概念是艺术在自主性,比如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史观念。在他看来,每个时代都会有某种作为艺术本质的艺术意志,它制约着特定时期的艺术风格:
创造性的艺术意志将人与客体的关系调整为以我们的感官去感知它们的样子;这就是为何我们已经赋予了事物以形状和色彩(恰如我们以诗歌中的艺术意志使事物视觉化一样)……倾向于通过视觉艺术将事物做悦人的视觉化。(18)
尽管李格尔也说艺术意志带有内驱力的性质,且受制于民族、地域和时代而有所变化,但实际上他要努力证明的是,艺术意志是导致艺术史演变的内源性的和根源性的动力。比如他区分的古代埃及、希腊古典和中世纪晚期三个阶段,艺术风格及观看方式的递变,完全受制于内在的艺术意志的支配。
社会史则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如果说形式主义范式强调的是内在演化规律的话,那么,语境主义则聚焦于作为背景的社会文化对艺术风格嬗变的影响。各种各样的社会史范式旨在证明艺术风格的变化乃是社会变化的产物。更激进的理论强调,艺术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知识体系,深受16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些表面上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的艺术史,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制约着艺术史的叙事。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些全新的概念来研究艺术史,诸如“阶级斗争”“视觉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觉意识形态”等。由此楬橥艺术史与社会阶级结构之间隐而不现的关系。(19)更进一步,激进的艺术社会史家哈金尼古拉(Nocos Hadjinicolaou)直接提出,应该用“视觉意识形态”概念来取代传统的风格概念。他说:“艺术史不过是种种视觉意识形态的历史。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替换一下1920年代的中产阶级口号,用‘图像生产史就是视觉意识形态史’,来代替‘艺术史即风格史’。进而可以说,艺术史这门学科的主题就是种种视觉意识形态,它们就出现在时间过程之中。”(20)由此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就成为视觉意识形态的分析,而传统的风格概念便被聚焦到艺术的社会集团利益及其艺术风格的分析上来。于是,艺术史研究成为文化的阶级分析的领地,风格史所专注的那些可见性形式问题统统转化为阶级的视觉意识形态问题。
假如我们跳出形式论与语境论的两种艺术史叙事的对立格局,可以发现两者其实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逻辑,虽然在艺术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两者针锋相对。站在语境论的立场上看,形式论说到底不过是“垂死的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异性恋”价值观的产物;从形式论的观点来看,语境论完全不顾艺术史叙事对象是艺术而非政治,将艺术史变成政治问题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主张语境分析的艺术史研究,也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在形式论止步的地方起步,进一步挖掘风格后面社会成因;其二是把焦点直接对准艺术家及其制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不再关心风格的形式层面。所以,这就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那就是艺术史叙事的形式社会史,或者说是形式语境论。在这第三条道路上,形式与语境并不是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找到一些结合点,使得艺术史叙事既有风格形式的具体分析,又有涵盖了相关的语境问题的研究。当然,这第三条道路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以形式分析为重心的艺术史研究,语境及其相关问题蕴含其中;另一种是以语境分析为重心的艺术史叙事,形式分析最终用来说明语境的制约性甚至支配性。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往艺术史无论风格史还是社会史,倾向于某种类型学的研究,亦即将艺术家归类为特定的群体或运动风格,进而对其作总体的说明。而克拉克更加倾向于个体性的研究,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艺术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每个艺术家对语境的反应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群体的风格类型学研究不足以说明特定艺术家的独一性艺术表征。所以,克拉克主张并践履一种艺术家的个案性研究,以期揭示出每个艺术家对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独特反应。这一研究方法是由启发性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艺术史从来就有一个信条:“艺术史是匿名的。”这就是说艺术史关注的不是具体个别现象,而是更为普遍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或群体的艺术风格。如何在个案性研究中保持一定的社会文化普遍性问题框架,个体如何与一定的群体关联,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因为不管怎样,艺术史都不会是个别艺术家的历史,所以艺术家之间社会的、历史的和艺术的关联始终是艺术史叙事必须关注的。
四、展览与学术的二元叙事
艺术我们讨论了一些艺术史叙事的方法论,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往往都来自一个领域:学术界或知识界,尤其是随着晚近社会文化的科层化和体制化的进一步发展,艺术史知识的载体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其生产者主要是教授、专家等专业学者。但是,如果我们超越学术界的艺术史知识系统,便会发现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史知识,它们不在书本上、课堂上、研讨会上和专业杂志上,而是以一种活生生的形态与大众亲密接触,那就是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史及其呈现方式。特别是随着艺术博物馆的迅猛发展,从官办博物馆到民营博物馆,从国家收藏到大公司收藏到个人收藏,艺术史的叙事呈现为另一种方式。这就引发了学术的艺术史叙事与展览的艺术史叙事的二元对峙,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艺术史知识生产体制,艺术博物馆是以策展、作品展陈的方式展开的艺术史叙事,是具体的艺术品的实物形态编排所展示的对艺术史的叙事,它有赖于策展人和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士直接的通力合作。学界的艺术史叙事主体却来自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一些专业艺术史家或研究者在书斋、课堂、出版物和专业会议等机制中形成的艺术史叙事,更带有文本性。
1999年,在美国的克拉克艺术史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年度会议,主题是“两种艺术史:博物馆与大学”,三年后出版了这次会议的同名论文集。会议的发起人和论文集主编哈克索森(Charles W.Haxthausen)在导言中写道,当他提议召开一次该主题的会议时,得到了欧洲和北美艺术史学者和博物馆策展人的出乎意料的热烈响应。从此次会议及其讨论来看,以下一些问题与两种艺术史的紧张有关。(21)
首先,总体上看,学院派的艺术史往往比博物馆的艺术史更为激进,更偏重于理论和社会史,而博物馆的艺术史叙事则更关注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因而显得比较保守。一些在学院派艺术史中的议题或方案,常常很难在博物馆展出中呈现,比如激进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批判等。这就造成了两种艺术史之间的对抗性叙事。
其次,学院派艺术史叙事往往是学者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的反映,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比如在学者的艺术史著述或课堂或会议上,学者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理论想象和论证,但博物馆的艺术史展陈却要受到诸多现实问题的限制,从资金筹措到观众兴趣到社会反响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博物馆艺术史的故事讲述内容和方式。比较起来,学院派的艺术史叙事更具个性化自由,体现了研究者兴趣导向;而博物馆的艺术史叙事则更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带有社会效益和观众导向的倾向。有个别展览由于采取了激进的艺术史叙事,导致了公共舆论和收藏家、画商、批评家乃至普通观众的抵触和怨怒,进而使得展出归于失败。这样的事例清楚地表明博物馆叙事是一个公共事件的特性。这就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体制性因素(资金和观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展览中讲什么和怎么讲艺术的历史故事?观众的偏好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展览的内容和形式?
再次,博物馆与学院派的艺术史叙事所关注的媒介亦有所不同。博物馆关注的是艺术品实物形态,是需要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品的编排或组织,在特定的历史线索或主题中加以呈现,进而彰显出艺术品及其艺术家的艺术史意义。所以,博物馆展出的形式、结构,展品的顺序和关系,对于艺术品及其艺术家的理解具有导向性。正像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加斯科尔在其《维米尔的赌注》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艺术品只是一个手段,它并不存在任何孤立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展馆展览空间里,展览的特定安排必然对一幅画会产生特定的影响,所以一幅画的艺术史意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空间里被生产出来的。(22)相比之下,学院派的艺术史叙事,尽管仍以艺术品为中心,但却不是实物形态的作品,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原作的照片复制品。更重要的是,学院派的艺术史叙事要通过文字,而图像不过是说明文字的例证而已,这与博物馆现场感的观看活动有很大的不同。由此便延伸出一个复杂的问题:艺术史叙事的文字与画作直接的复杂关系。有人发现许多展览所出版销售画册或专辑,常常是邀约一些专家写的文章,与具体的展品及其展览之间并无直接的相关性。这就导致两种对立的艺术史叙事:博物馆艺术史叙事依赖展品实物,隐含其后的是一种重要的信念:艺术品原作远比阐释性的文字重要;而学院派艺术史家们则认为,艺术史叙事必须通过文字的阐释,由此呈现出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更有趣的是,博物馆人士很少会涉猎学院派的艺术史知识生产,而学院派的艺术史家们却往往参与到博物馆的展陈实践中去。
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最值得注意是如下说法,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实并不是博物馆和大学这些艺术史建制或学科内部的紧张关系,而是艺术史与公众的紧张关系。(23)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指出了两个群体的相关性,一个是“内集团”,另一个是“外集团”。艺术史与公众的关系就是内集团与外集团的关系,是艺术界各种专业人士及其职业和各种与艺术受众的关系。正像这个问题的提出者道伊奇的文章标题所标示的那样:“谁的艺术史?不列颠80和90年代的策展人、学者和博物馆访客。”道伊奇至少给出了三种人选:策展人、学者和公众。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有接踵而至,公众是谁呢?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访客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抽象的,但很多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指出,博物馆的访客永远是一群人,就是中产阶级。诚如布尔迪厄在研究西方社会中的艺术趣味是指出的那样,趣味是一个区分性的概念,“趣味使被纳入人身体的物质范畴内的区别进入有意的区分的象征范畴内。”(24)换言之,通常所说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特定社会阶级的产物,去卢浮宫观画,听勋伯格音乐,读《尤利西斯》,往往始终是一群人,即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因为“‘眼光’是由教育再生产出来的一种历史产物”。(25)而教育则与阶级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以此观点来看,所谓的博物馆访客也就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普泛的公众概念。按照奥尔特加上世纪初的研究,现代社会将人们分为两个阵营,一是大众,他们对各种新艺术或先锋派不感兴趣也无法理解;二是“少数选民”,他们经过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经济地位,所有具备了某种感官来欣赏高雅的或先锋的艺术。(26)这个情况在今天仍然存在,即使在中国当下社会,去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其实就是这些“少数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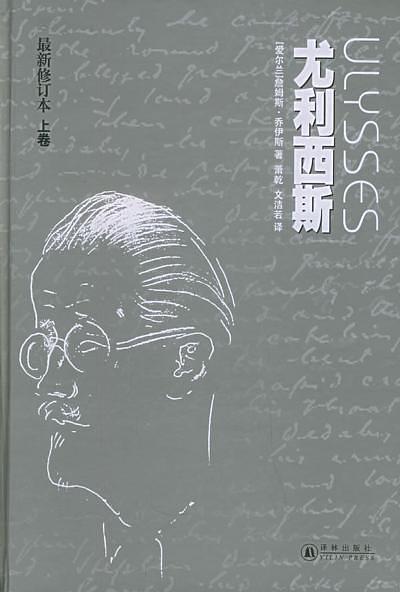
《尤利西斯》译林出版社(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回到内集团,两种艺术史叙事实际上是艺术史知识生产的两种不同形态。学院派的艺术史是主要是学术导向,面向学术共同体,所以往往体现出比较激进和创新的观念与方法。一种新理论和新观念的出现,往往带来新的艺术史故事素材的重新编排,导致新的贯穿主题,建构新的故事讲述方式。但学院派的艺术史叙事多以语言文本为载体,以同行专家讨论评议为目标,并不涉及一般公众或中产阶级受众。而博物馆叙事则直接面对社会公众,每一次展览所构成的艺术史叙述,既要考虑到博物馆(尤其是公共馆)的社会反应和舆论评价,又必须顾及资金筹措和大多数受众的观感和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的艺术史叙事面向更大的社会文化层面,因而所受的传统和当下的限制更为明显。
当然,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那就是大学博物馆。较之于社会上的公共或民间博物馆,大学博物馆与学术体制关系更为密切,展览的实验性和学术性也更强,其受众比社会博物馆范围更小也更为专业。这就带来融合学院派艺术史叙事与博物馆艺术史叙事的可能性。(27)
学院派与博物馆两种艺术史叙事的差异和冲突,实际上是丹托所说的“艺术界”的内在张力所致。按照丹托的界定,“将某物视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亦即艺术界。”(28)他后来补充说道,艺术品是符号性表达,在这种符号表达中它们体现了其意义。批评的意义是辨识意义并解释意义的呈现方式。照此说法,批评就是某种有关理由的话语,它参与了对艺术体制理论的艺术界的界定:把某物看成艺术也就是准备好按照它表达什么及它如何表达来解释它。(29)如果我们引申一下丹托的说法,可以做如下表述:何为艺术史需要某种艺术史的氛围,而艺术界内不同的群体依附于不同的体制,他们会生产出不同的艺术史知识。学院派与博物馆的艺术史叙事差异会永远存在。
注释:
①Michael Clarke and Deborah Clarke,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Te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569922.001.0001/acref-9780199569922-e-115?rskey=qD8b7I&resu1t=4[2018年8月2日登陆]。
②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Baltimore: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84.
③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0页。
④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⑤费德勒:《论艺术的本质》,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93、69-70页。
⑥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60-62页。
⑦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⑧Hal Foster,ed,Vision and Visuality(Seattle:The Bay Press,1988),ix.
⑨帕诺夫斯基:《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0页。
⑩同上,第20-21页。
(11)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0-162页。
(12)Jules David Prown,"Art History vs.the History of Art." In Art Journal,Vol.44,No.4(Winter,1984),pp.313-314.
(1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5年,第65-67、145-147页。
(14)See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Raymond Williams,The Sociology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15)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7-248页。
(16)卡拉克:《论艺术的社会史》,在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11页。
(17)See Anne D'Alleva,Methods & Theories of Art History(London:Laurence King,2005),pp.46-86.
(18)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213-214页。
(19)Nicos Hadjinicolaou,Art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London:Pluto,1978),pp.4-6.
(20)Ibid,p.98.
(21)See Charles W.Haxthausen,ed.,The Two Art Histories:The Museum and the University(Williamstown:Clark Art Institute,2002).
(22)See Ivan Gaskell,Vermeers Wager:Speculations on Art History,Theory and Art Museums(2000).
(23)Stephen Deuchar,"Whose Art History? Curators,Academics,and the Museum Visitor in Britai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Charles W.Haxthausen,ed,The Two Art Histories:The Museum and the University(Williamstown:Clark Art Institute,2002).
(24)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4页。
(25)同上,第4页。
(26)奥尔特加:《艺术的非人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27)参见维特克维尔:《20世纪后期的美术馆的重要性》,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8)Arthur Danto,"The Art World," in Carolyn Kormeyer,ed,Aaesthetics:The Big Question(Oxford:Blackwell,1998),p.40.
(29)丹托:《再论艺术界》,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学经典及其在中国传播接受的比较文献学研究”[17ZDA02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美术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